甲流会不会穿个马甲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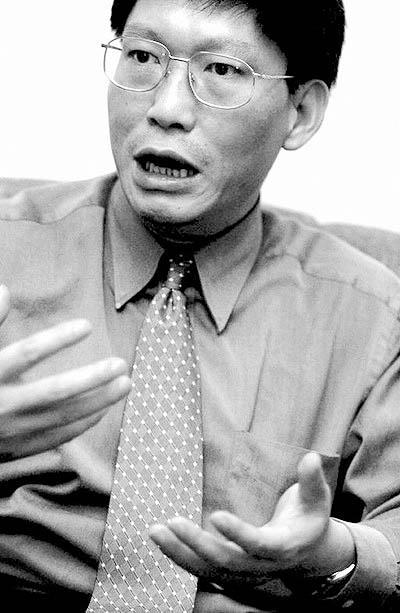
管轶

2009年10月29日,吉林,甲型H1N1流感防控。
胡小璐摄
尽管人们正在慢慢忘记,但甲型H1N1流感的威胁并未远去。
至少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官方网站上,与甲型H1N1流感有关的内容仍然被放在醒目的位置,仅次于为前往南非世界杯的球迷们做出的“卫生建议”。
而来自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系的研究者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猪身上进行基因重组后产生了一种新病毒。这一研究成果刊发在6月18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甲流并没有离开。”尽管在此之前,人们更愿意相信,每30年才会暴发一次大流感。更何况,甲型H1N1流感对人们造成的实际威胁,远比想象中轻微。但WHO病毒监测网络成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家伊恩·利普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病毒是难以预测的,不能因为去年大流感暴发,今年就开始松懈。病毒的演化速度太快了,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一种全新的病毒
眼下,重新唤起人们“甲流记忆”的新病毒,正待在微生物系管轶教授的实验室里。
这位病毒学家是世界级的权威流感专家。2003年春天,他最先分离出SARS病毒。两年后禽流感暴发时,他和团队又绘制出“禽流感传播的图谱”。
而这一次,“禽流感猎人”将目光瞄向了甲型H1N1流感。
流感病毒共由8个基因节段组成。如果两个病毒在同一细胞中相遇,并且它们的基因间能够互相兼容并自由组合,那么最后有可能出现256种子代病毒。从2009年10月到2010年1月,港大的研究小组一共在猪的样本上发现了8种“都与甲流有着亲缘关系”,但基因型各不相同的流感病毒。
病毒其实是无色的,但在论文中,研究者喜欢用各种鲜艳的色彩来代表病毒内部的基因段,从而让人们清晰地识别病毒间细微的差别。
“第一组基因型全是鲜红色的,这是与去年大流感基本一致的基因型。”实验室的博士后朱华晨说,她是论文的作者之一。嫩绿色的一组紧随其后,这是广泛流行在欧亚大陆的禽流感病毒,由鸟类传染给猪。第三组橘黄色的病毒,学名为“北美三重重组病毒”,据说,它已经在北美地区流行了10年以上,并在近年逐步扩散到其他几个大洲。
接下来的5种新发现的病毒基因型,已经不再是单一颜色,而是黄色、蓝色和绿色杂乱地交织在其中,这是“病毒之间频繁的基因交流后产生的新品种”。蓝色代表已经在全世界猪群中至少流行了七八十年的古典型猪流感病毒。
“但最后一种最为特别。”朱华晨强调。在这种病毒中,NA基因段呈鲜红色,也就是说,这段基因与甲型H1N1流感病毒相同。
根据病毒类别、宿主、发现地点、序号、分离年份和亚型等等,这株于2009年10月22日分离出的“新面孔”,被命名为“A/Swine/HK/201/2010(H1N1)”。不过,长期陪伴它的实验人员,更愿意亲切地称其为“香港201”。
十几年的流感调查实验日志表明,“香港201”在此以前从未被发现过。“红色片段”则立场鲜明地证明,甲型H1N1流感病毒传播给猪后,与猪体内原有的病毒基因进行重组,生成一种携带人类大流感基因的全新病毒。
一个笨拙的研究方法
尽管这种新病毒与甲流病毒只有一个相同的基因段,但它们却有着相似的个性。“香港201”同样也是一株活泼的病毒,一切与此相关的实验,必须在安全性极高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中进行。
想要进入该实验室可是一件浩大的工程,朱华晨每天都要“从头发武装到脚趾”。穿上类似面对生化武器时的防护服,戴上防毒面罩和呼吸器,再踏上雨鞋。此外,这身服装的所有接口都必须用密封胶布粘起来。
在P3实验室里,她需要经过8道房门才能到达饲养着携带病毒的猪的笼子。每走进一道门,气压都在降低,这就保证了空气只能由屋外流到屋内,而无法让屋内带有病毒的空气反向流出。
因此,面对着可怕的高危险病毒,实验人员从不担心,“在实验室里感染的几率可比在街上感染的几率小得多”。一个教授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世界上出现一种病毒有着禽流感的毒性和甲流的传播能力,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跑进P3,把自己锁在里面”。
在这个安全实验室最尽头的屋子里,才是感染了“香港201”病毒的猪生活的地方。
在过去的12年里,研究人员坚持每两周一次前往一家位于香港上水的屠宰场。这里有华南地区不同省份的猪,研究人员收集样本,并借此监测猪身上的流感病毒感染的情况。这是一项由香港大学和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共同开展的监测计划。
“我们进行着十分笨拙的科学研究。”管轶说。
这种看似“笨拙”的行为,不断充实着他们的病毒资料库。长期以来,猪被认为是猪、禽鸟、人类流感病毒的“混合容器”,禽类和人类之间的病毒很难互相感染,但猪却对这两种宿主携带的病毒都很敏感,“就像一个大搅拌器,把猪、鸟、人的病毒在其中混合,最终产生很多基因变种”。
此前,中国的华南地区一向被认为是产生新流感病种和大流感变异株的中心。去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暴发时,曾有外国学者臆断,这是由于“中国的养猪工人到美国加州,并将这个流感在北美传播开来”。
但管轶的研究团队在2009年10月以前,从未在猪身上发现过甲型H1N1流感病毒。“我们的数据完全推翻了这个说法”,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我们在猪身上检测到病毒的时间正好是中国区大流感爆发的高峰,这间接地证明,这种病毒绝非来自中国。”
当然,很多人并不知道,曾经让他们在2009年感到恐慌的H1N1病毒,并不是这个星球上的新产物。至少在上个世纪初暴发的西班牙流感中,正是H1N1型病毒中的一种感染了全球20%到40%的人口。在这场被称作“史上最恐怖的流感”中,有近5000万人死去,几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5倍。
一个并不可知的未来
不过,研究者们发现,“香港201”在猪群中可以“很有效地传播”,但似乎并没有很大威力。被传染的猪并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至少,它们既不打喷嚏,也不流鼻涕,“只不过原来很活泼,挺爱打架,现在却变得懒洋洋的”。
研究小组还调查了长期生活在猪群身边一些人的血清学结果。但血清学只能检测到病毒中表面蛋白所诱导生成的抗体,并且同一亚型病毒之间往往存在交叉反应,因此一个人的抗体是来自去年大流感的病毒,还是来自大流感的新型重组病毒,往往很难确定。他们计划利用人类的一些细胞或组织器官进行离体培养,“用这种方式看看新病毒是否会传染人”。
就眼下而言,科学家们并不知道,这种病毒是否能再次传播回人类。不过,没有人敢对流感病毒掉以轻心。根据WHO的报告,截至6月20日,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14个国家和地区确诊了H1N1甲型流感病例,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8209例。
在亚洲地区,最新一则病例来自中国台湾,一名62岁的医师于6月18日死于甲流,这时距离他发病仅有两周时间。
对于管轶来说,这也并不是他第一次面对难题。这位今年只有48岁的教授,曾在非典期间,第一个成功分离SARS病毒,并判断出SARS病毒极有可能是通过果子狸传播给人类。在明确了病源后,非典二次暴发的可能性被扼死在摇篮里。
而当2005年禽流感暴发时,管轶所带领的团队,又从样本中成功排出了250多个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这些样本,是从超过10万只禽类中取得的。仅仅获取样本,就已经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儿”,研究人员每天都跑到市场里去,说服摊主,让他们从待售的鸡、鸭、水鸟身上抽血,并收集那些可能带有传染病的粪便。
现在,这位休闲活动只剩下“看看新闻和足球”的教授表示,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计算机里也有很多论文等着完成”。他很少觉得疲惫,甚至在外国媒体的眼中,他被勾勒为一个不断抽烟的中国教授,“充满了科学上的狂妄”,并且“算不上很有耐性”。
但管轶愿意承认,“2009年H1N1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发现“香港201”后,他也并不回避,“在进行科学实验之前,病毒学家没有办法告诉你,究竟哪种病毒危险,哪种病毒不危险。”
他只是相信,如果世界上能多些愿意进行这样“笨拙的科学研究”的实验室,许多未来的病毒也许就能像“香港201”一样,被密切监视,也许最终会被销于无形。
“流感其实一刻也不停地在变,我们是在追,还不只是找。”朱华晨说,“另外,新病毒每一秒钟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生成,我们关心的是,谁才可能引起大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