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近日成功申遗。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个部分,始建于公元前486年,曾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此,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传播与公众参与专家组成员、文化遗产传播专家齐欣。在他看来,大运河文化遗产申遗成功,是社会各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大运河申遗成功会有怎样的社会影响?
齐欣:我们可以用最通俗的方法,将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影响,划分为“自身价值”和“身外价值”。
大运河不仅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交融的过程,而且还对大遗址式的文化遗产风貌区,提供了认知和管理的实验。更重要的是,“她”对我们社会参与者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大运河已是许多人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启蒙老师;另外,大运河的申遗经验,可以推及其他保护对象——比如成千上万待保护的传统村落。大运河是当下国内众多文化遗产“难兄难弟”中比较幸运的一个,“她”申遗成功反而不会让我们停下来。
中国青年报:你这个“我们”指的是谁?
齐欣:“我们”,指的是所有自觉地认同文化遗产价值的个体、群体和团体。这种认同感,首先来自于对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智慧的尊敬,新的特点是,我们开始从文化遗产的根本属性,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智慧之真实完整证明”中,强烈寻找自我的法理定位。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保护一个远古的文化遗产,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受损害,为我们自己保值。到了这一步,中国人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世界水平更贴近了。社会力量,也不再是“花边力量”了。
中国青年报: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可以辨识出来吗?
齐欣:非常清晰!大运河申遗是社会各界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发酵过程。率先觉醒并渴望得到社会支持的是文物圈。在大运河申遗成为我们的目标之前,传统文物保护,依靠的多是专业、行政的方法。比如故宫,比如颐和园,哪怕是西湖文化景观,其实都可划定在一个相对简单的范围,不需要太多外界或多元的支持力量。但,大运河不成——摊开地图看看,几乎大部分地盘,都不是文物部门能说了算的。
2005年12月15日,从新华社刊登“运河三老”致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区)的公开信起,全国政协及政协委员、专家、媒体、沿岸城市,与文物主管部门一道,共同推动了这一轮的申遗行动。
以我自身参与的大运河申遗过程为例。到了2008年年初,申遗基本上进入国家主管部门管理的正式轨道,“我们”没事儿了。但随着价值发掘的深入,将来如何真实完整地保护大运河,让人们怎样来欣赏她,我不认为这是国家文物局的专长,这是我们传播人士的专长。于是,“大运河遗产小道”的理念和实践慢慢出现了。
中国青年报:“遗产小道”,意味着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吗?
齐欣:大运河遗产小道,是完全由社会力量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一个文化遗产传播产品,是将旅游、体验、运动等时尚要素集合的平台。“大运河遗产小道”有三条规定:一、必须为了体验遗产去走,行走路线在大运河两岸500米至1000米范围之内;二、必须步行或者骑行;三、强调遗产点的联通而非兴建,注重真实完整的保护。
这个理念提出后,率先去实现的是以大学生为主的社会群体。大家实地规划一段就命名一段,最新的成果出现在北京。大家一致同意,将白浮泉沿京密引水渠至积水潭的一段,命名为“罗哲文小道”,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开拓者为大运河申遗“扣动扳机的人”。
从“大运河遗产小道”开始,我们归纳出“遗产小道方法”,并立刻应用到了蜀道的申遗中;由“遗产小道方法”引申出了“文化遗产传播”概念和体系;文化遗产传播,又开始应用到传统村落保护……你看,大运河给了我们多么广阔的“身外价值”!
中国青年报: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作为社会力量,你们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齐欣:“我们”明白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敌人”是谁。
原来我们认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敌人”是开发商、贪婪的资本和农家乐式的旅游。但现在开始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对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停留在埋怨、幻想于等待中的自己!
我们当下社会正处于人类历史上难以循迹的快速发展期,多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但文化遗产,我认为会成为继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村、街”之后的另一道文化防线,甚至是最后一道防线。 这意味着,需要一个社会化的系统来挽救文化遗产。进一步说,文化遗产传承,其实就是文化信息价值转化为社会力的过程。这种社会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没有主动地去捡起来。
中国青年报:在参与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中,社会力量遇到过哪些现实难点?
齐欣:1972年签署“巴黎公约”时,人们还没意识到会出现中国大运河这么大规模的文化遗产。如今,这不仅是中国人的贡献,更是人类智慧发展的一个新脚印。
随着公众自我认知的演化,个体的奉献与分享行为正在形成合力。而且文物界也意识到,原来几个专家就能厘清的难题,现在百分之百地要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才能有最终的解答。这是一个新的转折机会。这需要文物圈再一次革自己的命。为了适应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要求,需要打破以前专业和小范围的局限。全新的格局一旦形成,社会力量的公益氛围会明显成为主流,青年人会突出地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力。
中国青年报:青年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能看到什么?
齐欣:文化遗产的价值,最重要的是要真实完整地传承给后代。那么,最先被吸引过来的,是满怀理想、愿意绽放青春的年轻人,而且是原来关注儿童、关注环保的那些年轻人。为啥?因为他们开始了解:文化遗产,就是另外一批失学的孩子,就是另外一片人文的大自然。
大运河申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是“文化遗产视角”。大学生是这个视角下各种课题的积极实践者。像“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城市——厦门”和“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大学”两个实践项目,全部都获得了省级社会实践奖。我坚信,有知识,愿意分享智慧并参与的年轻人,会很快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社会中坚力量。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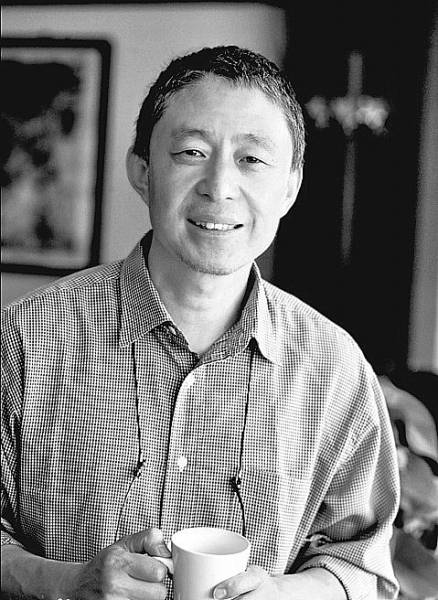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