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我觉得花儿是很平凡的东西。
学校的花坛里种着大批的木槿,小学时的照片多半会以木槿为背景,我在旁边傻笑。木槿的枝干挺拔,淡紫色的花朵排列得太过整齐,而且每朵都长得一模一样,像是手工课上用绢纸扎的假花——之前我看到木槿这个带着诗经的古雅韵味的名字时,有许多美好的想象,后来才知道它就是从前见过的那么家常的花朵,有略微的失望。但这花是可以吃的,花瓣入口有一种丝滑感和淡淡的甜味。初夏时校园里还有一种粉色的单瓣蔷薇开放,花朵单薄却香气袭人。它们长了很多年,枝蔓的规模已经很大,把花坛占得满满的,还要扩张开来。
其实孩子们很少会去摘蔷薇,花瓣太薄容易扯坏,香气也不平易,让人有一种眩晕的沉醉感。我们最喜欢摘的,是栀子花。谁家院子里若种着一棵大栀子是让人羡慕的,很多同学便会央求她摘几朵半开的带过来,教室里便弥漫着一股清幽香甜的气息。有的女孩子还在栀子花的花蒂上穿上棉线,挂在脖子上充当项链,走起路来一晃一晃地散发着幽香。老师们通常喜欢把含苞的栀子花插在办公桌上的水瓶里,等它慢慢开放,绿色的花苞绽开后是肥白可爱的,花瓣有种饱满的质感,过几天之后,又慢慢萎缩失掉水分,花心发了黑,香气也渐渐萎靡起来。
姥爷家满院子都是花,独独没有栀子。四季桂和茉莉的香气也很怡人,只是花朵太小,四季桂的白色花朵在绿叶的海洋中星星点点地点缀着,不起眼儿,茉莉是重瓣的,更精致些,所以才会被写进歌里传唱吧。姥爷有时候会让我摘一些茉莉和金银花,晾干了放在他自制的烟叶里——那样的烟叶装进旱烟袋里,入口时也许会有花朵的芬芳吧,我暗暗想。
姥爷的房间门口栽有五六种颜色的月季,像少女的脸庞般饱满。院门口还有一丛丛的鸡冠花,鲜艳的大红色,花朵绵密,摸上去像是一种上好的布艺。我曾经偷偷折下一朵鸡冠花,试图别在头上做头饰,被姥爷训斥了一顿。姥爷爱花如命,在他的心目中,花的地位似乎远超过我。而爷爷却宠我更多,我揪下他花盆里含苞的一串红,只为了吮吸里面的蜜汁,扔了一地红屑,他也一点儿不生气,还主动把门前的百合摘下来,做打卤面给我吃。
大妈家种着大丽花,那时候我们管它叫地瓜花,显得乡土,富有菜市场的气息,花朵硕大,花瓣重重叠叠,明艳照人,它把精力全用在了开出精致的花儿来,丝毫没有香气,我便无视它的存在,只有在记忆中闪回时,才觉得惊艳。
大妈所在的巷子里有几棵洋槐,花开的时候,会有外地来的养蜂人驻扎在附近,整条街便是花香混合着蜜蜂的嗡嗡声。附近的孩子们纷纷搬着凳子上树撸槐花吃,入口甜滋滋的,比木槿好吃得多,大人说生槐花吃多了会肿脸,可以用开水焯一下,做包子馅儿,只是做馅儿的时候已经完全辨别不出它原本是花儿了,并不比山苜楂的味道更好。我也并没有见过哪个孩子因为贪吃槐花肿过脸。
田野里常见一种粉色的花,走在山路上时我常折下一枝来玩,剥开它圆锥形种子的外皮,掏出种子来。后来才知道它有着很霸气的名字,叫王不留行,是康乃馨的近亲。很多年不曾在夏季去过家乡的田野,也就没再见过这种花。即便在网上看到它的照片,也能迅速联想起从前的某个夏日,干燥的土地上,蜥蜴在迅速爬行,一个孩子在山路上四处寻找可以在水泥墙面上写字以及适合做“抓石子”道具的石头,装在口袋里沉甸甸的,满满都是欢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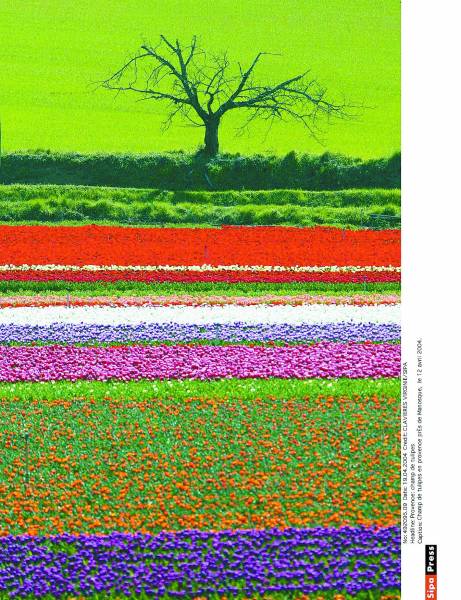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