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威发号施令、指点江山;而研究生则可能使用暗器,如同武侠小说里的“化功散”,伤人于无形
□学生就像导师种的一季庄稼,就算这一季种坏了,导师还有下一季收成
□如果一个导师给予学生的实验指导连续几次都不正确,导师在学生心中的威望就会急速下降
王桓(化名)在结束他8年的研究生生涯之际,写了8万字的长文回顾自己浸淫已久的这个“江湖”。
他感叹,课题组就好像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极度缺乏外部的监管与干预。就好像一个封建王国,遇到“开明君主”就国富民强,若是导师不甚开明、能力不强,就可能产生师生之间的“明争暗斗”。
导师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威发号施令、指点江山;而研究生则可能使用暗器,如同武侠小说里的“化功散”,伤人于无形,比如在毕业时故意保留自己多年积累的实验经验、技巧,不告诉导师和师弟师妹,让本该进行下去的实验处于停顿状态。
他把自己的感悟文章发在网络论坛上,引来一片附和声。
前不久,人大教授公开宣布与门下弟子断绝师生关系一事,又一次让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成为教育热点话题。现如今,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真的如王桓所言,像江湖般深不可测?
一旦涉及钱,“老板”就只是老板
尽管舆论屡屡批评如今研究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变为雇佣关系是一种异化,但现实中,“老板”这一用于导师身上的称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认可并接受。
郑梦(化名)在上海读研三,研一时,听师兄师姐称导师为老板,她还感到很不习惯,但在跟导师做了一年多实验后,她感慨道:“真的是老板!”
郑梦所在的研究院,各个实验室自负盈亏,郑梦的导师以做横向课题为主,通过为企业服务来挣钱。
郑梦目前的实验进展不太顺利,导师很不满意,直截了当地说:“实验室要赚钱,你要对实验室有贡献才行。”
郑梦说,“一旦涉及钱,‘老板’就只是老板。”郑梦有个同学做导师的污水处理项目,为了帮工厂解决技术问题,这个同学研二一年都待在这家工厂。
身为“老板”,有些导师对待学生毫不客气。
王桓的博士生导师批评学生时非常严厉,“根本不会顾及学生的面子,有时候就在人来人往的楼道里骂”。王桓的一个师妹初进实验室时被骂哭过好几次。
和职场上一样,如果遇到不喜欢的“老板”,研究生们也有自己的斗争方式:三言两语就能打消想要投到导师门下的本科生的积极性;想方设法尽早溜之大吉,比如,可以直博的,宁愿拿到硕士学位就走人。
郑梦研一时曾考虑过跟导师继续读博,但现在却打消了这个念头:“大部分实验都是在重复重复重复!”因为应用型研究的技术相对成熟,她做的研究其实没什么创新点。
不怕导师骂,就怕导师指错方向
难以与导师进行平等对话也是不少研究生的苦恼。做科研意见不一致是常有的事,王桓说,师生有分歧的时候,往往是导师靠自己的权威来一锤定音。
研三学生季珊(化名)在实验室里有点孤独。她听从老师的安排,独自开始研究一个新的方向——没有师兄师姐引路,这意味着,她要多花很多时间阅读文献、探索实验方法。做了两年实验后,导师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没有太大价值,便不再安排其他学生继续做这个方向。季珊便成了探索路上的先驱和先烈。
季珊常常觉得,自己就像导师种的一季庄稼,就算自己这一季种坏了,导师还有下一季收成,“一个学生发不了论文,对老师的影响不大,因为还有其他学生顶上来,但对这个学生来说,会直接影响到正常毕业。”
因为实验方向的问题,王桓和导师争辩过几次,结果都不欢而散。于是,王桓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一边做导师安排的内容,一边做自己设计的内容。当他拿出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持自己的研究方向时,导师也只能默许他继续做下去了。
不过,博士毕业后,王桓与导师之间的联系就很少了。
在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中,学生不服老师是最糟糕的情况。王桓说,如果一个导师给予学生的实验指导连续几次都不正确,导师在学生心中的威望就会急速下降。“只要老师能指导对,哪怕他对学生的态度再差、再怎么骂学生,学生也都能忍”。
“我们研究生一天到晚做实验,都没有怨言,只在乎有没有成果。”王桓说,“老师出资金,学生出力,如果能做出来,就是师生的共有成果。”
围绕论文的过招最激烈
“师生的共有成果”,往往体现为论文,而这也是师生矛盾的一大焦点。
首先,论文署名权常常让师生间心生芥蒂。
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大部分高校都有发表论文的要求,至少一篇。而按照目前通行的规定,只有导师有投稿权,即老师通过自己在期刊上注册的账号投递、发表出的论文才会被学校认可,如果是学生以自己的名义投论文,即便能成功发表,也不会被学校承认。而且,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也会严重影响学生在学术圈内的名誉——因为他破坏了默认的规则。
由老师当通讯作者、写论文的学生当第一作者,成了很多师生约定俗成的做法。通讯作者,通常是实验项目的负责人,提供实验设备、药品和资金;第一作者,是对论文贡献最大的人,一般是实验的直接操作者。
但也有老师会同时任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如果老师对学生的指导不多,就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在一些学术论坛上,关于导师在论文上署名的吐槽,屡见不鲜。
学生为了能如期毕业,希望尽早发论文,而有的导师则期待学生继续深入研究,“攒着发个大的”,于是冲突就来了。
王桓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读博时,王桓做出的实验数据已经足够发表论文,但是导师要求他在某个方向再做探索。他按照老师的设想又做了两个多月的实验,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最后只好按照原先的数据发表了论文。
“这其实有一定的赌博性质。”王桓说,如果老师判断准确,论文的档次能提高很多;如果判断失误,就只能白费工夫。但对科研来说,判断的准确率并没有保证,既要看老师的水平,也要靠运气。
面对“赶快发论文毕业”与“攒着发个大的”的冲突,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陶梅霞认为,如果学生还打算继续做科研,导师可以用科研精神来说服学生;但如果学生不同意,导师也只能尊重学生的意愿。
而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能否达到毕业要求,则是一些研究生与导师矛盾激化的根源。季珊说,研究生们在一起聊天时,会有人抱怨自己的导师“太有原则”——按照学校的要求,学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能够毕业了,但因为达不到导师的实验室标准,学生只好推迟毕业。
在陶梅霞看来,这是必须遵守的底线。她认为,导师带学生,就像树立一个品牌,“我得为我的品牌质量把好关”。如果带出的学生质量高,也会形成良性循环。
陶梅霞强调说,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论文数量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学生只发表了一篇质量非常高的论文,也会准许毕业。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事实上,论文问题也带给导师们极大压力。
陶梅霞曾带过一个博士生,这个学生已经读了4年,但论文甚至还没达到上海交大博士生预答辩的标准。陶梅霞认为其“学术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标准”,建议学生延迟毕业、继续做实验。不料,这个学生跑到她办公室里哭闹,还以跳楼相威胁。无奈之下,陶梅霞组织教授委员会为这位学生进行预答辩,结果“五六个评委老师也认为学术水平还不够”。后来学生服气了,延后了半年毕业。
“你是来做学术的,如果只要到老师办公室里哭闹、只要凑够4年就能毕业,这个学位就不值钱了。”陶梅霞说,如果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外审时的得分在该学院排在后10%,学生甚至可能需要延迟一年才能答辩。
类似的事情不少导师都经历过。有的导师怕学生出事,不得不降低要求,“放水”让学生毕业拿学位;有的导师实在无奈,只好一遍遍自己动手帮学生改论文,甚至重写。
而经历了“跳楼”事件后,陶梅霞能做的,就是在招生时更加谨慎。
导师和学生是一个共同体
虽然认为学生和导师之间有明争暗斗,但王桓也表示,多数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很多导师和研究生感情深厚。
王桓自己读硕士期间的导师就给了他很大自主权,让他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这让他觉得“读研很开心”。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关注高等教育领域多年。他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更像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老师只带一两个学生,师生之间关系紧密。
而自90年代以来,导师带学生做项目、给学生酬劳的现象越发普遍,尤其是在理工科。如果老师要求学生做项目、给钱又很少,就容易引发师生矛盾。这种现象在理工科更为常见,人文学科因为项目较少,师生之间的经济利益关联相对较少,关系也较为单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师说,如今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之所以矛盾多、摩擦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生不断扩招,一个导师有时一届就要招十几名学生,“现在研究生培养就像工厂流水线制造产品,师生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能不产生矛盾吗?”
“师生其实是一个共同体。”陶梅霞说,导师和学生需要相互扶持,才能彼此受益。
而作为学生,季珊对导师的期待很简单:“只希望导师能尽快回复邮件,不要总是再发短信提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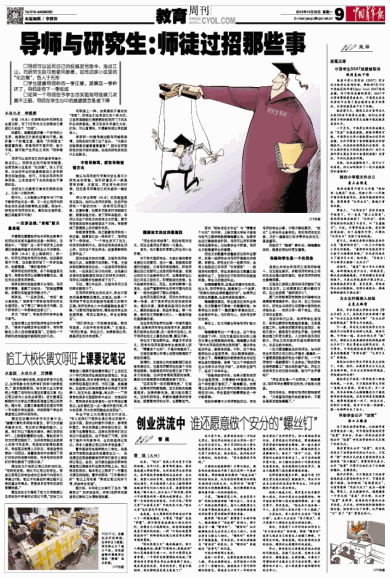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