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军旅作家高建国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作家出版社)面世了,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因涉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沙家浜》,甫一露面,即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捧书细读,才发现此书所涉已远远超越《沙家浜》之范畴。作为一部再现苏南烽火抗战史的纪实文学,其呈现手法也颇有新意。日前,本报记者对作者高建国进行了专访。
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么一部30多万字记录历史的大作品,你却选择从一颗小小的子弹切入,创作时是怎么考虑的?
高建国:这个问题提得蛮有意思。全篇之所以从子弹切入,我自己考虑,首先是结构上的需要。以“子弹”和“经典”两个要素作题目,本身带有悬念,比较吸引人,同时又构成了贯穿作品70多年历史纵深的一条明线。
与此相对应,作品还设置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转换的阶段性特征,构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大战略及推进战略实施,乃至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组织领导艺术地再现当年大战略制定实施这一暗线。我尝试让一明一暗两条线在作品中并行不悖,开合有致,使作品构成一种复式结构。
其次,我认为这有利于揭示和彰显作品的个性。一颗子弹引出一部红色经典,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有像以新四军老六团为基础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以下简称“江抗”)这样有鲜明的红军传承和基因、又以上海一带有文化的青年官兵为主体的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才能够创造和书写。
另外,这颗子弹有着很深的寓意和很强的象征意义,它来自“忠义救国军”的美械装备,却引发了红色经典《芦荡火种》和《沙家浜》的创作,使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横泾成为江南绿色名镇,而且经芦荡英雄血肉之躯几十年化育,已经成为主人公刘飞人格和精神的象征。
中国青年报记者: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选择重现这段历史?
高建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百万大裁军,原武汉军区机关和部队一部与济南军区合并。我一接触刚转隶的第20集团军部队,就发现这支部队与其他部队有两个迥然不同之处:同为离退休老干部,其他部队的老首长有的在家喂鸡种菜抱孙子,而这支部队的“老员外”们则乐此不疲地写书照相作报告;同样有着南征北战的光荣历史,这支部队与中国革命史上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有着更多割不断的联系:《东进序曲》《黄桥决战》《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红日》《战上海》,等等,都与其战斗历程密切相关。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就取材于第20军首任军长刘飞等36个伤病员坚守阳澄湖芦苇荡的独特斗争经历。1944年参加新四军的第20军文工团团长陈荣兰,转业去上海后还参与了《芦荡火种》的创作。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紧迫地认识到,在“江抗”老战士大都已经谢世的今天,曾经与创造过这段历史的老“江抗”有过交集、相对熟悉军史并能够以正确的历史观反映那段烽火路程的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责无旁贷地肩负起重述、再现、回放历史的责任,这是促使我动笔写这部作品的重要原因。
中国青年报记者:纪实文学是文学,但更要纪实,必须追求事实与真相。你把自己这部历史题材的作品定位为长篇纪实文学,那么在写作中,你是如何把握真实呈现与文学描述之间平衡的呢?
高建国: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和艺术魅力所在。而写7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还要延伸到北伐、土地革命战争等更为辽远的历史时空,大量、具体、翔实地掌握史料并作出恰当的判断与取舍,是非常困难的。
为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我首先要弄清读懂当时的时代环境,从国际国内的大背景和各种政治力量博弈中正确分析和认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为准确把握作品的基调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我特别注重借助可靠史料并做好去伪存真工作。由于年代久远,即使是亲历者的一些回忆也未必完全准确。如有的回忆录讲,周恩来1939年二三月间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同大家一起唱《新四军军歌》,实际上这首歌是周恩来离开皖南半年之后才创作出来的。这样的“穿越”是在借鉴史料中要认真注意的。
再次,发挥好历史“活化石”的作用。我请58年前为崔左夫创作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提供过素材的97岁的老首长施光华把关,结果老首长提出,稿中提到的一位“烈士”他解放后在上海见到过,这让我避免了一起差错。
寻访重要遗址印证和感受当年的重大事件和战斗,对我的写作也很有帮助。在采访和写作中,我还注意发挥“江抗”老前辈子女的作用,从他们那里采访到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当然,依靠上级主管部门和军地权威专家把关,也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这部作品纵贯70年的历史时空,其中涉及若干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创作中你是怎样把握史料与文学关系的?
高建国:这个问题触及作品构建中一个绕不过去和不可回避的特殊矛盾。由于作品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其内容仅靠单一的纯文学描述难以承载,宏大叙事势必要使用大量重要而确凿的史料。作品展现了“江抗”在苏南东路地区两度勃兴艰难竭蹶的历史进程,虽不是在编著“江抗”战史,但作为较为全面记述“江抗”发展历程的大型纪实文学作品,应成为言之凿凿的“江抗”信史和外传。所以,我要求自己的作品必须“史料为基”。
另外,在描述国际国内局势、重大战略形成和发展过程时,精当有力的政论和夹叙夹议的写法必不可少,有的章节甚至出现了“思想大于形象”这一逸出文学常规的现象。这是由作品题材的特质所规定的。我觉得,这种厚重历史题材的写作,在基调和风格的把握上,应坚持文学、史实和思想三金铸一。
中国青年报记者:历史是过去的今天,今天是历史的延伸,正因为历史与现实有如此紧密的关联,人们才常说要以史为镜。你期待读者在你所呈现的这段历史镜子中可以得到什么?
高建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回首70多年前那场付出巨大民族牺牲的战争,很重要的就是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在向历史和传统致敬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从“江抗”在东路的两度勃兴和经历的成败利钝可以看出,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正确的战略判断与指导,对于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来说至关重要。
同时,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和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决定因素。没有刘飞、夏光这些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红军钢铁战士的核心领导作用,伤病员就不可能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中顽强生存。他们的坚守,保证了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红旗不倒。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了你这部作品才发现,《沙家浜》这部红色经典的前生不仅起源于沪剧《芦荡火种》,更可追溯到1957年第20军59师文化科副科长崔左夫的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可真不容易。
高建国:确实是这样,在这部作品采访、写作过程中,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任何经得起历史检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传诸后世的优秀文艺作品,都是深刻体察和准确反映那个时代特有精神的产物。《芦荡火种》和《沙家浜》的创作道路,就是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革命文艺创作的方向。在亿万人民同心共书中国梦的新的历史时期,要创作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伟大祖国、无愧于伟大人民的传世佳作,就必须按照习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为人民立传,为时代写照,才能有效解决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记者:作为一部记录历史的作品,大背景描写、宏观叙事是必不可少的,你的作品中也不乏此表现手法。但在细读时,我也注意到你同时也非常注重微观观察、故事呈现、细节叙述,在创作中,你是如何考虑二者之间平衡的呢?
高建国:这部作品展现了红色经典创意萌发和化茧成蝶的经过,其中必然伴随着“江抗”成长壮大的历史,也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大纵深上勾勒我党制定实施抗日游击战争大战略的过程,因而,全景式宏观叙事是内在需求。创作中,我特别注意把握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因为没有宏观,看不清背景和走势;没有微观,又难以打动人感染人。我的做法是,首先,从总体上搭建好叙事框架的四梁八柱,使历史真实与叙事逻辑统一起来。其次,注意撷取一些生动耐读、有思想张力的历史细节,作为作品的血肉点缀其间。同时,叙事中从结构到行文,我都注意要有一点故事性,中国人是吃故事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写作中你遇到过困难吗?如果遇到过,那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是怎样克服的?
高建国:写作中当然遇到很多困难,如一些记述历史事件的文字语焉不详,一些历史片断的资料几近空白,一些历史人物评价难以把握,等等。但最大的困难,还是如何处理遵循文学创作规律与全面客观反映苏南东路地区抗战两次勃兴和新四军发展历程的关系问题。
创作之初,我写了一篇题为《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的小中篇,基本讲清了《沙家浜》这部红色经典的前世今生,但稿子显得比较平。另起炉灶时,我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构筑敌后游击战争大战略切入,用芦荡英雄刘飞胸中的一颗子弹,把构筑实施战略与艺术再现战略贯穿起来,力求使新四军老六团东进作战的战术行动彰显宏大的战略背景,这样也使子弹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个构思虽然对那段历史的反观和描述有了新的视角,但任过“江抗”政治部主任和旅团主官的刘飞毕竟只是一个中高级领导干部,再现波澜壮阔的东路抗战史必须要写大将,必须要塑造好老六团东进的决策者陈毅和“江抗”与新“江抗”主要领导人叶飞、谭震林等叱咤风云的抗日名将的形象。既要着力刻画好刘飞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又要着眼历史真实从全局上为东路抗日英雄群体传神写照,这种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处理把握,让我颇费心思,自认为也颇下了一番工夫。当然,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还有待读者检验。
本报记者 李雪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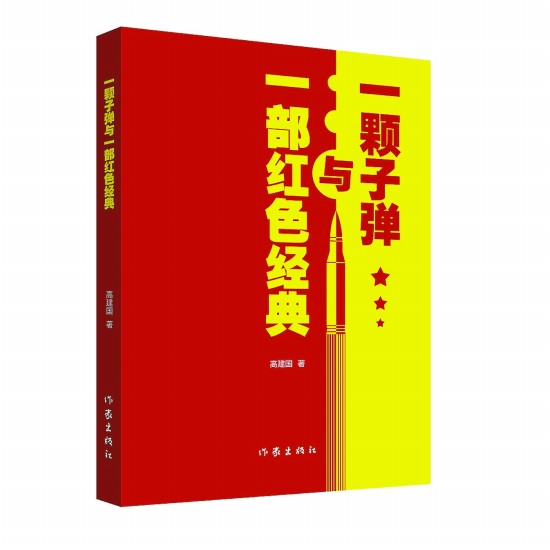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