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阵阵眩晕,5岁的美国小姑娘安妮·戈茨丹克突然剧烈呕吐起来。她们一家刚刚结束了在一个墨西哥小镇的旅行,正驱车返乡。到了下午,她左腿犹如刀割,甚至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坐起来。
“我怀疑这是小儿麻痹症。”家庭医生奥利佛对焦急惊惧的父母说。这似乎不可能。这一年春天,全美有12万名儿童接种了卡特实验室的脊髓灰质疫苗。安妮就是其中一个。
在安妮的身体里,疫苗的病毒未被按计划灭活。它们潜藏在本应催生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的抗原物质里,游走,爆发。安妮的右腿永久瘫痪了。在以后的人生中,她只能依靠拐杖和轮椅生存,还需要不断移除因为瘫痪而坏死的组织。
她遇上的,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故之一。
那是1955年春天。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生物制品控制实验室里,电话铃声不断响起。这批脊髓灰质疫苗令4万接种者染病,连带传染了1万人。最终,164人永久瘫痪,5人死亡。
这一事故使不少美国人拒绝注射疫苗。
消耗的信任怎么修复?这个国家花了60年做这件事。
这场瘟疫是人为的
事故发生两年后,安妮坐上了原告席,宽松的红色毛衣遮掩着她残疾的身体。这是此后极大影响疫苗管理流程的戈茨丹克诉卡特实验室一案。
她代表了两年来整个美国的呼声:如果我们不知道灾害是如何发生的,那么它必将再次发生。
安妮所遭遇的病痛,并非俗称为“恶魔抽签”的合格疫苗引发的严重不良反应,也不是与疫苗不相干的偶合反应。
事实上,事件爆发后不到一个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身——流行病信息服务部(EIS)——就展开了针对卡特事故的调查。
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这支团队收集起这年春天所有小儿麻痹症病例,还将感染情况与前五个春天的情况进行对比。
病人信息的确定是尤为重要的:病人年纪多大、住哪儿、有什么症状;有没有接受疫苗接种,有没有接触过接种疫苗的人,具体是哪一批疫苗;此人体内能否被检测出脊髓灰质病毒,具体是哪种。
这场灾害的绵延版图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他们眼前。
所有发病者接种的疫苗都来自同一家公司:位于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
后来回顾,危机早在一开始就有迹象显露。
不止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根据当时的法律,政府文件是生产疫苗的唯一参照。医学家索尔克的疫苗生产注意事项有55页长,而实验室分发给各个生产商的注意事项只有5页长,标题就是“最低标准”。
监管的实际效率值得怀疑。法律并不强制要求制造商告知政府哪一批疫苗没有通过安全测试。这样,只要制造商不提交有问题的疫苗植株,政府就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
疫苗执照的审核也被一种仓促的热情裹挟了。评估会在密歇根州安娜堡一间香烟味儿呛人的酒店房间里举行。直到下午快3点钟,人才全部到齐。没有人提前看过审批报告,而他们被要求傍晚拿出决策来。
五家实验室的疫苗执照都审核通过。当天晚上,全国各地的诊所陆续收到装有疫苗的纸盒,上面标注着“加急”。
随后,在自己家二层的阳光房里,安妮完成了脊髓灰质疫苗接种。这种由医学家索尔克研发的疫苗刚刚获得接种执照。在大学工作的父母毫不犹豫地选择为女儿做好准备。小姑娘并不知道命运已经在那一刻转折,心里还惦念着长大后做个兽医的梦想。
“这场瘟疫是人为的。”后来,传染病学家保罗奥菲特在《卡特事故:世界上第一例脊髓灰质疫苗如何导致疫苗恐慌》里,给这段往事写下这样的标题。
事故中另一个重要角色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当时的名称是“美国海军医疗服务机构卫生实验室”)。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就曾发生过天花疫苗被污染的事故。事后追溯源头,人们发现为疫苗提供血清的名叫“吉姆”的马,早已感染了破伤风。这件事让美国上下意识到,必须引入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对疫苗生产全程进行监督管理。
1902年7月,《生物制品控制法》由议会决议生效。从这时起,包括疫苗在内,“一切抵御疾病”的生物制剂联邦政府有权统一监管。也就是说,国家卫生研究院将监管与此有关的一切。
但实际操作层面,这片宏大的蓝图盖在一个45人的小机构头上。
生物制品控制实验室肩负着测试200种不同的产品和超过150家机构的责任。尽管成员都是医生或科学家,但在那个残酷的春天,这里没有一个人正经学习过脊髓灰质病毒。
如今在美国,疫苗不良反应的受害者只需要填写表格就能进入索赔程序
官司如何定案,陪审团整整讨论了28天,安妮大多数时候都和妈妈在休息室里耐心地等待着。最终,她们获得14.73万美元的巨额赔款。陪审团裁定,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是负责监管的国家卫生研究院。而卡特实验室,虽然在疫苗的研制中并无失职,仍需要对疫苗的不良反应负责。
此后再有疫苗不良反应发生,受害者都可以援引这次的判决要求疫苗生产企业赔偿,而无需证明它在生产过程中失职。
从此,“无过错责任”即“严格产品责任制度”被建立起来。更多疫苗受害者的索赔之门被这场诉讼打开。
此外,一个严格的疫苗监管体系被建立起来。
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共同建立了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不论是医护人员、疫苗生产者还是疫苗接种者,不需要任何知识门槛,随时能向这一系统报告疫苗接种不良事件。通过这一系统,还能随时查询问题疫苗的同批次药品。
卡特事故爆发后,曾有不少大受惊吓的美国家长拒绝给孩子注射疫苗。这似乎是平常百姓应对天降大祸的通常反应。20世纪70年代,伦敦爆发百日咳疫苗不良反应,英国接种率狂降了一半;日本的反应则更严重,不到十分之一的人选择接受疫苗接种。
这些抵制接种行动使一些传染病死灰复燃,在英国,每10万人中突发百日咳发病的人数由1个人上升为200个人。日本则爆发出现1.3万多病例。
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免疫接种每年能避免200万至300万人死亡,是抵御传染疾病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向病毒冲击的“回火(backfire)”击中了自己,有媒体这么形容卡特事故。
既以火种抵御黑暗侵袭,就有被灼伤的风险。疫苗从生产到最终注射,太多环节可能出错了。这样的风险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或时代。
1902年,印度,107人接种了被破伤风杆菌污染的鼠疫疫苗,19人死亡。
1928年,澳大利亚,白喉疫苗被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12名接种儿童死于败血症,6名病重。
20世纪30年代,德国,有毒性的结核杆菌与卡介苗被保存在同一个实验室, 251名婴儿误服,72名死亡,死者中只有一位撑过了1周岁。
……
在1957年因卡特实验室对安妮的巨额赔偿而欢欣鼓舞的公众没有想到,该裁决增加了药物企业潜在的赔偿责任,他们不愿意在疫苗生产上投入了。第二年,流感疫苗的短缺危机爆发。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国会1986年通过《国家儿童疫苗接种伤害法案》。这为儿童时期接种疫苗而致伤的人们获得救济确立了法律依据。疫苗生产企业的压力减少了。
两年后,“国际疫苗伤害赔偿计划(VICP)”通过并实施,为受害者提供简捷的索赔程序。
如今在美国,疫苗不良反应的受害者只需要填写表格就能进入索赔程序,并不需要走法律程序。用于赔偿的信托资金主要来自疫苗生产企业根据销售所得缴纳的基金,以及政府拨款和捐款。企业的赔偿风险被分散了,受害者也避免了旷日持久的官司。
至今,VICP已经覆盖了所有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推荐的所有对儿童常规实施的疫苗。截至2006年,受害者申请案例已经达到11947例,经审查获得救济的有2017例,支付总金额达到16.2亿美元。
这种医疗上的悲剧或许无法避免,但绝不能漠然接受
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针对疫苗不良反应受害者都有各自的补偿计划。
与美国市场化运行的救济金补偿方式不同,英国和日本采取的是行政补给模式。在1979年英国《疫苗损害补偿法》和1976年日本《预防接种法》保障下,资金来自国家拨款,补偿计划涵盖常用疫苗。申请人只需填表即可开始索赔程序。
瑞典则在1962年通过《全国保险法》,展开责任保险补偿模式。几乎所有瑞典制药公司和进口商都成为了药品保险协会的成员。
1972年,美国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CBER)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分离出来。在它的主导下,各个环节都被量化监管起来。以储存为例,疫苗的装运和到货的时间间隔,日常储存冷藏室和冷冻室的温度都有明文规定。冰箱中被要求放置大瓶装的水,以减少开关门对箱内温度的影响。储存场所负责人还要制定应急预案,应对突然断电或者机械故障。
距离卡特事故已过去60年。如今,美国疫苗获得批准需要整整一年,支持材料足足有6000页。
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下,一支疫苗安全团队随时待命作出快速反应。市场上任何疫苗一旦被认定对公众有实质危险,就会被责令召回或下架。
与此同时,任何违规操作都可能触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检查机制,令疫苗生产商付出高昂的代价。
疫苗事故导致的残疾,击碎了安妮的兽医梦。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她利用补偿款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教授。如今,她和丈夫女儿居住在一间满是书架的房子里,养着两只宠物狗、4只猫和一条蛇。她幸存了下来,与命运的错误缠斗,追上了生活。
然而,风险并没有消失。下一个安妮还在这世界某处沉默着,带着对未来的幻想。在自己书籍的结尾,奥菲特写道:“与杀害我们孩子的疾病抗争,在某种程度上像一场战争。当我们还击,无辜的人有时候会被误伤。这种医疗悲剧或许无法避免,但绝不能漠然接受。”
正如学者所预言的那样,2013年底,“高温疫苗事件”同样在公共卫生事业已经高度发达的香港发生。香港东华医院一个储存疫苗的冰箱达到了10摄氏度,比指定温度高了2到8摄氏度。
只是,这一次,没有多少恐慌,也并没有伤亡。在例行检查中发现问题后,院方销毁了冰箱中剩余的30多支疫苗,一个个找到了此前在这里接种流感疫苗的116人,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的7人以及另外4位接种乙型肝炎疫苗的市民。一场本可能酿成灾祸的事故,在透明的信息面前消弭于无形。
本报记者 王梦影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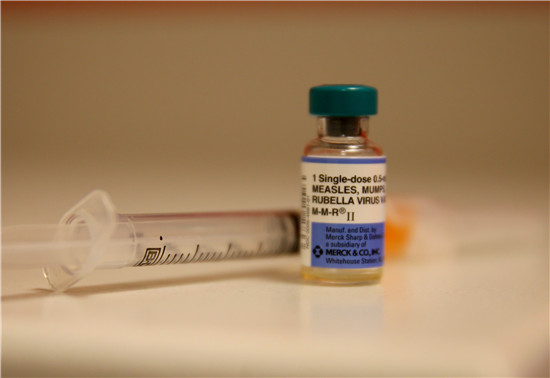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