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出生时是个健康的婴儿,3岁时不幸罹患脑膜炎,导致癫痫,智力和个性变得有些“古怪”。但他十分热爱音乐,听过的旋律马上就能唱出来。如果说有人的记忆像照相机,马丁的记忆则如留声机。当奥利弗·萨克斯在养老院遇到他时,已经是老人的马丁说,自己记得2000出以上的歌剧,不只是旋律、乐器,还有所有的歌词。然而除去音乐,他的脑袋里几乎空无一物,连2加2等于几都无法计算。
这是美国神经科学家、科普作家奥利弗·萨克斯在《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一书中讲的故事。作为《纽约客》等杂志的常驻专栏作家,他所讲的故事都是与神经认知和心理认知有关的真实案例,而且往往只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却不提供解决方案,可以理解为想给读者更多空间,也可能是人的大脑实在太奇妙。
这是一本讲人与音乐的书,确切一些,是讲病人与音乐。叔本华说:“音乐表达的是生活中最完美的精髓。”人类这个物种的特征不只是语言,通过音乐来认知自我是人类文化中非常根本的一部分。而这本书,将刷新我们对于音乐与大脑关系的认知。
弗里德曼医生车祸后不久,发现自己再也不喜欢听音乐了。而在此之前,音乐是他几十年来的精神食粮。
作曲家托克5岁开始学钢琴,有一天他对老师说:“我喜欢蓝色的那首。”老师大惑不解,托克也觉得很奇怪,每个调明明都有颜色,其他人看不见吗?
19世纪的牛津音乐教授乌斯利爵士音乐天赋绝佳,他在5岁的时候说:“爸爸打喷嚏的音是G,风吹的音是D,家里钟响的那两个音是B小调。”
一位老妇人的左腿动了手术,虽然一切很顺利,但腿还是动不了。然而,就在她听爱尔兰吉格舞曲的时候,那条动过手术的腿,居然会跟着打拍子。
这些堪称电影桥段的故事都是萨克斯工作手记的文学化表述。而对中国读者来说,有一个故事颇有普遍性——关于“神曲”的入侵。
有时候,一段乐曲接连几天、夜以继日地不断在脑海中循环播放,它通常是电影或电视剧主题曲、广告曲、广场舞配乐……萨克斯的一个朋友尼克就曾被一首歌缠上过,那是一部喜剧电视剧《凡夫俗妻妙宝贝》的主题曲《爱与婚姻》,只听了一遍,就在脑子里日夜“播放”了10天之久,无处可逃。
萨克斯写道:“在我们被一段乐曲或广告歌纠缠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和神经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音乐具有什么样的特性,才会变得这么‘危险’?”
一种解释是,我们在建构视觉世界的时候是主动的,会根据个人喜好而有所取舍,但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已经谱写好的。尽管对同一段音乐,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诠释和感觉,但乐曲的基本特质,比如速度、节奏、旋律、音色等,是固定的。正是因为这种精确性,每个音符就像复刻在我们大脑里一样,让我们特别容易受音乐感染,甚至变得病态。当然,“神曲”本身故意用不断反复的段落来加深人们的印象,这往往是一首神曲中最具“魔性”的部分。
当人类祖先第一次用骨头吹出声音,或者用木棒敲出节奏,音乐就开始钻入人类的脑中。但“神曲”的入侵,似乎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事。
对此,萨克斯说,曾经音乐要在教堂或者音乐厅才能听到,但随着录音机、电视机、iPod等电子设备的普及,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音乐,甚至被震耳欲聋的音乐淹没。大脑负担过重,难免会有不良后果。“动听的音乐也许不只是可做牙膏广告歌,还可能对我们的神经产生致命的吸引力”。
不久前,国内引进出版了包括《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在内的萨克斯的“探索者”系列丛书。其中,《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的第一章,一位歌唱家皮博士大脑视觉区长了一个肿瘤,导致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严重受损,只有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尚存,于是当他起身找帽子时,伸手就抓住了妻子的头。《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一书中,画家艾先生由于遭遇车祸而受到脑损伤,变成了彻底的色盲,但对黑白二色和各种灰度的直觉能力变得异常敏锐。
萨克斯希望通过记录一个个不可思议的个体,改变一代人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认知,获得超越现有生命的可能。他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要寻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也以自己的方式死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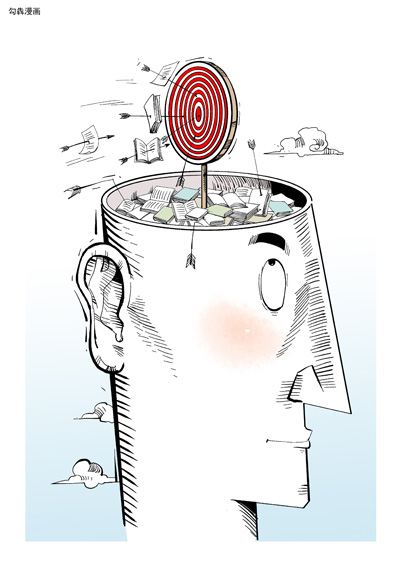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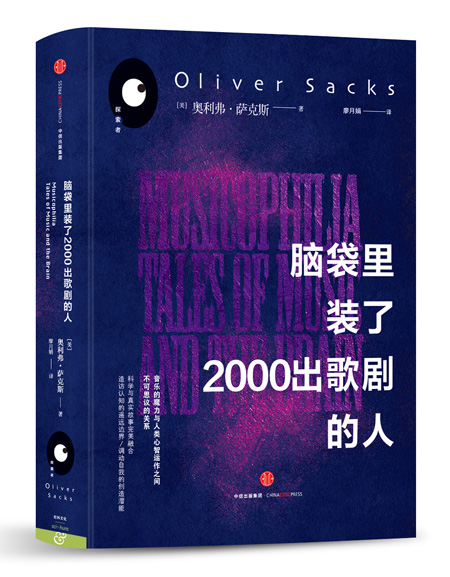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