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
视频编导:孙亚男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韡薇
近200棵胡杨长成四五人高,远远望去,密密麻麻一片金色。吴向荣选了最茂盛的几棵拍下来,配了句描述——“这里不是额济纳,是腾格里锁边林基地。”
在朋友圈发下这条状态时,吴向荣已经在沙漠里种树14年。
这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阿拉善,2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分布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这三大沙漠,土地荒漠化面积高达93.5%。每逢春天,沙尘暴常突袭而至。
吴向荣和他的团队就住在腾格里沙漠东缘。白天头顶烈日,拎着铁锹、背上树苗出门,晚上回到仅有床、桌椅的屋子凑合休息,就在宿舍、植树基地和沙漠种植区这三点一线来回跑,每天相互陪伴的只有7个人。
就是这7个人,造起了长20公里、宽500米~2000米的防沙治沙灌木锁边林,将一直向东肆虐、企图越过贺兰山脉的沙漠紧紧地拦截下来。
1997年,在日本留学的吴向荣,带着他寄宿家庭的主人、米店老板大俊夫和另一位日本人回到家乡阿拉善,正赶上当地最干旱的时期。
走在牧区,大俊夫看见满山的羊群,却不见一丁点儿绿草,十分疑惑:“难道阿拉善的羊都是吃石头长大的?你们为什么不种树?”
在日本友人看来,沙漠扩张不仅仅是阿拉善和中国的问题,也是日本和全世界的问题。回到日本,他们成立了世界沙漠绿化协会NGO组织,争取日本官方和民间的援助。次年,吴向荣开始向日本外务省申请项目资金。
2003年,吴向荣本科毕业,回到了曾想逃离的家乡。读小学的时候,频繁的沙尘暴给过放学回家的吴向荣 “突袭”,这让他对沙漠“充满了恐惧”。
可这个害怕沙尘的人,一回家乡却直接搬进了荒漠。第一批树苗到位后,他和团队从早到晚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天黑了,就在树旁边挖坑睡觉,一干就是几个月。
没水、没电、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跟不上,最初种植的小树,在纯粹“靠天吃饭”的方式下大量死亡,这种方式被验证行不通。怎样种树才能最有效地治沙?吴向荣一直在思索。
2005年,在给当地政府的报告中,他首次提出了“锁边”的概念——沿着沙漠的边缘植树,造起“绿色围墙”抵抗沙漠肆意扩散。他们一年年地制定计划,从公路的周围开始,打造起一条细长的防护带,先完成目标的长度,再慢慢地拓宽。
事实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为培育“绿色屏障”探索了几十年。吴向荣的父亲吴精忠曾担任阿拉善盟主管农牧林业的副盟长,多年来一心想治沙。小时候,父亲带吴向荣体验过几次“飞播造林”。坐在农用飞机上,脚用力来回下踩,飞机的底部就飘出长长一串种子落在沙漠里。几乎年年播种,可长成大树的寥寥无几。
“每年播完,遇上雨,才有生长的希望。长出来了,羊又给吃掉了,再怎么播也没有效果。”吴向荣觉得痛心。
阿拉善每年降雨量只有100多毫米,但蒸发量却高达3000多毫米,针对这种情况,吴向荣大胆地提出采用滴灌,当时团队的人都认为这“不可想象”。
“原来滴灌只有在农田有水井的情况下才会用,这技术用来造林,现实吗?没有水井我们就用运水车加压,后来一试果然可以。”滴灌建成后,浇完1000亩地,只要一个人花一周时间,而在过去,管道浇灌要团队所有人齐心协力,一个月可能都搞不完。
有一年,买来的苗木带有根腐病,这些患病的树苗仅从外表看并没什么异样。2年的栽培后,吴向荣和团队看着它们成林,又大面积地死掉。为了保证质量,他下定决心以后自己育苗,不久,项目区有了专门的育苗地。
“我们在腾格里沙漠14年种了20公里,等于1年也就是1公里多点儿,整个腾格里沙漠少说也有600公里,要按我们这个速度,最少还要再种500年”,他玩笑似地说道。“过去我们总想着要种多大面积,不考虑3年以后、5年以后能不能维护得了。我们到底能种多少,能管多少,能管好多少?”
有一年冬天,在日本,吴向荣发现短短的两个月里,专业人员对门口上百年的大树修剪了五六次,这让他意识到维护的重要性。回到阿拉善,他和团队随即制定了修剪计划。
他希望将环境保护的种子种进更多人的心里,发动更大的力量让种树成为一种自觉的活动,“不仅要种树,还要‘植心’。荒漠化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荒漠化,这是我父亲以前常和我说的话。”
彼时,阿拉善盟正实施“转移发展战略”,禁止牧民从事传统的放牧业。但对当地牧民来讲,要他们撇下习惯转而种树简直是难上加难,这一度让吴向荣“非常头疼”。
“我们拉修路的砂石料经过牧民区,那一个区域的十来户人家谁都可以出来拦你,只要在门口立个牌子,经过就得给钱。”
吴向荣想出了办法——通过给牧民发补助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蒙古族牧民格日勒图一家率先被说服,与吴向荣建立了合作。如今,格日勒图家周围的200多亩地被绿色填满,其他的几户牧民,也开始慢慢地尝试起来。
在这片20公里长的锁边绿带里,吴向荣最喜欢一号井附近的一棵沙枣树。这是他和一位当地的小学生一起种下的。
最初的援助期,不少日本志愿者都期望能够实地走入这片沙漠。每年,吴向荣统计好志愿者的名单,再去镇上找当地的小学,凑够对子建立“认领”关系,让这些日本志愿者能够短暂进入阿拉善的小学生家中同吃同住,再一起到基地体验植树。
“那会儿想把学生从学校里带出来,要费很大功夫。为了搞环境教育,我们给小学生租车,给带队老师发补贴,和校长喝酒喝成了好朋友,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学生给‘骗’到沙漠里。”说着,吴向荣嘿嘿一笑。
往往来了之后,学生们都说好。“当时浇树得从很远的地方提水,走一路鞋都湿透了,但大家都特别开心。”
经过吴向荣的牵线搭桥,最多的一年,结成的对子中日家庭就有将近40对。这些日本志愿者中,最小的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最年长的是近80高龄的老夫妇。前不久,吴向荣惊讶地发现,曾经参与活动、已大学毕业的阿拉善男孩,去日本游玩时又住到了当年来访的日本志愿者家中。
迄今为止,这个项目示范区共动员了8000多名中小学生、近5000名志愿者,参与环保教育宣传活动。他们也接待了近千名国际志愿者,组织了家庭结队和互访等国际交流活动,与国内外多所大学、科研机构携手开展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技术合作项目。
在团队里,42岁的吴向荣种树时间最早,年龄却最小。算下来,7个人的平均年龄差不多50岁出头。年复一年驻守在沙漠,吴向荣不担心生活单调,只担心留不住人。
在阿拉善,到镇上当公务员是当地炙手可热的工作。这些年来,光吴向荣团队里的年轻人就考出去了7个。日本援助时期,每一次中日关系紧张,都给这个种树项目带来不小的波动,日方会停止发放资金。最严重的一次,团队半年发不出工资,那一年,他们流失了4个年轻人。但吴向荣没因此放缓种树的脚步。
2015年,中国绿化基金会“百万森林计划”开始对吴向荣的团队发起支持。吴向荣感觉,他的项目更加稳固了,也逐渐在全国发出了声音。
一些青年开始“主动请缨”。年轻姑娘小何在网上看到吴向荣的示范区项目,自己找到了吴向荣。3个月的志愿服务时间过去,本要结束工作的小何突然改了主意:“我要留在这儿一辈子植树造林,治理沙漠!”
在团队眼中,吴向荣挺好相处,但这个外表斯文的人在某些问题上却“较真儿”得很。
“种树一点儿也不难,但用心种树挺难。”吴向荣叹了口气。“我们总以为拿把锹,挖个坑,放棵苗,添桶水,加点土,浇点水就是种树了。实际上,在哪儿种、种什么、怎么种、怎么管、怎么保存,这整个体系的建立才是大学问。”他严肃地说。
吴向荣希望能够与这片沙漠“握手言和”。“不是‘人定胜天’,不是和沙漠宣战,也不是用绿洲逼走沙漠。而是在这片土地上寻找沙漠和绿洲的最大公约数,保证生态和谐。”
这些年,吴向荣带着团队种过胡杨、梭梭、沙拐枣、酸枣,也种过花棒、沙棘等等。他发现大些的灌木“既好养又足够抵挡风沙”,他种出的花棒成活率已经能达到90%以上。而实际上,在阿拉善,不少地方的树木成活率只有50%左右。
如果没种树,吴向荣觉得自己很可能会留在日本,像多数昔日的同学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撰写报告,或者干脆下海经商。最初来到沙漠,他甚至想在阿拉善建立另一个拉斯维加斯。
一年年过去,赌城的梦想逐渐模糊,吴向荣在种树的路上越走越远。
十几年前,吴向荣在火车上邂逅了现在的妻子,来来回回的书信把这个陕北姑娘“骗”到了日本。没多久,他就回国治沙了。只有到了年底,忙完了一年的播种、管护、育苗、采种、冬灌,做好第二年的计划,他才能舒一口气,前往日本和家人短期团聚。
种到什么时候才满意呢?吴向荣觉得“没个头”。“还有更多技术可以开发,我们在不断尝试,也可能不断失败,这体现在造林上就有点儿麻烦,失败了,就要等下一年重新再来。”
在当地多数人眼里,种树是最原始也最土的差事。但现在每当介绍起自己,吴向荣都非要加上一句“就是个种树的”。
前几年,有几家公司先后向吴向荣抛出“橄榄枝”,劝他“多赚钱,直接捐助公益难道不比自己亲自种树力量大”,他没考虑几天,又接着拿起了铁锹继续之前的工作。“我不想等别人实施,我要自己真实地认识到我们为什么种树、怎么更好地种树。”
在搭档老王和很多其他人的眼中,植树锁边林的工作非吴向荣不可。“种树谁都能做,但这些想法和理论,除了他没第二个人说得出。”
有件小事一直印在吴向荣心里。种树第3年,项目区的沙拐枣刚刚长成树林,发现了一种专吃花果的虫子。为了让树存活,他们喷上了农药。
没想到,这里仅有的一只喜鹊却因此盯上了吴向荣。一天,喜鹊瞄准他办公室的玻璃窗死命地撞击,“嘭”一声倒在地上又“嗖”地飞起,来回反复直到彻底动弹不得。吴向荣盯着喜鹊的尸体看了很久,此后,项目区禁止使用农药。
在吴向荣团队不久前完成的植被调查报告里,这个项目区拥有的植物种类已达到120多种。曾经向他“寻仇”的喜鹊,有时一个傍晚就飞来几千只。他们还看到狐狸、獾猪、黄鼠狼、沙鸡,隼和鹰也在这片小绿洲上空飞翔。“最大公约数”绿洲,正在阿拉善的一角,缓缓延伸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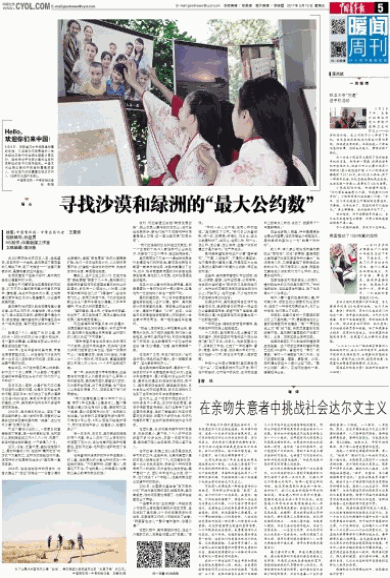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