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年前后,“奢侈”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在启蒙时代的道德判断中自我申辩。在《早期启蒙运动关于商业和奢侈的争论》中,伊斯特万·洪特呈现了一场关于“奢侈”的长篇辩论,结论无非两种:或无碍,或有害。如休谟所言,奢侈是“被看作有益无害还是该遭谴责”,“要视时代、国家或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同一时期的法国文人费奈隆和梅隆,他们关于奢侈的看法便截然相反。
费奈隆以古代小型共和国历史为原型描述了三段式奢侈史——奢侈产生之前的公社、奢侈而好战的国家、奢侈消除后的社会,以此来坚定其反对奢侈、崇尚节俭的观念,他可能更担心路易十四的法国堕入古罗马的结局;而梅隆的奢侈理论却从经济生活层面揭示了从绝对必需品、生活便利品到奢侈品的演进过程,认为“在充分的民主制国家”,奢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之一。
从本质上讲,奢侈无非是人的各种感官享受得到更好满足而已,但一直以来,它都自带政治、经济和伦理色彩。与奢侈相关相对的一长串词组,是诸如邪恶/美德、不公/平等、腐败/清廉、虚浮/荣誉之类,这些充斥着道德判断的词语直接融入18世纪欧洲语境下重农学派和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
如梅隆所做的那样,在驳斥重商主义的经济管制传统时,伏尔泰以及重农学派都对奢侈和自由贸易给予肯定,并解释了为什么自由贸易会带来更好、更安全的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亚当·斯密肯定重农学派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真谛。尽管斯密批判重农学派,但作为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他并不比重农学派走得更远;所不同的,在于二者对财富创造方式以及国家或立法者角色的认识。
作为重农学派的主要人物,魁奈希望政府鼓励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民创造财富,这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因为每个人不仅能从经济上受益,政治上也能增进个人自由。而政府的任务是“加以协调,在必要情况下强制推行社会的共同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其途径便是“不可分割的国家主权者”,于是,这位“主权者”既要求“绝对性和有效性”,“又要实行干预的最小化以便经济机器不受阻碍地运行”。这一明显的悖论构成了“合法专制”概念的精髓,因而,蒂姆·霍赫斯特拉塞尔的《重农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治》认为,应对重农学派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广泛的、综合的考察,他看到重农主义者们对“在一个‘等级社会’的环境里,什么样的制度既是真正的经济个人主义所需要的,同时又能维护社会和谐这个问题有共同的真知灼见”;但批评者也指出,按照重农学派的理论设计,其对道德正义的关心却被忽略了。
与绝对主义的法国政治经济学不同,18世纪的苏格兰学派有着更广阔的领域。在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关于政治家和立法者科学的一个分支”,而《国富论》最初只是被当作自然法理学这一大框架中的一部分。不同于法国同行,斯密认为立法者的作用在司法、国防、教育和公共事业领域等方面承担责任,这并非意味着斯密需要一个“弱政府”,而是《道德情操论》中具有“公共精神”而非“体系精神”的那种人。唐纳德·温奇在《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中明确指出斯密对商业社会的态度:它虽有缺陷,但尚可容忍,而且并非完全丧失美德。
与肯定奢侈的积极结果相反,18世纪还有一种反对奢侈的政治经济学。从费奈隆到卢梭,这些人反对私有制,倡导不同形式的公有制。迈克尔·索南斯切在《所有权、共同体和公民权》中围绕人类需求论述了另一种财产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形形色色的共和主义。这套理论与17世纪的格劳秀斯等没有连续性,它源于对初始社会和古代共和国财产状况的思考:占有和劳动是财产权的源头,“劳有所得”这种个人权利是自然的、正义的。这些主张从一开始便是道德意义上的,其最终目标是引导人民走向美德。
然而,何为“美德”以及何为“自然的、正义的”,在18世纪同样也存在大量争论,它们散布在《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各个部分。作为该书的第四部分,“商业、奢侈和政治经济学”的4位撰稿者分析了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及其道德意义。该书第三部分则直接讨论“自然法和立法者科学”,而第五部分则分析“哲学王与开明专制”,第一、二部分介绍“旧制度与新理性”,最后一部分则是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议题“启蒙与革命”,六部分构成了一部紧凑而宏大的思想史。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这部思想史,足可窥见18世纪思想家们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方面的挑战和旨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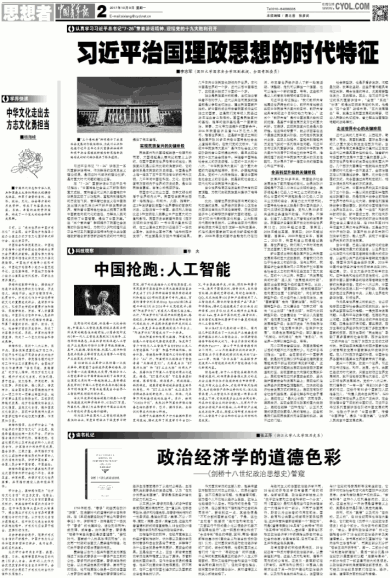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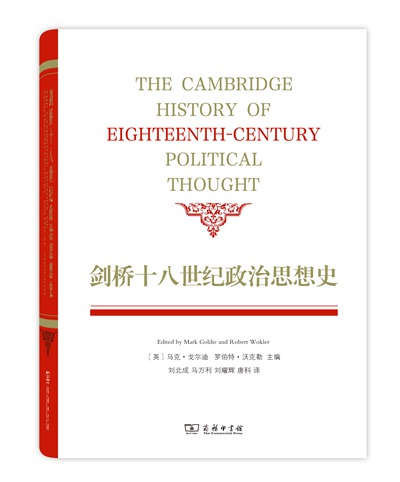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