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的日子前后加起来不过四年。他的居所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水水西头”,是一处友人亲戚相助搭建起来的暂时栖身之所,它是简陋的。但对于一个外出避乱的落魄文人来说,既有人送来修造茅屋之资,还能向人要来数目不小的各种树苗,也还算不错的一种景况。
大致算起来,杜甫向老友索要的树苗包括竹林一顷,应有1万根左右,另有桤树10余亩、桃树100根以及不知道具体数量的松树苗、李树苗和黄梅树苗。到底是不是到手如此之多的数量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杜甫索要的这些树种都到位了,且的的确确栽种在了草堂周围。草堂有桃树林一片是真实的,有荷塘也是真实的,而且荷塘上还有水槛,竹子多得让他发愁也是真实的。杜甫极喜松树,虽精心呵护,存活率依然不高,竹子却长得太快,他每年因此要砍竹千竿,所以才会有“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样的诗句留存下来。
没有足够能力养家糊口,却把大片土地用于栽种无经济作用的树和花,这种事也只有文人才干得出来。茅屋简陋,生活寒苦,杜甫心中也苦,也自惭,但仅此为止,因为苦和惭自来就是一个有用世之志而不能的文人的必然心境,这不丢人,反而可以在这样的苦痛中磨练意志,显其刚韧。而这些松、这些花就是用以自我贞定和自我构建的绝佳象征符号。
在居蜀期间的诗作中,杜甫把自己流寓成都的原因说得非常清楚,“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和那些故意隐逸的文人士大夫不同,杜甫居蜀不过是被逼无奈,暂避风尘,并没有和当朝为敌的宏大背书,内心深处也没有为自己预设一个巨大的藩篱,用以和这个世界对抗。也因此,对生活的穷苦和寒酸,也就自然而然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一面。
看上去,杜甫是满足的。但是,杜甫不是别人,他是那个写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是那个向唐玄宗献上三篇大赋的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许多论家喜欢把这首《蜀相》诗作为杜甫居蜀期间的代表作,认为这才是杜甫在成都生活的全部心思所在,这才是杜甫之为杜甫,是他壮志未酬、龙游浅水的自然心理表现。所以,他要说“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要表现“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的高洁之志,更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这样的高调表态。但我不大愿意接受什么代表作一说,我更情愿把杜甫的这些诗句理解为一种年华虚度、光阴耗费的自惭和内疚。他必须认真处理自己在草堂生活的调性,否则他内心那道坎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
他要处理幽居和贞洁的关系,要处理懒惰闲散与志存高远的关系,要处理一事无成、光阴虚度与心怀社稷的关系,还要处理心安知足与形骸不适而神烦意恼的关系。
步履深林,开樽独酌,是孤独;诗酒自宽,怡然欢悦,是自适。藩篱无限景,恣意买江天,是怀抱。不同意思的诗作都是当时心情的一种自然反应。也惟其如此丰富,杜甫才最终成为杜甫。
在那些宏伟壮观的楼台庙宇悉数倒塌之际,杜甫草堂保留了下来。它是不是杜甫曾经居住过的那间草堂,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处穷但矢志不移的姿态,一种洁身自好的干净和素凛,一种为苍生黎民鼓与呼的寒士怀抱。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多么低调谦逊的言辞,多么虚怀若谷的心态。这个住在风雨飘摇的茅屋中满身是病的小老头,何曾想到,这个世界真就如此,真的就有文章惊动了海内,让后代无数的人不辞车马行旅之劳顿,真的就停留在了这间破旧不堪的茅草屋前——门前池水平静,花径幽香四溢,黄四娘在那里卖茶却不吆喝,桃花开得烂漫却不妖娆,落叶半床,狂花满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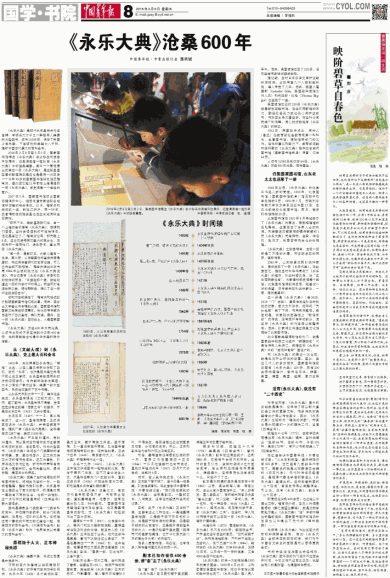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