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神在远古起源之时,不像其他文化的神那样为实体(如印度的devas、希腊的theos、希伯来的Yahweh),而是虚体的 (申)。
(申)。
《周易·系辞》说:“神无方而易无体。”正是对原始时代无方的虚体之神的理性化描述。神在远古之初,与灵相同。《广韵》曰:“神,灵也。”但灵字突出的只是上下四方的虚体,而神( )强调了天上地下四方这一虚体运行的规律。神这一方面的特点,不但体现在彩陶和青铜的图案之中,更在理性化之后演进为太极图中的S形。当神以S形出现,内蕴了对天地互动规律的体察和体悟,成为中国思想在远古起源时的重要特点。
)强调了天上地下四方这一虚体运行的规律。神这一方面的特点,不但体现在彩陶和青铜的图案之中,更在理性化之后演进为太极图中的S形。当神以S形出现,内蕴了对天地互动规律的体察和体悟,成为中国思想在远古起源时的重要特点。
当远古文化从虚体之灵演进到实体之神的时候,神也由虚体的 (申)提升到具有实体外貌的“
(申)提升到具有实体外貌的“ ”。
”。 ,即由“鬼”的实体外形和“申”的虚体内容合为一体构成,在先秦文献中称为鬼神,简化一点可以只称鬼。《墨子》中的“明鬼”之篇、《庄子·达生》中的“有鬼”之论、《九歌》中呈现的“山鬼”等,都指的是这种“
,即由“鬼”的实体外形和“申”的虚体内容合为一体构成,在先秦文献中称为鬼神,简化一点可以只称鬼。《墨子》中的“明鬼”之篇、《庄子·达生》中的“有鬼”之论、《九歌》中呈现的“山鬼”等,都指的是这种“ ”。
”。
在实体之神的时代,鬼的外形多种多样,当时日月星辰山水动植之“ ”,多以动物的面貌出现,比如,太阳为鸟、月亮为蟾。
”,多以动物的面貌出现,比如,太阳为鸟、月亮为蟾。
而有鬼旁为实体之 ,曾为一个普遍现象:天上北斗为鬿,是一个带着斧钺之斤的鬼;天上云气而成鬽;山为鬼的,则有
,曾为一个普遍现象:天上北斗为鬿,是一个带着斧钺之斤的鬼;天上云气而成鬽;山为鬼的,则有 、
、 、魑等;
、魑等; 字,若从土应为土之鬼,若从草,为草之鬼;石之美者曰玉,玉之鬼曰瑰;木石为鬼的有磈、
字,若从土应为土之鬼,若从草,为草之鬼;石之美者曰玉,玉之鬼曰瑰;木石为鬼的有磈、 ;水之鬼曰魍魉,禽鸟为鬼的有魋,动物为鬼的有
;水之鬼曰魍魉,禽鸟为鬼的有魋,动物为鬼的有 、
、 、
、 、
、 。
。
《庄子·达生》讲了山、水、丘、泽、污泥、灶、户的各种鬼,都没有鬼旁但有实体怪形。可见,在虚体之灵升为实体之神的相当一段时间,实体之神是以鬼申合一的 观念存在的。中国思想在实体之神阶段,实体之神内蕴着虚体之
观念存在的。中国思想在实体之神阶段,实体之神内蕴着虚体之 (申),应为一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特点决定了远古时代,神的世界向理性时代气的世界的演进。
(申),应为一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特点决定了远古时代,神的世界向理性时代气的世界的演进。
实体之形的“鬼”和虚体之灵的“申”合一的 ,进一步演进,在大类上分化出:天神、地祇、人鬼、物鬽。
,进一步演进,在大类上分化出:天神、地祇、人鬼、物鬽。
天上的神灵,特别是风云雷雨,虚体特征甚为明显,因此,用本具有虚体的“申”来代表,天神在仪式之中,往往会以想象出来的形象出现,远古的仪式,以中杆之示为核心,在中杆之示下的仪式中,虚体之申,有了两个方面的演进,一是有了实体的形象,二是以抽象的牌位来概括神的内容。
中国天神的演进,从结构上讲,形成了以北极-极星-北斗为中心的天神体系。从形象来讲,成为既有分别又有关联、还可互换的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形象,日月即是日月,风云即是风云;二是实体形象,在动物为主的神形时代为动物,如东方七宿为青龙,西方七宿为白虎,在人物为主的神形时代为人物,如《离骚》中的“望舒”和“飞廉”;三是抽象形象,即仪式中的牌位。
如果按文字的演进来对之强为区分,“申”可用来指自然之象,“ ”可用来指实体形象,“神”可用来指抽象牌位。中杆之示在远古仪式的演进中,后来成为了牌位之“示”,正好与“申”加“示”为神的主流观念相合。因此,申定形在神上。
”可用来指实体形象,“神”可用来指抽象牌位。中杆之示在远古仪式的演进中,后来成为了牌位之“示”,正好与“申”加“示”为神的主流观念相合。因此,申定形在神上。
地上神灵,包含着两个特征:一是地上神灵靠与天的互动而产生神性灵性,因此,以仪式中天地互动的中杆之“示”来命名,《周礼·春官·大宗伯》称为“地示”;二是地上神灵与地域特点相关,从而以特定地域人群的“氏”来命名,中杆之“示”加上氏族之“氏”为“祇”,称为“地祇”。
历史学家丁山说,示、氏、是三字相通。“示”(地上仪式中心的中杆)和“是”(仪式中心之示下的舞蹈和咒语),都讲的是由天地互动而来的相通性和正确性,“氏”则是具有地域性的族群特点。在远古,“姓”是血缘族群聚合体,“氏”是以地域为中心的多姓族的族群聚合体。不同姓族的聚合,其观念根据就在有共同的地神。
地祇作为神灵,其外形特征,最初应是由此族群想象出来的符合自身特点的形象,这形象即被塑形在中杆(示)之上,又体现在巫王的体饰之上和仪式中的器物之上。地祇作为地上神灵,在远古的演进中,成为“社”(再后来有社稷合一),外形只成为五色地坛上的一个牌位(示)。本来的外形之鬼已经被抽象化和理性化了,在这一演进中,地之(鬼之外形和神灵内质合一的) ,就演变成了以牌位来象征、没有外形只有内质(神灵)的地祇。
,就演变成了以牌位来象征、没有外形只有内质(神灵)的地祇。
祖先神灵,在远古观念的演进中,原来以非人的动物或植物或气象的外形为主(《诗经·商颂》讲“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后来,人的形象成为主流,在天神-地示-人祖的演进中,族群祖先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祖庙的仪式中,原来以动物植物为祖先的外形逐渐消失,以抽象牌位和代表血缘亲情、由自己后辈扮演的“尸”成了主流。
《礼记·郊特牲》:“尸,神像也。”《通典》:“自周以前,天地宗庙社稷一切享祭,凡皆立尸。秦汉以降,中华则无矣。”尸在《山海经》中是具有动物或植物等非人形象活显出来:如《中山经》中的“帝女死正,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大荒东经》的“奢比之尸”。
夏商周以来,祖先神占了主流地位,尸都是人的形象,已逝祖先本有人形,尸的形象也为人形,祖鬼外形以人形为主。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曰:“祭必有尸者,节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当天神地示都抽象化之后,本为祖 外形之鬼,还以在世的形象留在记忆之中,并以尸的形象出现在仪式之中。
外形之鬼,还以在世的形象留在记忆之中,并以尸的形象出现在仪式之中。
郑玄注《仪礼·士虞礼》曰:“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外形之鬼主要在祖 中存在,因此,鬼成为祖先之神的专称,成为人死为鬼的专名,并从天地神灵中退却出来。从而,鬼神一词的内容变成了以人之祖先神为鬼、非人的天地之神为神的复合词。
中存在,因此,鬼成为祖先之神的专称,成为人死为鬼的专名,并从天地神灵中退却出来。从而,鬼神一词的内容变成了以人之祖先神为鬼、非人的天地之神为神的复合词。
物之神灵,在鬼-神-灵进行天、地、人、物的分类演进,在《周礼·春官》里被命名为“鬽”。郑玄注曰:“百物之神曰鬽。”《说文》释“鬽”曰:“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
这对“鬽”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定义:一是在内在之质上,《尔雅·释诂上》中“老,寿也”,是物因老而修炼成精,从而具有了神性;二是从外在之形上,《说文》释“彡”曰:“毛饰画文也。” 把具有美丽之义的“彡”加在“鬼”之上而成“鬽”,是对鬽之外形的正面赞美。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讲得更精确:“古多以羽旄为饰,象彡。”即用毛皮鸟羽而组织成美的图案。更深一层的是,彡为远古仪式中,毛皮鸟羽之巫在鼓的节奏中起舞时,显出的飞动光耀状态。
在这一语境中,彡主要有两种含义。首先是美善,有彡的字多与美善相连,兽类中虎的美丽外皮为彪,飞禽中雕的美丽外羽为彫,蛇类中螭有美丽外形为彨,古礼仪式中人饰皮羽而有美丽外形曰彣。
随着人鬼在鬼-神-灵体系中地位日益重要,天神地示人鬼物鬽的区别日益分明,鬽的地位和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字形上,“鬽”变成“魅”,属于妖怪一类。孙诒让《周礼正义》说魅,“即物之老而能为精怪者”。“精”成了“精怪”,《说文》曰:“怪,异也。”魅成了异于日常的奇异之物。服虔注《左传·宣公三年》云:“魅,怪物。”不从“精”的角度,而从“怪”的角度去讲魅了。段玉裁注《说文》云:“魅,人面兽身而四足,好惑人。”已成异于正常理性世界中的怪物了。
天神地示人鬼在理性化的演进中,进入朝廷的宗教体系,本来与其一体的物之鬽,就从正面形象转变为具有负面意义的物之魅。
先秦在理性化的进程中,定型为理性化和宗教化合一的文化。在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够解决的范畴内,用理性思考,在此之外则用神性思考,二者以理性为主而相互为用。
体现在朝廷建筑上,理性化的宫殿是中心,左祖庙,右社坛,四郊为天地日月坛。在思想观念上,神也有两方面的演进:在理性方面,神,与其起源上的虚体相一致,一方面在主体上,成为与形相对之神,即《荀子·天论》的“形具而神生”。
在这一意义上,神即为人心之主,所谓“心之宝也”(《淮南子·精神》)、“心之用也”(扬雄《太玄·中》)、“智之渊也”(《淮南子·俶真训》)……似等于理性的运用。由之而有一系列词汇:神气、精神、神采、神色、神志、神韵等。
由于神有宗教性的一面,又可释为“知人之所不知谓之神”(《淮南子·兵略》)、“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由之而有一系列词汇:神通、神妙、神机、神会等。
在客体方面,神展开为天地运动中既有规律又不可见的一面。正如《荀子·天论》讲的:“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神在宗教方面,提升为实体之神,具体而言,分为三个方面。
在朝廷的理性和宗教合一内容中,其宗教性形成了三大宗教体系:一是以中央朝廷为主体的主流宗教体系,以天坛地社祖庙为核心,用牌位方式将天神地示祖鬼组成虚灵化的祭祀体系;二是由汉至唐形成对朝廷具有辅助作用、在民间很普遍的佛教道教,一种有具体神像体系、典籍体系、仪式体系的宗教体系;三是在以上两种体系之外,面对各类神奇怪异现象,形成主要由历史名人而来的神灵形象(如关公),和主要由民间灵异现象而来的新的精怪形象(如白蛇),前者往往进入到国家祭祀体系之中,后者则根据具体情况,有的进入已有体系,有的则外在于已有体系,成为所谓的淫祠。禁止淫祠和改造淫祠,是古代社会的常见现象。
理解了神、灵、鬼、怪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出现、演进、定型,对于中国文化会有更深的理解。中国的神、灵、鬼、怪,何以如此出现、演进、定型,又是理解中国文化整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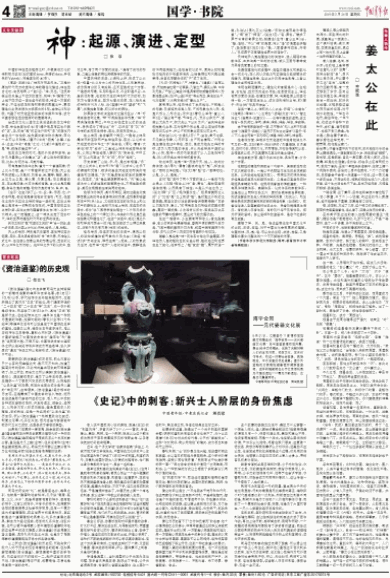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