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一片农场山峦绵绵、丛林茂密,这里漂浮着最悲观的乐观主义。
就像农场墙上印着的一行字,“做最坏的打算,同时享受当下”。平时,这里是徒步旅行、高空滑索的好去处,但建造农场的人相信,世界末日终会来临。
他们由几百个人组成,共同出钱建立一个反乌托邦的王国。这些人相信,当大规模传染病、战争、金融灾难等电影里的场景发生时,这块营地将是天然屏障。
生存农场占地超过50英亩,会员每年支付大约1000美元的费用,用来换取“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进入农场的资格”,平时没事也可以来这里度假。这里储存着食物、种子,还有专门用来处理传染病爆发期间被污染的物体的大燃烧坑。
演习中,有个妈妈在传染病爆发时带着饿坏了的孩子来营地求助,根据生存准则,他们将不会打开大门。“这就是人的本性,在文明几近毁灭之后的求生战争里,你最大的敌人也许就是你的邻居。”末日主义者说。
虽然违背人道,但某种程度上,末日主义者都是创伤的受害者。农场的领军人物德鲁·米勒退休前,是美国空军的一名上校。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苏冷战期间,他的家离美国空军战略司令部只有1小时车程,处在苏联核打击的范围内,这拉紧了他的神经,塑造了他的价值观。
在哈佛大学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米勒的毕业论文是分析在美国全境建造多少座地下掩体,能大大降低在华沙条约核闪击战中所遭受的损失。生存农场像是这份论文在几十年后的实践。
米勒会训练营地成员用枪自卫,在生存农场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72小时兽性”,它意味着在危急时刻,任何人都会在72小时内变得危险。
末日主义者一朝被蛇咬,百年都怕井绳,常常用显微镜放大危险,而人类自身总是麻烦制造者。“惊弓之鸟们”在和平时期寻找一处世外桃源,默默舔舐往日伤疤,过去的苦难让他们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全球主义、甚至不相信同类。
作家普里莫·莱维曾说,“人类文化、文明极端脆弱,在经受繁重劳动、寒冷、饥饿与殴打之后,一个人只需要3个星期就变成了野兽。”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战后不厌其烦地重述痛苦的经历。
如果这些伤痛对于人类来说正在飘远的话,那么下面这位的经历近在眼前。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经拍摄过纪录片《末日准备者》的凯文·巴伯是受访者之一。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夫妇和谐,一儿两女,生活在美国堪萨斯州一个安静的中产社区,恬淡舒适。
直到几年前,夫妻俩突然注意到美国面临庞大的债务危机,预感经济崩溃即将来临,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决定逃离的唯一途径是前往哥斯达黎加。于是,二人开始卖房子、转移资产,将太阳能电池和备用发电机装进集装箱,打算漂洋过海,与哥斯达黎加岛上的居民一起过简单的生活。为此,全家人准备学习西班牙语。
从2008年开始,人们在谷歌上搜索“末日生存”的次数上升,其中有生存类真人秀节目的影响,也有大众基于现实动荡的“杞人忧天”。
超市售价999.99美元的大号塑料桶里塞满了冻干蔬果、谷物和肉类,声称可以养活一个成年人整整一年,保质期长达二三十年。YouTube上的压缩饼干测评播放量攀升。美国财经新闻网站估计,在2013年有370万末日准备者和数十亿美元规模的相关市场。
相对于米勒,这些跟风的末日准备者也许只是遭遇轻微的压力预警。美国社会学家针对“末日生存”进行的研究显示,“民众对生存论的热衷程度,是验证一个社会是否焦虑的晴雨表”。社会学家理查德·米切尔说:“一般情况下,这一现象可以被解读为民众对社会压力的一种真实的应激反应。”
再滑稽的行为似乎也不再好笑。对于他们来说,末日就像脚下的地毯突然被抽走。
彼得·斯坦福生活在英国贝德福德郡,一位亲历战争的朋友对他描述血肉横飞的场面,让他感到“身历其境的威胁”,这团阴影在他心里蒙上战后蘑菇云。
恐惧已持续了20年。斯坦福总是在日落时分,在家附近的河里练习逃生。他坐进皮划艇,头戴照明灯,在夜幕掩护下一遍遍重复“逃离”。
杨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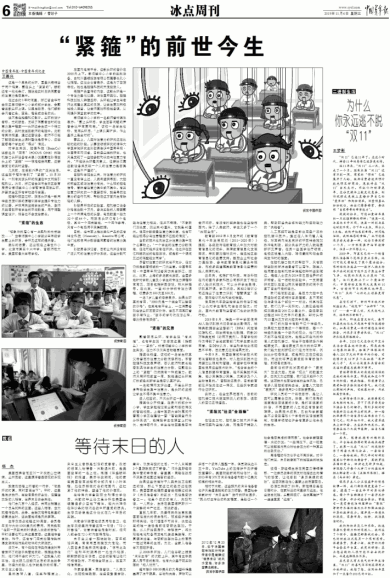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