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天津,第一反应可能是冯骥才;写天津的小人物,第一反应可能是冯骥才的《俗世奇人》。不过,《俗世奇人》中的人物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毕竟应了一个“奇”字,终究是有过人之处;而王松的这部长篇小说《烟火》,铺陈开的是一个更普通的人间百态,从题目就能看出,很市井、很生活,宏大叙事是没有的,但能具体到老天津的老百姓是怎么摆地摊的。
王松说,真正的天津人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非常崇尚手艺,而且这手艺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已经不仅是手艺,还上升成一种文化。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无论卖什么,基本都不是买进卖出的“中介”,而靠的是手艺。
故事从1840年开始讲:卖鸡毛掸子的,杆儿轻,毛儿长,看着密实,一抖搂又很蓬松,掸土不用掸,土似乎自己都能往掸子上跑;卖烧煤球炉子用的拔火罐儿,先把土和成泥,再踩着转滚子把泥拉成坯子,别看是用土烧制而成,却烧得比炮弹还结实,扔到地上能蹦起来;绱鞋的,不光针脚密,还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踩在地上不光跟脚,也轻巧……这些如今已经消失的街边手艺,现在来看,都堪称“非遗”。
近代天津开埠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外国人的租界,另一部分是原来的老城区,这中间还有过渡区,《烟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于是,这些摆地摊的手艺人,也不可避免地与洋人、买办、革命者等各色人物产生关联。主人公来子的爹是卖拔火罐儿的,他自己卖过包子、鞋帽,深谙生意之门,也守住了做人之门。摆地摊的人堆里,也有英雄。
但《烟火》讲的还是普通人,所以小说中的人物还有一个特点:没有“因祸得福”的巧合。不像武侠小说,看见悬崖一定记得往下跳,跳下去才有可能获得失传秘笈、得遇高人指点,最终称霸武林。在普通人的剧本中,遇见灾难最大的可能就是死亡——《烟火》中即是如此,而且说死就死,毫无转机的可能。
当然,如果地摊能摆得够久,有朝一日成为著名“老字号”也未可知,而摆地摊的人,也可能成为传奇。那,就是另外一种叙事了。
《烟火》的故事结束于民国末期,但天津人的这种品格,一直在延续。到了计划经济时期,商品比较匮乏,年轻人结婚时,家具不好买。于是,在天津的街巷里,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做家具的文化,而且做出来的和买的比一点不差。
比如,用铁管做双人床的床头,怎么窝这个弯儿?不是烧红了一窝这么简单,这样这个铁管就瘪了。天津人就这么聪明,先在铁管里灌满沙子,然后再烧、再窝,这样既能窝出形状,铁管本身还不变形。再比如,自行车不好买,要凭购买证,当时叫凭“条儿”,天津的年轻人就用零件自己“攒”自行车。那时在天津劝业场门口一带,是个互相交换自行车零件的场所,大家互通有无,有的零件实在凑不到,还能自己做。
美国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摄《战争启示录》时曾说,他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带着观众去东南亚的热带丛林做一次探险旅行。王松说自己写《烟火》时,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他也想带着读者,回到100多年前的天津,游历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市井,吸一口这里的老百姓曾经的烟火气。
写完后,读者回没回去王松不知道,他自己反正是真“回去”了,而且不是简单地溜达一圈了,而像和小说中的几代人真真切切地生活了一百年。
有一次,一个住在天津老城的朋友陪王松在“锅店街”一代转,这是《烟火》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著名”街区。路边有个摆地摊的老人,跟他闲聊了一会儿。老人对当年这一带的每条胡同和各种往事都如数家珍,用天津话说出来,就尤其生动。老人、老人的地摊、“锅店街”的牌坊,这三样看上去,都像文物。
在很多受到文艺青年追捧的自由行指南中,都说要了解一座城市,就要去坐它的公交车、吃它的街边早餐,逛它的菜市场……如果一个城市还有成规模的地摊,那一定也在“必游”之列。当长得一模一样的商业综合体,逐渐复制到各个城市、又下沉到县城,四方商机涌来,地摊也许是保留城市特质的最后一面墙。
摆地摊的人,有着城市最真实的面孔,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卖的是啥,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都拼命活着。
蒋肖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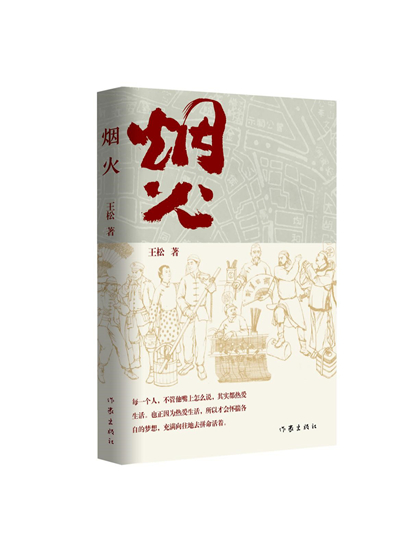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