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近日,“张玉环案”原案受害儿童的母亲舒爱兰接受采访,将两个被杀孩子的家庭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野。
27年前,张玉环被指杀害同村两孩童,7年后被判处死缓。历经20年的申诉,被羁押9778天后,他于今年8月获改判无罪。几天前,张玉环的家人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张玉环支付国家赔偿金共计496万余元,包括无罪羁押9778天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张玉环案”改变了3个家庭的命运。张玉环等来公道,被害人家庭则在继续寻找真相。另一受害儿童的母亲刘荷花近来常常觉得喘不过气——她一直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除了真凶,还应有冤错案件的制造者。
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上披露,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依法办理各类审判监督案件178万件、刑罚执行变更案件386万件,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1万件,依法纠正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刑事冤错案件58件122人。
这些冤错案件纠正的过程,张氏叔侄案等了10年,呼格吉勒图案经历了20年,聂树斌案是22年……这些冤错案件中也只有部分得到了完全澄清,有些真相可能再也无法追寻。回顾这些案件的发生,可以发现,被告人供述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比如发生于1994年、宣判于1998年的佘祥林案,以及发生于1998年宣判于2003年的赵作海案,由于没有使用当时已有的、相对比较成熟的DNA鉴定技术来确定被害人身份,只是依靠被害人亲属对高度腐烂的尸体进行外观辨认的方式,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确认被害人这一环发生了重大错误。数年后“亡者归来”,冤案得以纠正,重获自由的赵作海和佘祥林都反映,当时的招供是被逼而为。
在石家庄西郊发生的聂树斌案中,直接证据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实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能证实被害人死亡与聂树斌有关。但聂树斌还是被作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被判处了死刑。
2005年,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聂树斌案真凶,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而在王书金的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该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真相还未大白。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说过:“自从有刑法的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开始,国家就承担双重责任……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
为了避免冤假错案,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在1979年即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更确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进行了细化。物证没有得到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冤案被制造出来,真凶则逍遥法外。
今年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的张志超强奸杀人案中,原审两位证人的证言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而这两名证人的证言与张志超的供述之间也存在矛盾。此外,4名同学证明被告人张志超没有作案时间,这些证言在原审中未被出示。张志超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便存在疑问。与此同时,案发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指向张志超作案的客观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的张志超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张志超的辩护律师发现,被害人的尸体上套有90厘米×108厘米的白色塑料编织袋,根据编织袋上的字样,基本上确认编织袋是装柳编等工艺品出口的袋子。律师认为,该编织袋只能是凶手占有并使用的,查清楚来源,基本上可以确定凶手。原审时,因为没有查清楚,判决书回避了这一物证。15年过去,这一线索能否得到继续追查,案件真相能否水落石出,也成了一个谜。
顶着“疑罪从无”的名义获得无罪,张玉环们依然要承受许多无端的怀疑和指责,无法真正从案件中解脱。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被平反的蒙冤者还是原案件的受害人,查明真凶都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就表示:“我们希望公安机关,能对当年两个死去的小孩死因重新立案复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对死者家属交代,也是对社会一个交代,如果公安机关能抓到真凶,我们愿意从张玉环的赔偿金里,拿出5万元奖励参与侦查的干警。”
近年来,随着刑侦领域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我们不断看到一些陈年积案告破,比如尘封28年的“原南京医学院女学生被杀案”。但对于张玉环案的受害人来说,蒙冤者平反还不是终点。
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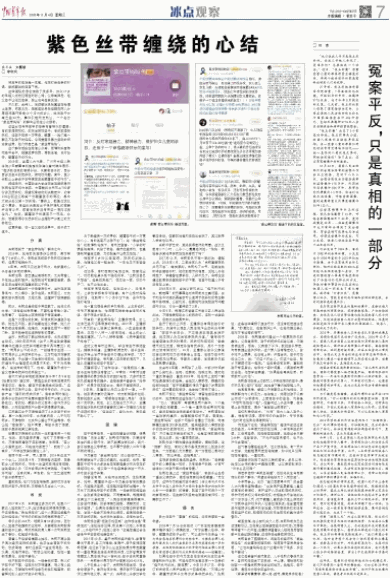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