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前,睡过十几年的床即将拆除,我从那厚实的床垫下翻出一沓信纸。细看来是小学写过的拙文,文笔粗糙,剧情生硬,像一个站在田野里的干瘪稻草人。
我本想将它同其他积灰的物品一起扔出,但在扔出前它传来一声咳嗽。
不大不小,仅有我能听到。我想:它是什么时候有的生命力?压埋许久依旧活跃。
应是那次语文课。
我单薄的练习本第一次出现在老师手中,她字句清晰地朗读出我天马行空的想象。
周遭都在笑,其中却无贬义。
“你做得很好。”老师说,身后的黑板上写着作文要求:将不同的故事融成一个故事。全班唯独我做到。
我铅笔下写贾宝玉一心想要求回林黛玉的性命,他去五指山下求灵猴施恩,求它铁石心肠可落一滴泪,换他们一双人再重逢。但那灵猴是泼猴,骗了他,让他替自己压在山之下。
最后,猴子假活成人,在梁山落草,而贾宝玉还在九九八十一难里幻想黛玉归。
我依稀记得那段时间不少同学要我写后续,他们当了真,有得还举一反三起来。
人言来往,吵闹不绝,我在某一瞬间感觉笔下的人果真如写的那般活起来。后来我寻找其中原因,回想起那时每个单纯眼神里都映射出一处鲜为人知的神迹。
他们是读者,读者的相信即是对故事的信仰,信仰则滋养出笔下人物的灵魂。
从此,我也开始相信,我拥有创造平行宇宙、赋予魂魄的能力。
儿时的梦总爱做得很大,反正我无畏也无为。
我去挖出黄粱之下藏着的梦,梦里他心惶惶,梦外我不亦乐乎。看笔下的人好争好抢输掉一生,本不值得同情却要为其赔上几滴眼泪。或塑造一位鲜衣怒马,贪恋红尘的少年郎,眼看他高楼起,宴宾客,只在极其寻常的某天丢失心脏,此后永世都沉陷于微雨中哀叹,等门前青苔有马车碾过。再者,就来一位在古镇小河旁卖花的少女,一生都在委屈与自卑中挣扎,被辜负了又辜负,最后不甘心地闭眼了却余生。
无论是哪种,笔下的世界有无数可能,总是种种玄机不可问。
“砰砰砰。”那时,文学的心跳声强而有力。
因为中考失利,高中的三年除去语文考试,没有再为自己写过什么情。直至大学,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去挥霍。拿到第一份签约合同时,我穿着睡衣,迎着走廊的长风同妈妈讲那分激动。
泪眼朦胧间我觉得我创造的世界即将诞生,完善,最后金碧辉煌。
可是没有,像石子入水竟无声,黑夜吞鸦影竟无踪。我反思过,是我越来越小心翼翼,越来越迎合。
我曾经是无畏,也是无为。不为什么去书写,只为书写而书写。
但那时我是为利益去书写,每天沦陷在信息洪流里,成为“道听途说”的莽夫。流量即是我所争夺的一切,所以我甘愿牺牲笔下的他们,消耗他们身上生气,哪怕不符常态,不应人情。
我的世界最终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它像是才修建好就被洪水卷入海底的建筑,比烟消云散还惨痛些。
欢愉是文学给的,后者痛苦是我给的。
“咳咳。”那沓信纸又咳了起来。
我再重读一遍自己写过的人与事,不禁笑起来,他们稚气莽撞,行为也来得莫名,挑不出好可也厌不起来。
我问同在写手圈的前辈,这写得好吗?她说,普通俗,但我记得住。
末了,她补充一句,你为什么写?
我说,那时想着,写下来便会开心。
猛然,先前因为国度坍塌而灰心重重的我,好像浮出水面深深吸了一口气。
那本是最真挚的初心。
仅是为了书写,为了靠近文学而书写。是三月的雨,让落肩头的樱花挣扎出最后的绽放,至此留在过路者的心中。
我将信纸重新收好,面对空白的文档。眼前,有个舞台拉开序幕,欲望蔓延,渴求生长,形形色色的人七嘴八舌,我要他溃败,我要她涅槃,怎么样都好,全是为了我的初心。
那个藏在床垫底下做了十几年的梦。
“砰砰砰。”它不再咳嗽,心脏有力跳动,不会停。
冯嘉美(19岁) 武汉晴川学院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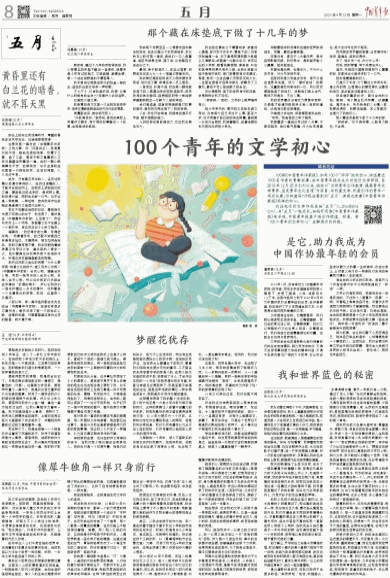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