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针对我国超过1万名科技工作者的调查数据显示:有24.0%的科技工作者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其中6.4%的科技工作者属于高风险人群;有一定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其中部分科技工作者属于中重度焦虑。
这份数据来自中科院心理所最新发布的《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作者之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近十年间即2009年、2017年和2019年进行的3次调查中,科技工作者的抑郁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近两次的调查中,科技工作者的轻、中、重度焦虑问题比例也均在上升。青年科研人员“心病”问题亟待关注。
中级职称科技工作者焦虑程度最高
作为青年教师,33岁的李铭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清晰的规划:40岁前一定要拿到教授职称。他自己心里盘算着:“如果以后我想做博士生导师,必须尽早评教授,否则未来很难拿到国家级的项目,或者发核心、典型的C刊。”
因此,工作5年来,一到寒暑假,他就把时间利用起来做科研项目。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近的他有些焦虑。
在去年副教授职称评定中,这位来自湖北某高校的青年教师“败下阵来”,全校80余名不同学院老师同台竞技,他是学院综合评分第一名,本以为志在必得,却在评委投票环节因未能拿到理想成绩而落选。
“时间紧迫,我要尽快在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不然就赶不上下半年评职称了。”李铭说。按照学校规定,今年他如果继续参评职称,就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学术成果,不能拿过去的“重复参加”,这让他感到“焦虑”,“正是评职称的关键时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今年4月,他申请了3个项目,博士后导师也催着他赶紧交文章。那时正逢学校组织体检,这位1987年出生的青年科研人员收到了“血糖偏高”的结果。从那以后,他便督促自己每周打篮球,锻炼身体。
《报告》显示,一些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其中,中级职称的科技工作者焦虑水平最高——有14.5%的人可能有中度焦虑或重度焦虑问题。
李铭就是“最高”之一。这些被“爆炒”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部分来自内部,自我期待;另一部分则来自外部,学校高要求。
以李铭所在学校为例,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仅增加了评职称的难度,也提高了年终考核的门槛。以往每年只需一个左右的省级项目即可达到“及格线”,如今要至少拿下两个省级项目才算合格,“而且对核心期刊的要求更加具体,直接划线到了排名的前30%左右”。
《报告》对科技工作者工作特征的维度进行细致研究,发现抑郁和焦虑与工作压力呈正相关,工作压力越大,抑郁和焦虑水平也越高,而其他4个方面如技能发展、决策自主、同事支持和上级支持均与抑郁和焦虑呈负相关。
科研起步阶段最难
另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刘爽,则面临科研成果的“限时任务”。入校时,学校和她签订了协议,3年期间完成规定任务,才能转为事业编制,否则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问题在于,起步太难了。”刘爽说。对于青年科研人员,一年到手的科研经费两万元左右,搭建实验平台,买实验设备,随便一个仪器就要三四千元,好一点的动辄上万。她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自己去找靠谱的供货商,市场比价,尽量买最便宜的东西,“这都需要时间”。
在她看来,只有平台搭建起来,才有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有些器材没有,你不得不放弃这个课题。就算勉强能完成项目,也做不到很精确。”
在办公室里,她偶尔和系里新老师聊天,发现不少同龄人都有类似焦虑。新入职的老师一没平台,二没人手,更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况。
陈祉妍说,适度的焦虑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促进有效解决问题,而过度的焦虑则会造成身心的痛苦,给学习和工作带来较大危害,甚至会造成正常社会的功能受损。
李铭明白,做科研是一个很苦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等待一瞬间的爆发。外部的环境压力加速着他的成长,“某种程度是推着我往前跑”。
不过,他有时候和老教授聊天发现,这似乎是“青椒”“青稞”成长的必然规律,30岁左右博士毕业,中间10年要集中解决房子、配偶、小孩等问题,等这些生存问题解决后,才能真正安稳下来,人才能平静下来。
“实际上从30~40岁,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煎熬的阶段,打好了基础后,过了40岁,事业慢慢有起色,焦虑、压力可能就自然消失了。”李铭说。
《报告》也佐证了他的观点:焦虑水平相对最低的,是正高职称的科技工作者。
科研教学生活角色需要平衡
刘爽是刚入职高校的新教师,上完大学第一堂课,她给朋友发了个信息,写着:英语说得嗑嗑巴巴,被督导逮了个正着。接着,她发了一连串的省略号。
“现实打了我一耳光。”她心里愧疚,“再多给一点时间,我是能把课讲好的。”
她所在的学院正缺人手,新教师还没参加完入职培训,领导就给她布置了任务:下周就得去给留学生上课。加班加点,她做完了PPT,第一次给学生上课紧张,加之英语不熟练,就有了这样的结果。
新人有科研考核任务,教学量也大。她曾在学校里碰到一位同事,脸色惨白,一问才知道一个星期每天都有课,而且都是最前沿的课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准备,“只能拼命地干,拼命地备课”。
除了科研、教学压力,来自家庭生活的压力,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情绪。
据北京某研究院王强观察,身边有女同事刚生完孩子不到一年,因工作项目原因,经常去外地出差,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有3个星期都在外地,“有时候明显感觉她情绪不高,心里装着事儿”。
海琴是一位有个1岁多大宝宝的“85后”科技工作者,她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孩子的教育问题:自己长期在外做科研项目,一个月最多回去一两次,家里老人负责照看孩子,可晚上一关灯小孩又哭又闹,老人管不住,小孩有时到11点多还没睡觉。
“孩子从小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导,但我的工作没办法让我常在她的身边。”海琴说。
对部分科技工作者而言,繁重科研任务和日常家庭生活的平衡出现了偏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团队对1310名科技工作者进行小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工作对家庭的消极影响,还是家庭对工作的消极影响,都与科技工作者更高的抑郁与焦虑得分正相关。
需加强心理健康素养知识和技能的普及
《报告》直观地反映了部分科技工作者的心理援助心声:接近八成的人认为应该定期做心理健康状况监测;58.9%的科技工作者愿意参加心理健康普及活动;71.6%的科技工作者愿意接受心理咨询。
博士期间,刘爽留学时了解到,在国外有的大学里采取了三级心理干预方法,如果你来求助,第一层给予心理上的疏导,如果精神上无法帮助你解决问题,他们还会成立调查小组,去所在院系调查,甚至会对领导进行处分。
“在国内,我们没有对科研人员成立专门的心理辅导室,或者心理咨询师不甚专业,很多人不会主动去寻求心理咨询。”刘爽观察,身边同事排解压力的方法更多是和朋友倾诉,或者打球运动。
她曾和同事探讨要不要去学校心理咨询室“看看”,得到的回复竟出奇地一致:去了也没用,如果真把自己压力告诉了学校心理师,万一被说出去,搞不好要得罪领导。
陈祉妍说,科技工作者普遍更愿意通过网络平台和绿色通道进行心理咨询,这种形式可以与自己单位保持相对独立,与《报告》发现的科技工作者对心理和情绪问题存在污名化和误解、对使用心理健康服务存在顾虑的结果是一致的。
《报告》发现,70.3%的科技工作者感到无法便利获得心理健康服务;40.6%的人认为费用构成使用心理服务的困难;约一半的人害怕看完心理医生之后被同事误解,还有近六成人表示自己“不能判断何时去求助”。
刘爽建议,可以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与行业权威的心理咨询师合作,利用名气增加被咨询者的信任感,“有抑郁症状的科研人员无法自我排解时,还是会倾向于寻找权威专家的帮助”。
如何为青年科研人员心理“减负”?
《报告》提出,要完善心理健康筛查和检测机制:为筛查出的高危个体提供就诊和转诊指导,避免出现延误干预和治疗时机;此外还可以从科研环境来改善,如加强团队支持,对于工作制度、环境客观条件进行改进和调整,营造关爱与支持的环境、氛围。
陈祉妍还建议,加强心理健康素养知识和技能的普及。她说,基于科技工作者的服务需要,在“知”的基础上,也要重视“行”的培养。对有助于提升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促进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心理技能,如可以提升自我效能感、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及时缓解压力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可以开展相关培训,开放学习资源和机会,让科技工作者可以掌握科学的知识和技能,有技“傍身”,从而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应采访者要求,李铭、刘爽、王强、海琴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记者 邱晨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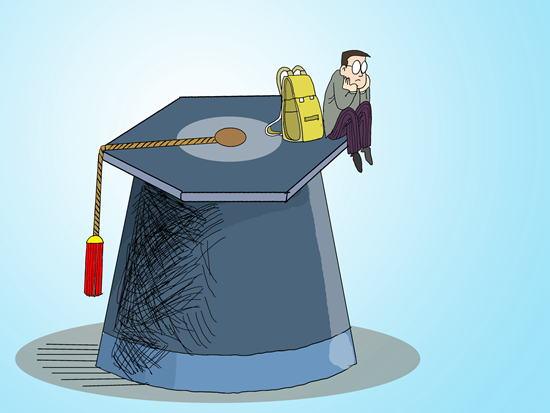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