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两位耄耋老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获得了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科学家在青年时期都已经担当重任:1964年,我国开始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飞机,34岁的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1964年,我国第一个自主设计、建造的屏蔽试验反应堆成功启动,那时的王大中只有29岁。
他们的成长故事带来哪些启发?面对新时代的科研竞争态势,如何优化环境助力青年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中揭榜挂帅?记者采访多位科研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完善科研评价的指挥棒
2007年回国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系主任陈华伟曾遭遇“水土不服”的难题:那时,国内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不够,更看重实际工程应用的社会效应,基础科研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经费捉襟见肘。
陈华伟带着团队死磕微纳仿生表面制造的研究,历经10年总结了梯度泰勒毛细升理论,提出了复杂微纳表面结构生物成形制造工艺方法。在40岁那年,他在《自然》发表论文,成为国内机械工程领域首位在该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凭借这一系列成果拿下科学探索奖等奖项。
“创新性研究风险大,不易成功,大部分人按部就班地做一些‘求稳’的项目。”陈华伟曾想,如果中国有十分之一的科研人员愿意做一些前沿性的突破研究,那么中国的科研创新力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匹敌的。
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此后,《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等文件紧锣密鼓地出台,不断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徐祥感到了明显的变化:以前的科研环境是“唯论文”“唯帽子”,为了论文而做科研,产出了不少低含金量的科研成果。近年来,评价体系已经开始注重科研工作者的“代表作”了。
他同时认为,科研评价体系仍待完善。他建议建立分类考核的方式,去支持基础研究学者做长期探索,应用型研究学者做科研落地。对于部分特殊学者,可不再采用短期评估的方式,转为长期考评的方式。
“让学术界的大师来做‘裁判’,哪怕某个阶段青年学者的文章并不出色,但只要有创新性思路,也不怕被埋没。”张徐祥说。
一些科研管理者认为,完善同行评议制度十分必要。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张友军告诉记者,对于一些时间周期长的科研项目,不应再“一刀切”地以文章论英雄,而是让同行专家去审定课题研究的社会价值、潜在学术价值等。
他建议,在同行评议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谁评议谁负责”的机制,构建同行评议的专家诚信制度,一旦课题评定出现问题,按照制度对评审人进行追责,并在档案中留下不诚信记录,起到行业警示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生物所前所长黄力支持同行评议,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片面依靠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去评价,以专家的科研经验、专业判断力,作出基于客观数据的判断,可以更全面地分析人才或成果水平。
此外,他建议分类评价,根据不同领域的课题周期、学科特点去制定相关的评价标准,建立专家评议库,采取匿名评议的方式,让科研“指挥棒”少一些行政、人情的干扰。
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几年前,黄力和团队做过一项有关青年课题组长的改革试验。
他们通过竞争性筛选程序,选择部分副高职称的青年科研人员,给予一定的人、财、物支持,让他们独立主持实验室工作。令人惊喜的是,4-6年后,这些青年科技工作者中的多数人成为杰青、优青、国重副主任等“人才”。
以历史的眼光去纵向分析,黄力反思:如果给青年科技工作者一个足够宽容、信任和鼓励的成长通道,那么部分人可以抓住机会,迅速成长。但若这批人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或许就会被耽误或埋没。
他认为,可以探索一条给优秀科研人员培养与上升的职业发展通道。
在企业,青年科研人员培养机制同样重要。一家国企下属研究所管理人员表示,在部分国企单位,科研人员的流动渠道较少,职业天花板较低。企业的人才评价与筛选机制大多是根据绩效来划分等级,对于优秀科研人员的发展通道规划尚未完善。
在世界范围内,以谷歌、亚马逊、苹果等互联网企业为例,其内部员工在技术研发上重视创新性的成果研发。在国内,马化腾等企业家也明确表示要加强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移动支付再先进,没有手机终端,没有芯片和操作系统,竞争起来的话,你的实力也不够。”
在高校科研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吕琳媛所在的团队被称为“敢死队”,他们探索的是“从0到1”的科研课题。
有一天,学院的党委书记对她说:“有什么想法就大胆去做,我们都会支持。”吕琳媛心里一阵感动,“这种信任对青年学者从事原创性工作来说,非常重要。”
吕琳媛感慨,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支持机制,她的科研之路可能也走不到今天。
建立回归科学价值本源的科研体系
要做出一项原创性科学成果有多难?
吕琳媛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团队从事大脑神经联接图谱研究,该研究从启动开始,团队成员陆续更新了几拨儿人,有的成员加入三四年后就退出了。9年后,这项“难产”的成果终于问世,登上了《科学》杂志。
吕琳媛说,在科研领域,这支团队已经是幸运儿了,很多团队10年也未必能磨出一剑。
这意味着,科研人员需要极高的试错成本。以上述故事为例,过去9年,团队里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可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成果去申报项目、评奖和职称评定;对3年学业的硕士生、4年学业的博士生而言,他们可能没有科研成果达到毕业要求。
未来,这种情况将会有所好转。2021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其中明确提出,“国家加大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奖励。”
通过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选结果可以看出,获奖项目平均研究时间是11.9年,其中研究时间10-15年的项目数量最多,占比38.9%。而曾经数度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1年开出“双子星”。
科研人员有了更足的底气来坐“冷板凳”。
社会各界的相关投入也越来越多。2018年,腾讯基金会斥资10亿元设立科学探索奖,不关注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而是聚焦尚在探索期的年轻科学家。该奖项发起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表示,就是要支持年轻人做其他人想做但做不出、不敢做,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研究,为青年科学家冲顶科学高峰提供物质补给、也提供精神鼓励和价值认同。
如何回归科学价值本源?
吕琳媛描绘过一个从事原创性科研工作的“乌托邦”:那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研究所,只要敢想敢做,合理的科研项目都会获得支持,不用担心考核压力,不用担心天马行空的想法被大师们嘲笑,可以对任何科学发现提出质疑。
在那里,无论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还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大家,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科研交流机会。吕琳媛认为,“那是科学的天堂”。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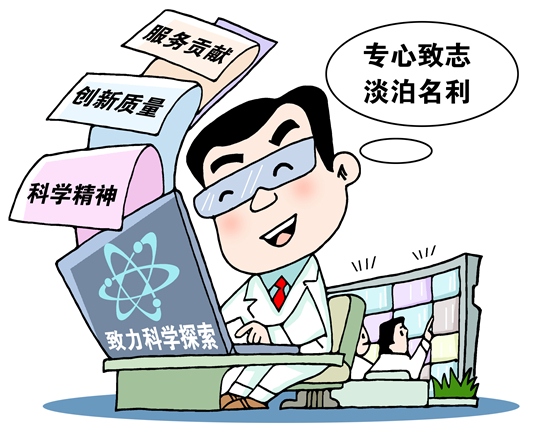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