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开始前,洗好碗筷,我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对面楼的落地窗——客厅的灯亮着,看来这家人并没有去外地过年。
他们是一年前的春天搬进我家对面楼的,透过他们新换的落地窗,偶尔能看到一位男士在阳台的跑步机上锻炼;靠近窗户的沙发是亮黄色的,日落时会镀上耀眼的金色;还有一盏不知是做什么用的长明灯,在客厅里彻夜不熄。隔着几十米,看不真切,但日子久了,也能拼凑出一些信息。
他们不习惯拉窗帘,我也不好意思就这么直勾勾地打量。记得2020年,网上曾曝出山东某小区的一名女业主透过玻璃窗发现对面楼里的男子在家赤身裸体,于是拍照发到了业主群里,并喊话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及未成年人。没想到照片一发出,男业主毫不示弱地反击道:知道吗,你犯法了!并表示已经报警。之后有律师表示,男子在家中的行为并不违法,反而是女业主的行为直接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对方是可以要求其赔礼道歉,甚至赔偿损失的。
在引来“他人的目光”之前,玻璃窗的出现,是为了将更多的光线引入室内。至今,在苏州的一些园林和古村落里还能看到一种“明瓦窗”,制作明瓦的主要材料为贝壳、羊角、云母片等,当然在透光性上无法与玻璃相比。我们也有制作玻璃的经验,但作为建筑材料使用的工业玻璃算是舶来品。根据一些文书的记载,雍正年间,紫禁城内开始使用进口的平板玻璃。这些玻璃从西欧远涉重洋而来,稀有且昂贵,所以起初只在窗户中心一两个窗格上安装,四周仍旧糊的是窗户纸。据说,进口一平方米玻璃合纹银15两,按当时的房价计算,安两扇玻璃的钱与一间房屋的售价差不多。
不过,知乎作者Kai在整理这些历史资料时发现,先于宫中,几千里外的商贸之都广州,更早地用上了整扇的玻璃窗。雍正年间,商贸兴盛,洋货行在广州城外渐渐形成规模,有实力的洋货行不但有店铺、仓库、货场、码头,还在庭院里建有专门出租给欧洲客商居住的“夷馆”。这些小楼按照西式建筑的样式建造,窗户用的玻璃就是这些来中国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的欧洲商人带来的。
受益于材料和工艺的进步,透明建筑在19世纪得到了“跳跃式”的发展,玻璃被大量应用在层出不穷的建筑式样中,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图景。当然,它的反光、易碎、高耗能等特点给人们带来了各种问题,但它的流行,就像每一种生活方式的出现,总是与当下社会人们内心的渴望同频——它为拥挤、逼仄的城市带来了明媚的光线,为隔绝、封闭的人造建筑引入了天空、飞鸟、绿植等更多的自然元素,也因此,那些可以透过玻璃窗享受到自然之美的海景房、山景房,总是被标出更高的价格。人类从自然走向城市,在为自己建造庇护之所时,依旧希望与自然、与他者保持着某种警醒、联系,而这正是空间秩序上的“透明性”真正的意义所在,“透明性并不一定代表通透,它意味着关系”(妹岛和世,建筑师)。
就像我并不认识对面五号楼的那家人,但我知道他家正对路口的阳台上,常年趴着一只边牧。挥挥手,它便会机灵地直立起前肢,歪头盯着你,如果主人恰好在一旁打理花草,也会隔着玻璃挥挥手;还有四号楼一层的一对年近八十的老夫妻,在阳台上种了几百盆多肉植物,过路的孩子总是禁不住扒着窗户张望,老两口也并不会觉得厌烦,常常跟大家互动;而一号楼靠西头的六楼,小区里的人都称他们家为“气氛担当”,逢年过节,他们的窗户上准会亮起各式各样的彩灯,今年春节又多了六盏虎头花灯。
现代生活让我们变得看似独立,互联网更是创造了一种一个人就能好好活下去的图景,但与此同时,深刻的现实却不断地提醒我们,个人是无法仅凭一己之力重建意义与尊严的,“当代生活,个人的出路在于关系,我们要重新去构建与社会、与他者的关系”(项飙,社会学家)。
其实,华灯初上,让我们感到希望的不仅仅是“有一盏灯是为我亮起”,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在这一束孤独、渺小的灯光周围,还会有一盏又一盏的灯亮起,在夜晚来临之时,透过一扇扇玻璃窗,这些灯光,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互相映照、互为彼此。
还记得2020年春天的武汉,从一扇没有关上的窗户里飘出的红色窗帘吗?还有意大利那个被隔离在家的小学生,隔着玻璃和其他同学拍下的那张全班合影?正是依赖于由城市构建的空间秩序,我们在这里与他人建立了更多的链接、获得了更多的支撑,也才有了在这里生活的必要。
郑萍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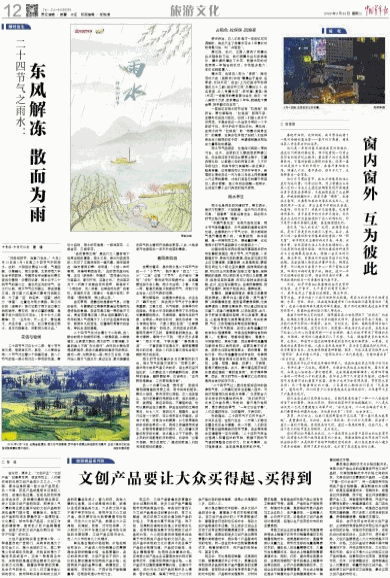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