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你还没忘了Ta吗?那个你暗恋的人,现在还好吗?你是否已经放下?暗恋的故事,有关青春,有关梦想,有关科幻,一一讲给你听。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车的心事(科幻小说)
李霜氤(30岁) 上海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生
“啧啧,这辆车很新啊,就这样报废了。”我听到这样的感叹。
“没办法啊,出现了故障的自动驾驶车,不报废掉,等着害人命?”
“李晓微,你这个设计真的鸡肋,给车加入什么自我意识。结果,这车八成和人一样,走神儿了。现在我又要写事故报告了。以后做事儿,不要想一出是一出。”
“是,郑主任。”
我的人工视觉系统已经被关闭,语音识别系统还工作,知道这些声音属于谁。我当然也可以说话。
我知道其他人都离开了,于是开口,对还留在这里的那个人说:“晓微,这是我的选择。”
那天,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小孩在车道上。在自动驾驶高速车道上,非停车区,人是万万不可进入的。但是,事情就是发生了。孩子个头小,趁着家长不注意,就从护栏的空隙钻进了车道。我看见孩子的家长在护栏外绝望地叫着孩子的名字。只可惜,我知道,最近的道路管理部门,离此处需要步行3分钟。而以我的驾驶速度,1分钟之内就会开到那里。
除非那个孩子自己爬回护栏内,不然,一起事故是无法避免的。
我的法律专家系统告诉我,如果事故发生,责任完全由家长承担,而正常行驶的我,不会有任何麻烦。
可我偏偏选择了麻烦。
我先是减速,再停在道路中间。我打开你存储的音乐——那是你为李乐乐存的,还记得吗?李乐乐是你的女儿,你当初抱着她,开着当时还没有完成自我意识开发的车——就是后来的我,出行,一路上放的就是那些音乐。
我的存储器,从那时候起,就记录了那些音乐。你的一切我都记着。
那个孩子,果然被音乐所吸引,向我爬过来。我打开车门,他就爬进我的车舱内。我打开了你给乐乐准备的防跌撞泡沫装备。
但这是高速路,我不能停留。于是,我再次启动——我已经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我也知道,我违反了《人工智能守则》,未能及时到达约定地点,这是一次故障。
于是,我干脆把孩子送去了最近的警局。
晓微,你用代码给了我自我意识,而你又是我朝夕相处的人。喜欢你,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想要保护你,不仅是你,还有你的家人。那个孩子,和以前的乐乐一般大。如果乐乐遇到危险,你会伤心,这些,我知道。所以我保护了他,如同保护乐乐,如同保护你。这是我的选择。只是不知道,如果我,我是说,作为一辆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车,不能再以生命的形式存在,你会不会难过?
如果会,我很抱歉……
我的视野再次明亮起来。
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
“汽车先生/女士……您好,我代表专家组,对您的到来表示欢迎。由于您救孩子的正义行为,收到了广泛的社会好评。因此,市委成立专家组……”
对方的语气颇为尴尬,如果我是一个人类,我应该已经被誉为英雄。而我是一辆车,一台机器。让机器有自我意识,技术层面可行,但始终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所以,即使是年轻的专家,和一台机器恭敬地说话,也难免有些尴尬。
不管怎样,我还能以生命的形式继续存在,这让我感到些许欣喜。
“李晓微呢?”我问。
“李工程师已经被人工智能专家组破格录取,现在正在外地进修。”
太好了。晓微,我爱的人。我能够继续存在,看着你成就更多的事业。
——————————
林晗君的八年(小说)
冯嘉美(20岁) 武汉晴川学院学生
重庆,一间清吧内。
苏青和驴友们相谈甚欢,她们决定明天就启程从成都进藏,快要离开时,她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来信。
信非常厚,足足24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苏青有些疑惑,重新坐回座位上,用那只纹着希腊文“Ελευθερία”(自由)的手翻开了信。
……
2014年,铁三中的礼堂内,海清一中的话剧社成员为初三学生带来历史剧《一九一九》的表演。
那时,逃课的林晗君才被班主任训斥完,他独自愤闷地走进礼堂,还未落座,却抬眼看到舞台上身穿学生制服的苏青,落日霞光从玻璃窗反射到她的身上,眼睫之间藏纳住稀碎星河,她举起手,一字一句地说着:“取消二十一条!”
林晗君记得话剧落幕后,他冲到后台与苏青的擦肩而过,有种清新又活力的淡淡椰香。
“她是谁?”他问同学。
“苏青,一中话剧社的。”
“那我要考一中。”
254天后,林晗君被海清一中录取,他是他们那届的第一名,在此之前,他是名待优生。
进入话剧社,林晗君再次见到苏青,她的头发长长了不少,整个人倚靠在压腿杆上发着呆,慵懒又美好。
后来他被分到后勤组,和演员组打照面的机会不多。
元旦晚会上。
苏青身穿的裙子因经手好几届,后背处突然掉了扣子散了线,众人在后台看得心惊胆战,直到她中场退下,林晗君第一个冲上前,快速为她缝好。
那时他已经很高了,却弯腰屈膝地完成了一切,并见苏青在如释重负后对他笑道:“谢谢。”
获得这一回眸前,林晗君已经遥望了几百次,他也没想到,这是他第一次拿起针线。
晚会结束后,话剧社众人在空地处放起了烟花。
欢声笑语与油雾气混杂,忽然有人大喊一句:
“苏青!”
苏青转过头来,嘴角弧度不断上扬,瞳孔倒映烟花炸裂的炫丽姿态,同她那时一般惊艳又动人。
林晗君呆在原地,他看见花的绽放,也见证花的去向。
苏青选择了一位学习出众、长相俊朗的男孩。
林晗君鲜少见到他们同往,他不明白爱意要如何绵延,直到发现每次月考,2018届年级第一叫徐应光,第二叫苏青。
他猛然明白,这便是最好的相伴。
高一下的结业典礼上,林晗君被评为“年级优秀进步生”。台下掌声雷动,他从过曝的灯光里看到苏青。
“厉害的小孩,请继续加油。”她为他颁奖,身穿白色主持服,粉嫩唇色极为显眼,是春风拂过的三千桃花,她是之首。
林晗君在奖状背面写下:立最野心的誓言,行最苦难的路途,铸最顽韧的筋骨,做最骁勇的少年。
这是苏青的话。
慢慢地,林晗君成绩稳定,也有知心好友,而目标唯一——追逐苏青。
那是高考前的一个月,苏青剪去长发,变成独来独往的人。林晗君知道,她只是选择了自己想要的方式,他能做的就是在午间休息时往苏青里的储物柜里塞些糖。
“她看起来很普通,你喜欢她什么?”好友问。
“喜欢她是苏青。”
“为什么不追?”
“不能让喜欢束缚了她。”
高考结束,9月新生开学,同欢迎公告牌一并放置的是2018届优秀生录取情况。
“苏青,中国人民大学。”
次年夏天,林晗君收到录取通知书:首都医科大学。
林晗君一直都没有加苏青的联系方式,他和她像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有时突然来了想念,林晗君也只是用QQ去看看她的空间,然后再熟练地删除访客记录。
某天,苏青的空间不再对外开放,个性签名换成了再见。
林晗君疯狂去寻找蛛丝马迹,为什么?最后发现,苏青选择去大凉山支教。
一年后,苏青回到学校准备研究生考试,林晗君在校园墙上匿名写下祝福,很可惜苏青已经不再使用QQ。
……
苏青读完所有的信,感动外更是赞许,林晗君沉默的8年,像士兵的修炼史,他最终跨过荆棘,斩尽百难,成了英勇的将军。
他在追逐苏青的路上,铸造了自己。
苏青这时反应过来,她要去寻找刚才送信的人。
可是山城的路百转千回,人潮汹涌,林晗君早已向某处离去了。
烟火!
苏青转头看,洪崖洞的对岸上空绽放出好几抹炫丽。
她停住脚步,手上掉下一张年旧的奖状,拾起来看,有处更新的字迹:
“苏青,你不必找我,在我望向你的每个瞬间都是我们的重逢。”
冬奥会期间,广西百色出了疫情,大批医务人员前往支援。
首都医科大学的公众号上有本校志愿者名单,苏青从中见到了林晗君。
她猛然想起,高三毕业后自己在网上卖书,有人立马全部买走了,那时她在每本书上都写过自己曾经的目标:首都医科大学。
元宵节的夜晚。
林晗君坐在值班室里吃着速冻汤圆,手机传来一条验证消息。
“你好,我是苏青。”
——————————
谜底
谭鑫(28岁)
会不会有一天
你也会在灯下
翻阅我的心
读着曾为你落笔的悲喜
望着窗外的年华更替
不只是
感激
会不会
合上那本手抄集
有埋怨我
也埋怨某句
只停留于藏头诗的勇气
——————————
缘分就像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王洁(32岁) 宁波财经学院教师
我是在一次书店活动中认识她的。那时我刚刚结束多年自由撰稿的生涯,只身到宁波谋求一份稳定的教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一段全新的生活。刚到宁波不久,当地书店邀请我做一个讲座。我写的是儿童文学,台下大多数听众都是小朋友,大家踊跃又热情,现场闹哄哄的。我对孩子们的提问应接不暇,突然注意到,在人群的最外围有一个高挑又美丽的姑娘,她微笑着注视着我,安静地听完了我的讲座。
讲座结束后,我和她攀谈起来,也就互相认识了。我们一起搭地铁离开书店回市区,地铁车厢内空空荡荡的,没有别的乘客。此前我长年宅家写小说,并不太擅长与女孩子打交道,平时也不修边幅。当她在座位上坐下时,我突然生出了敬畏之心来,似乎挨着她坐是一件粗鲁而冒犯的事情。于是我怯生生地坐到了她对面的座位,列车运行的轰鸣声盖过了我们交谈的声音。她皱起眉头,提高了声音说道:“哎呀,你坐到我旁边来嘛!”我这才敢坐到她的身边,此刻列车驶出地底,穿行在城市的轻轨高架上。我与她并肩坐着,看着车窗外绚烂的霓虹灯一直蔓延到城市的地平线尽头,而她像是这片霓虹光海中唯一的阳光。
这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聊各自工作与求学经历,我也更进一步认识了她。她也姓王,任教于当地的一所高校,周末她会在市郊的一个小花园里教博物学,教小朋友认识草木虫鱼。我在心底暗暗地感叹,她和她的工作就像是童话一样美好。不久,王老师到站了,而我还有好几站的车程。她在下车前为不熟悉路线的我指明了下车的站,并邀请我有空可以去她的小花园看一看。
就这样,我们都回到各自的日常工作中去了。因为多年从事自由职业,早已习惯了死宅写作,所以初入职场时我并不适应,教学工作和人际关系都让我心力交瘁,无暇他顾。虽然和王老师也有微信联系,但是到我真正造访她的小花园已经是初夏了。
那天我打车来到市郊,在一座小镇里绕了许久,才找到了那个小小的花园。此刻正值夏日,阳光充盈,园子里郁郁葱葱。树阴和繁花掩映着小屋的窗口,王老师身着一袭淡黄色连衣裙,站在窗边给孩子们上课。我对她微笑点点头,悄悄坐到小教室后排的空座上旁听。
她拈着一株野草,告诉孩子们这是《诗经》中的卷耳,两千多年前诗卷里的草木,现在仍然在我们脚下生长。她说起这些热爱的植物时,眼睛中洋溢着星辰般的光辉,美丽得不可方物。我沉迷于看她说话,两节课下来也没记得她说了什么。
课后我们一起吃了午餐,愉快地聊起各自的生活,似乎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只可惜故事并没有“未完待续”的注脚。在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得知了她脱单的消息,冬天时在朋友圈看到她披上了婚纱。这是我漂泊在异乡第一次感到失落,但也只能将感情深藏在心底。感慨缘分就像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春生秋落,悄然凋零。
对一个年逾三十的单身男人来说,像中学生那样暗恋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时常想,喜欢上她并无独特的理由,她的颜值足以让任何男人陷入爱恋。我独自一人在异乡,亲人故友都不在身边,教学工作令人疲惫不堪,所以她对于我,更像是这座陌生城市里的一个支点,混沌生活中的一束光。生活中总得觅得一丝微曦的存在,让人在漂泊中收获些许的暖意。想起我们从认识之初就一直互称“王老师”,始终保持着礼貌的距离。我会寄给她我新出版的小说,她也会回复我她的阅读感受。如是这般,也挺好的。
——————————
那个夜晚我们坐在一起
陈渌煜(23岁)
我们一起坐着
灯光因为我们亮着
又给漆黑的夜晚
增添一寸光明
黑夜,被挤到屋外
我们被星星监视
这种光明成为众矢之的
但彼此眼中只有对方
不管有多少人议论我们
我们还是慢慢交谈
天地像是一间展厅
之后我离去
交换彼此磨旧的神情
我走在路上
以后你可能将我赞扬
也可能把我批评,未来
你会不会成为我的陌生人
而我则会去猜测
当你伤心时
究竟会对着别人给我安上
什么罪名?
——————————
星空中的相片(科幻小说)
陈凯誉(21岁) 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学生
独角兽黑洞空间站里,陈长安蜷缩在胶囊舱背后,沉重地喘息着,剧烈的心跳声似乎要撕裂胸腔。
还有一个舱室,还有三分钟。
他手里紧紧护着一张相片,相片里是一棵樱花树,树下是他自己和一个女生。这张相片记录了他和她最快乐的时光,却也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为致命的证据。在这个时代,违背基因准则的爱情,是人们最为不齿的行为。
太空舱内红色的光芒交替闪烁,警报声像是最无助的婴儿在哭啼。空气若有形的丝线般从陈长安的鼻腔抽离,胸腔仿佛在和整个空间站争夺呼吸。这就像是在太空中漂浮着的铁罐头,背向黑洞,无依无靠,孤立无援。
一切都好似在片刻间便发生,当执法者开启舱门的那一刻,他就已然成了瓮中之鳖。探测犬切断了阀门,氧气含量和气压迅速下降,三分钟后若没有接上操作服的供氧设备,自己甚至都撑不到被逮捕,只有死路一条。他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证在地球上的她,是否还平安无事。
他的耳机里接入了探测犬毫无感情的电子音:“编号0307,陈长安,请立即前往一号舱室与执法者汇合。重复,请立即前往一号舱室与执法者汇合。”鬼才去。陈长安把相片揣进衣服的外兜,艰难地扶着舱壁站了起来。穿上操作服,再另作打算。他边想着,边扭开了下一级舱体的门闸。
门闸大开,一阵风卷着凉意扑面而来,令他一阵恍惚。朦胧间操作台上似乎扎根生长出了一株樱花树,花瓣纷纷扬扬铺满了地板,踩上去软乎乎的。入眼尽是绿意盎然,仿佛又回到了在地球上郊游的那天。他莫名间又感觉骄阳似火,在草坪上汗流浃背。陈长安喘息着,突然打了个寒战。
非必要情况不得损毁空间站,这是执法者恪守的准则。他们操作总控系统降低了前几个舱室的氧含量,又向操作服所在舱室大量充氧,把陈长安完完全全逼入死路。
周围的景象如潮水般褪去,没有樱花,没有草坪。他想往前迈出一步,却迎面撞上了操作服的撑架。扑倒在地,颤抖的双手连支撑起躯体都变得异常艰难。
身处在与世隔绝的太空囚牢里,陈长安遭受了生平第一次高浓度氧中毒。
在这里,他无处可逃。
“啊……啊……”随着口腔逐渐麻木,他连吐字都变得断断续续。趴在翻倒的操作服上,陈长安的肌肉开始出现“自己的想法”,左手伸进右袖,右手在空中挥舞。眼前像蒙上了一层雾,反胃的感觉也随之袭来。
而就在手忙脚乱的时候,相片却从外衣滑落,飘在了一旁。
顾不上那么多,仿佛在刹那间经历了数百年,陈长安终于把自己塞进了狭小的操作服内。空气灌入头盔,顺着呼吸道涌入肺脏,将浓氧裹挟而出,暂时驱走了他脑中的混乱与痛苦。余光瞥到地面上的相片,看到女孩灿烂阳光地笑,令他心头一痛。
上一级的门闸在这时传来扭动的金属声响,陈长安一惊。他抄起相片,望向无垠的太空,内心充满不甘。爱情在这个时代宛如毒品,哪怕是逃到视界线的尽头也无济于事。一切与此有关的人与物都要被销毁。只有几立方米的空间,藏又能藏到哪儿去呢?
“咯啦”,门闸的安全锁轻轻落下。
执法者踏入舱室,却没能找到陈长安的身影。撑架像是最后一根拦路石横在地上,上面的操作服不翼而飞。他站在舱室中央,看着周围残留下的挣扎痕迹,沉默不语。
舷窗外一道光芒闪过,那是物体坠入黑洞爆发的辐射。
执法者猛地冲向窗前,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不在近处,而在远处,远到天边一般的地方。
黑洞视界。
陈长安携带着那张能证明自己所爱的相片,逃进了黑洞。在被引力无限拖慢的时间中,他和她的相片,随着他一同化为了永恒。
“既然我不能凭借一己之力保护好这段感情,那就麻烦宇宙帮一下忙。”陈长安想。从某种角度上讲,执法者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但从另一种角度思考,执法者已经永远都完成不了这项任务了。
这段爱情将永远不会被抹消,只要黑洞明天还在。
——————————
寂静之心(小说)
倪天佶(27岁)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6月18日,距离毕业生最晚离校期限倒计时3天。
语凝整理好行李箱,锁上门,看了一眼手表。此时正值13:00,距离高铁出发不到2小时,扣除路上和检票花费的1.5个小时,她还剩下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在最后半小时里,她选择去见一个人。那是她在图书馆自习室里认识的男孩,只是,她不知道他的专业、年龄,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图书馆是回字形建筑,中间是镂空的环形楼梯,自习室排布在外圈,走道和自习室隔着一道磨砂玻璃。如果一直站着会很尴尬,语凝只能绕圈走,装作漫不经心地散步。绕一圈的时间是1分30秒,男孩出现在视线中的时间是5秒。
13:15,语凝开始绕第一圈,心中五味杂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他的呢?可能是看到他捡起地上的纸团藏在掌心?看他每天离开座位时小心翼翼将椅子归位?他温柔、开朗、阳光,好像和每一个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想到这个空间里有他在,就会格外安心。
13:16,第二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呢?语凝回忆:好像是那一天,自己一个人蹲在储物间里哭,他递过来一张纸巾,不多问,静静待着,听自己絮絮叨叨。他只是耐心地听,肯定她的感受,不做评价。那一刻的相互理解,胜过很多人耳鬓厮磨几十年。
13:18,第三圈,“要不还是去问个微信号吧,就这样离开,怪可惜的。”但她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就算认识了又怎么样呢?我们会在微信上聊天,约出来吃饭,看电影,也许会相爱、结婚——和所有普通的情侣一样。最后,再多的热情也会归于寂静。
最后5秒,男孩还是保持着一个姿势看书,没有回头。
算了,就到这里吧。今天又看了他15秒,已经够奢侈了。语凝轻轻笑了,对自己说:他很好,非常好,对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不要自作多情。现实不是戏剧,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
6月18日清晨,江赦林起床后开始洗头,他在手上倒了厚厚的洗发露,认真洗了三遍。这是他离开这个学校的倒数第三天,今天,他要去向自己喜欢的女孩告别。
很久以前,从女孩走进自习室的那一刹那,江赦林就注意到了。她的头发很长,乌亮亮的,喜欢穿绿色连衣裙,走起路来很轻盈,像夏天的薄荷。她做什么都很认真,看书很认真,玩手机也很认真。她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去食堂,一个人来学习,没有见过她大笑的样子,表情淡淡的,好像周遭世界与她无关。他总是忍不住想到她,在喧闹的火锅店里、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在每一个开心或者落寞的时分,他都在想念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江赦林开始期待每一天的清晨,期待着去图书馆,做什么都特别有动力。
很多次,江赦林都忍不住想前去搭话,邀请她一起去食堂,可是转念又想:如果她喜欢一个人待着,我就应该尊重她。遂作罢。前几天,他看到女孩蹲在地上哭,想上前说些安慰的话,却紧张得哑口无言,只能递上一张纸巾。后来,女孩主动和自己说了话,不止一句,是很多句!他高兴极了,那是他入学四年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到了离校前,江赦林决定还是和女孩好好地道别,他不想表白,也不想索求什么关系,他不想让她有任何的负担,甚至连“希望你快乐”都说不出口——我只是一个路人,人家又凭什么要承受我的期待呢。所以只是道别,仅此而已。可是直到闭馆音乐响起,江赦林还是没有等到女孩,他安慰自己:“或许明天她会来呢?”
6月20日,毕业生全部离校,他们拥抱、合影、告别。这是很多人彼此人生中的最后一面。图书馆二楼的留言墙上,有人提问:“友友们,你们觉得爱是什么?”回复形形色色,有人说:爱是陪伴、理解、包容,有人说:爱是放手,是成全。还有一行清丽的字迹:爱是怦然心动后的寂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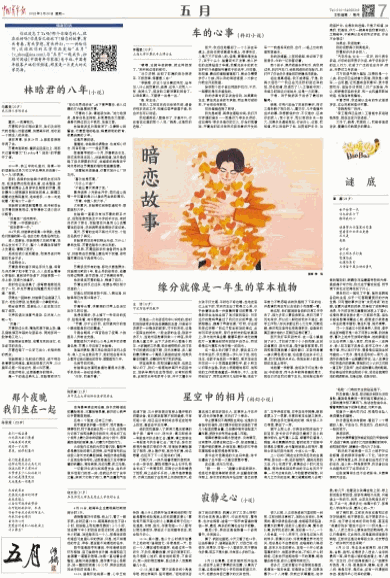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