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曹海琴被按下暂停键。
2020年8月,她患上乳腺癌,经历了两次手术,4次化疗。治疗过程中,她身体的每个关节都在疼痛,“仿佛被灌上水泥,要将关节撑开爆裂”。吃饭“成了一件恐惧的事情”,每天早上醒来,她都觉得恶心,口中又咸又涩,刷牙的自来水含在嘴里如同盐水。
生病期间,她胖了十几斤,颧骨发黑,头发剃光,左侧乳房被切除重建,“就像把一个包子的馅全部拿掉。”
而在这之前,她不允许自己体重超重,衣服永远鲜艳如新。她的人生像她的外形一样“完美”:在高校工作9年,她读博4年,又用5年时间完成博士后出站,其间,她还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儿童礼仪讲师,后来加入秦皇岛一家教育培训学校,成为教研负责人,教授阅读写作课。
生病时,她正沉浸在创业的激情中,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最忙时两分钟吃一顿饭,“像机器一样运转”。那时她认为做一顿饭、收拾家务是浪费时间,连陪伴孩子也是一种义务。
直到生病,她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在攀登,以至于“脚离开了地面”。
三十难立
医院的病理诊断报告出来时,曹海琴正在学校开会。看到报告上的“浸润性导管癌,组织学II级”,她瞬间全身冰冷,闪过几个念头:严重吗?我还能活多久?孩子怎么办?父母怎么办?
胡乱想了一会,她把结果一一通知爱人、朋友。当天下午,她如常上了一门线上写作课,讲到兴起,还给孩子唱了几句。
那时,她想的是:病来了,我就应对。
住院前一晚,她穿着紧身上衣,留着齐肩短发,和全家人微笑合影,带上几本书,收拾衣服前往天津肿瘤医院。面对来势汹汹的疾病,她一无所知,录制了一段音频给儿子,“像是说遗言”。
“有人说,肿瘤的形成至少需要10年。”2020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曹海琴回看过去10年,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在“攻克任务”的自己,而10年前的她,正处在“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候。”
那一年,她30岁,在秦皇岛一所大学做了4年辅导员。
她给学生的印象是“阳光、亲切”。一名新生记得,去学校第一天报到,看到她将一件薄毛衫的袖子系在前胸,“整个人在发光。当时我就觉得,我可以在这里读大学。”
她用20多天记住了136个学生的名字,对很多学生的记忆细致到县,家里几口人。学校要求寄成绩单给家长,她给每个学生家长写信,表扬学生的优点,有挂科的说明原因,鼓励学生。
如今,曹海琴回想起来,那时的自己跟很多人比是幸福的:工作稳定,婚姻美满,刚生下宝宝,衣食无忧。但当时她“盯着班上最上面的那几个人看”,发现同学有读博的,有出书的,还有年入百万的,反观自己,“没有一样东西拿得出手。”
站在三十而立的节点,曹海琴感到焦虑,“老觉得自己没立住。”
思前想后,她决定读在职博士。至于是否继续读以前的法学专业,她并不在意,“只要是文科专业的就行。”而博士毕业后,她就能转为一名专职教师,也不用再坐班。
她不喜欢坐班,尤其厌烦统计各种学生表格,查宿舍,值夜班。相比那些“纯事务性的工作”,她更喜欢教育工作,“做表这个事不是教育,影响人是教育。”
当时班上有个男孩自称“问题少年”,额头上系一条黑发带,发型冲上,攻击性强。一个初秋的黄昏,她在走廊里遇到男孩,听男孩讲家里的情况。
男孩说,那天她既没有表现同情,也没有表示出冷漠,这种态度给了他安全感。后来,男孩每个星期都拿一个本子找她,让她提建议,记下来,跟着照做。她鼓励男孩阅读,4年中,男孩写下6万多字的读书笔记。
“这个行业特别迷人,总能发生生命之间的深度连接。”进入学校的第二个学期,因为思政课缺老师,学校让曹海琴救急。从没讲过课的她硬着头皮,去图书馆搬来一摞书,研究怎么讲课。
她常常在人人网和学生互动。一次,一个学生给她留言,“我可能一直坐在角落,也没有老师的联系方式,但老师不经意说的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
“这给我触动很大,原来老师的角色这么重要。”曹海琴发现自己很喜欢讲课,读博后,她开始了在高铁上备课的生活,一边在秦皇岛给学生上课,一边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
那是她至今回忆的幸福时光。“见识、思维都有提高,我会觉得人生不断在升维,它可以帮我对抗很多焦虑。”
她常常去学校对面的剧场看话剧,演出结束后,夏夜,她和朋友一路吹着晚风,走向地铁站,兴奋地交流演出内容。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她去人艺看戏,去国家美术馆看展览,去正乙祠古戏楼听昆曲,尽管听不懂昆曲,但她觉得唱词美,舞台的扮相也美。
她大量阅读社科人文书籍,并如愿转为专职教师,踩着高跟鞋,穿着精心搭配的衣服,给学生讲授专业课。
如今,还有学生记得她的课。一个学生留言,在一节有关“爱国”的主题讨论中,老师讲述了借保钓为名而行伤人之实的事例,引导他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爱国”,“这让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学会独立思考。”
不少学生对她组织的辩论课印象深刻。一个学生记得,在一次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辩论中,班级中充满了“碰撞和兴奋”,但一名同学认为不该公开讨论这种话题,曹海琴便让这名同学做记录员。
教学期间,曹海琴还参与创办了读书会。每到周末,不同专业学生聚在桌前,啃读《社会契约论》《论语》等经典作品。
读书会办了7年,很多学生还与她保持着联系。一名毕业多年的学生说,当年读过什么书、讨论过什么话题,他已经很难想起来,但那些深谈的夜晚慰藉了他,“它不是中心化的讲学论坛,也不是以读书为名显示自己与俗流不同的伪社团,它让我有一个平台畅所欲言,让我知道还有很多人也认为读书和思考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精神需求在这个社会中是需要的。”
那也是曹海琴的精神家园。她喜欢和“小朋友”交流,一起成长,“那是一种深度的人际关系,是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是在做着关照灵魂的事情。”
“希望自己能不懈怠,不盲从,不媚上,亦不媚下。”曹海琴常常告诫自己,做教师,要警惕因为学识和地位优势而产生的傲慢,警惕倚老卖老的停滞不前,更要警惕“我受学生欢迎”的虚荣心。
证明
曹海琴想过,假如当初继续留在高校教书,不参与创业,可能身体不会累垮。
为了治病,她在北京进行了四期化疗。化疗导致白细胞下降,需要打升白针,每次打完后三四个小时,曹海琴感觉全身疼痛,只能卧床,“翻身都要用尽力气”。
好不容易盼到白细胞上来,转氨酶又高了,她不得不进行保肝治疗,“每天都有无数的细节提醒你,你是个病人,不要有企图过正常生活的非分之想。”
最后一次手术醒来时,她几乎被“冻”住,全身处于瘫痪状态,只有食指能微微动。
医生担心是合并格林巴利综合征,一种凶险的术后并发症。只有曹海琴知道,是老毛病“周期性麻痹”又犯了。这是一种以骨骼肌弛缓性瘫痪为主要表现、反复发作的疾病,持续时间大多在10天以上。
从1岁多起,曹海琴就与这种病共存。她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孩子,长辈曾因为她是女孩而失落,父母忙于工作,和她关系疏离。她很早学会砍价买菜、做饭,因为一双质量不过关的拖鞋独自与卖家理论。
对于这种先天性疾病,家人早已习以为常。小时候曹海琴每次患病,父母就把饭和尿盆放在床边,然后去上班。
她记得六七岁时无助的自己:独自躺在炕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吃力地一点点挪动身体去吃饭、方便,等待身体慢慢复苏。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愤恨命运不公,“为什么我不是个健康的孩子?爸妈为什么要生下我?生了我,在我这么难受的时候,又不管我。”上小学时,她没有把生病的事告诉老师和同学,由于身体虚弱,她体育课总是跑得最慢,招来同学的嘲笑。
“我很希望能够在一些方面证明自己。”但她找不到证明自己的路。上大一时,她疯狂参加学生社团、学生会,报各种竞赛,去图书馆看书。听亲戚们说吉林大学好,她努着劲考上了吉林大学研究生。
24岁,她结婚了,因为爱人并不介意她的疾病,“给我很大的安定感。”
但婚姻不能让她证明自己。她在焦虑中读了博士,成为专职教师。那几年,她觉得自己“时时刻刻在进步”,焦虑感大大减轻。
最让她忧虑的是儿子。儿子两三岁时,突然抗拒和人交流,出去吃饭见人躲避,看到玩耍的同龄人,也会哭着把头埋进妈妈怀里。
曹海琴带孩子去医院,排除了自闭症。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她开始阅读心理学著作,翻找和儿子情况类似的案例,意识到儿子的胆怯恐惧,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她把孩子带出门,但不逼迫孩子和人问好,“给他空间,在他尚未彻底放松时,让他先做一个安静的旁观者。”儿子在她的引导下渐渐变得开朗。
生活也许就这样过下去了。但到了2015年,曹海琴的教学岗位发生变化,她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境地。
当时35岁的曹海琴再次问自己30岁时的问题,立没立?答案是没有。
“心里有个很强的声音,对自己不满意。”当时,她抱着试试的心态去参加博士后面试,幸运通过。
她研究的方向转为宪法学,因为导师中途退休,研究方向再次转变,“跨度挺大,对我来说有点吃力。”
那时,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研究机构的研究员,集中精力发够论文,但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如愿。
她又开始找别的路,每年花几万元学习,上形象顾问课、礼仪培训课、商务写作课、快速阅读课,还报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但她仍然找不到自己的“独特价值”,“我热爱写作,但我不是个好作者。我每年写十余万字的学术论文,但是回看那些论文,觉得不忍卒读。我也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形象顾问,远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
她寻找自己的独特之处:热爱阅读,懂得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也是一名探索如何爱孩子的母亲。她找到新的努力方向:通过研读心理学经典,教人如何提升爱的能力。
她阅读了近百本心理类书籍,定期在自己开的公号更新文章,讲亲子关系,她组建成长社群,举办公益沙龙。
有家长告诉她,自己学会了控制情绪,尊重孩子。还有家长听完课程后反思,“很多时候我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把孩子当成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以爱的名义绑架孩子。”
“做家庭教育真的能让世界变好,能教会一个家庭妥善对待孩子。”她渐渐将重心转为家庭教育。
裹挟
就在她探索新的路时,2018年年末,一个朋友说想建立一家国学培训教育机构,邀请她加入。
当时,曹海琴正在给孩子挑选人文素养课程,研究了市面上很多的课程,都不满意。加上央视诗词大会等节目热播,国学大热,曹海琴觉得国学教育前景向好,决定加入。
“因为有读书会的互相滋养,我们觉得如果把对人的影响力前置,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他们给机构起名为“启文书院”,“启之以文,约之以礼。”
曹海琴准备后半生“专注于这项事业”,“教家长如何温和坚定地爱孩子。”
在那一年的年终总结里,曹海琴说,将“开启一份有意义的事业”。她在深圳的“罗振宇跨年演讲”现场度过了2018年的最后一天,穿着礼服,张开双臂,和演讲海报合影,海报上写着“时间的朋友”。
那时的她对未来充满展望,在微博写下未来十年的梦想清单,包括生二宝、开花店、开心理工作室、学画画和乐器、学习潜水、考取飞行执照、每年出一本书,以及,腰围始终保持目前尺寸。
生病后,她又转发了那条微博,梦想清单变成了“好好活着。好好陪伴亲人,让爱我的人们安心。”
在她最忙碌的时期,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每天四五点起床工作,只有几分钟吃饭时间,有一次忙到连鞋底断了都浑然不觉。
生病后,再看这段路,曹海琴觉得“步子迈得太快了”。最初,他们以为只是开一个“低幼版读书会”,创业后才意识到这事不简单,“要考虑人工、房租、管理、消防……方方面面。”
2019年春天,书院开业,邀请他们创业的朋友负责日常运营,曹海琴和另一位老师主攻教学。
不久,那位朋友因故退出。后来,一位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朋友觉得这个行业前景好,又加入进来,负责运营。
这位朋友将书院带入企业模式,他们制定的商业版图是:尽快研发出成熟的课程,然后进行模式复制,还要加大招生规模,尽快实现盈利。
原本一直在法学、政治学领域打转的曹海琴又啃了200多本有关阅读写作的书,研发适合学生的课程,并每周给十几位兼职教师培训阅读课。她还要每周给家长开家庭公益课,作为报名的增值服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来,为了让机构活下去,她将线下课转到线上,开公益直播课。
实际上,她一直播,就手脚冰凉,这源于小时候对容貌的不自信。每晚直播前,她从中午就开始紧张,直播时要反复看讲稿,但她不允许自己“矫情”往后缩,连续做了几十场直播。
“我觉得自己可棒了。”她一度迷恋这种“超级自律”的状态,陪儿子时想着备课,吃饭时想着直播。
那时,她心里始终回荡着一个声音,“要干出个样子,给那些退出的伙伴看看。”
“我把目标看得过重,无形中把人异化,被裹挟到工具性的节奏里。”她反省自己,“一个人没有真正建立起自信的时候,就要去找证明。我太着急自我实现。太贪心了。”
她一边录制线上课程,一边做博士后出站报告,工作越堆越多,每天忙到晚上11点回家。
到了2020年5月,曹海琴感觉越来越累,越来越爱喝冰咖啡,每天早上只能勉强睁开眼,挣扎着起床,后背发沉,胸部隐隐作痛。
那时,她已经一年多没有体检,“觉得出不了什么事。”她又去广州学习家庭教育相关的课程,直到8月,才抽出时间体检。
那次去体检,还是她为陪婆婆看病去的医院。“我对婆婆真诚的关心救了我一命。”
暂停
相比疾病对身体的摧残,曹海琴感受更深的,是疾病带来的无力感和孤独感。有一次,她去做加强核磁检查,检查后回到观察室,一手扎着针,一手拿东西,从柜子里拿红色的长外套,想给自己披上。
但从各个角度拽了好多次,怎么也披不上。外套滑落在地,一旁的护士一动不动。
曹海琴站在核磁室的长椅边,突然哭了。那是她第一次因为生病落泪。
看到病理结果时,她没流泪,还如常上完当天最后一节课。手术前后,她也没流泪,每天“乐滋滋”给病友做心理疏导,但披不上衣服的那个瞬间,她“被深深的孤独击中”,“这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面对疾病,面对生活,是一种铺天盖地的苍凉。”
回到病房后,她以玩笑的口吻跟病友说,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说完又恢复笑容。
她习惯了照顾别人的情绪。在大学当老师时,她会偶然给失眠的同学送红酒,给想吃西瓜的学生榨一杯西瓜汁,开导考研不顺的学生。生病时,有人说想吃鸡肉,她不动声色买来分享,有病友刚入住时,看到一群光头大哭,她走过去开导。
“我唯独没有善待过自己。”她后来反思。
是亲友的关爱帮助她挺过这段“至暗时光”。两个朋友放下工作和孩子,专程去医院照顾她,每天帮她擦身、洗脚,抱着她去卫生间。婆婆每餐给她准备七八种食物,养护她的胃。学生给她送日历、香薰、鲜花、假发。
“他们让我觉得没活够”。治疗中,由于激素的作用,曹海琴胖了十几斤,五官变形,脱发严重,每天清晨起来,枕头上都是黑黑一层。
最后一次化疗,她患上荨麻疹,全身遍布红色斑块,满身灼烧感,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线,像一只“讨人厌的红蟾蜍”。
但她仍要求自己保持美的姿态。每次外出检查前,她要穿自己的衣服,画上口红,戴上耳环。手术前一天晚上,她还在敷面膜,“这是一种仪式感,是向疾病宣战,你打不死我。”
在剃头这件事上,她也做足了仪式感:请来好友,有的负责剃头和化妆,有的负责拍照。“当年是我把你的长发盘起,今天,也是我把你的头发剃光。”好友哽咽。儿子看见她的样子,也背过身去抹眼泪。
曹海琴没有哭,因为她“作足了思想准备”。一张照片里,她穿着红色毛衣和一身深蓝色套裙,光着头,昂首微笑。
回望生病前的10年,曹海琴感觉自己始终在追逐“彼岸”,没法安定下来,“这个‘彼岸’,有时候是镜花水月的情感,有时候是青面獠牙的恐惧,更多时候,是光怪陆离的目标。”
借助这次疾病,她反而实现了“自由的特权”,“可以不读书不写作不思考不起床”。她的人生减速下来,有了大把时光看脱口秀、听相声、追宫斗剧、看农村美食博主里的人间烟火。有时候,她干脆用一个下午看日影在房间里舞动。
她开始认真品味美食。有一次,家人给她做了三鲜水饺,本来担心吃了呕吐,但咬开饺子皮,她闻到诱人清香,入口顿觉鲜美,“以前吃饭只为活着,哪里有这样的感受。”
很多被尘封的触觉在慢慢复苏。两次手术后,她感觉自己“像是被恶魔封印,无力支配肢体,被牢牢禁锢在床上”,当每一次可以翻身、拿勺子、自主站立、洗头,她都感到由衷欣喜,“以前从来不知道,快乐和满足可以这么简单。”
她意识到,自己奔跑多年,忘了安于当下。
“安于当下有很多层面,比如春天有没有认真去听鸟鸣,看树叶怎样从新绿到日渐浓密,有没有感受吹拂脸颊的风一天天暖起来?感受到脚踩的大地温度有变化?安于当下特别安慰人,抵御内卷,因为你眼睛一直看得不到的东西,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我还不行。”
以前,她看不起这些日常,但现在佩服那些“能把日子过好的人”,“哪怕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因为人说到底是要过日子的。”
她买来花土花盆,收集好种子,种入土里。看着幼嫩的小苗一天天破土而出,她想起苏东坡谪放黄州时,寻得一块土地,日夜劳作,播种收获,他说“自喜渐不为人识”,“不是别人不认识你,而是你自己相信其实不需要被别人认识。”
她越来越喜欢苏轼,“虽未曾体验稼穑艰难,也有了扎根于大地的扎实之感。”
医院走廊里有几盆绿植,曹海琴给它们一一取名,兰花叫“慵整纤纤手”,白掌花叫“画船听雨眠”,还有一盆观叶植物,她给取名“少奶奶”,那也是对切除乳腺的患者的别称,“不跟其他花争奇斗艳,只是默默碧绿。”
生病期间,书院的学生给她写信,希望她早日回去。她开玩笑,“一定要努力康复,长命百岁,为孩子们多提供点写作素材。”
重生
2021年3月,曹海琴结束了治疗,但她的身体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
她的一侧乳房被切除再造,掏空之后被装上硅胶,冬天时从室外回到室内,身体是热的,只有那只乳房是凉的。
出院时,医生告诉她,为了防止上肢出现淋巴水肿,不能抱孩子,炒菜不能颠勺。还有病友说,不能开车,“怕方向盘打猛了,影响手臂。”吃饭也不能无所顾忌,她要严格控糖,不能吃烧烤,不能吃腌制类食物。
如今,光是吃药,每个月花费1万多元,而自从她进行博士后研究,已将近7年没有稳定收入。有病友给她介绍干细胞治疗,一针10万元,需要6针,说能降低复发率。曹海琴没敢问,“我只是想稳稳当当活在当下,怎么就需要这么大开销?”
生病之后,曹海琴总在想“为什么是我”,“一定是我的生活里有喂养癌细胞的土壤,如果不把土壤铲除,那就意味着可能还是我。”
反思是痛苦的。有一天晚上,像是被触发了开关,曹海琴哭了两个多小时,“我不够爱我自己。”
“我特别舍得为别人付出”,这为她积攒了很多珍贵的情感,但她知道,付出的另一面是“恐惧”,“心里始终得到的爱不够,就会用多付出的这种方法试图来换取别人给予更多的爱。”
她意识到,自己内心一直是那个躺在床上,等待身体复苏的六七岁小女孩,“自卑、敏感、脆弱,需要被呵护,渴望被宠爱。”但外在的她不停给内在的自己提要求,要向前走,要活得体面,“成为一个让别人看得到的人”。
即使“小女孩”已经多次向她求救,在她直播紧张得手脚冰凉时,在她累得腰酸背痛时,但她发出命令,“怕什么怕,给我上。”“作为她的‘外在父母’,我对她比对谁都残忍。”
现在,为了活下去,她必须学着关注自己的感受。她有脾气了,遇到朋友圈不高兴的人,就拉黑对方。听到不高兴的话,该怼就怼。适当抱怨,她认为也无可厚非。
她的心境投射在一朵粉灿灿的芍药花中。刘禹锡认为芍药花“妖无格”,她不以为然,“关你何事?只要我欢喜,我就这样开,至少没有辜负这年华。”
她仍想自我实现,认为“大劫大难之后,人不该失去锐气,不该失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你平稳了,更加浩荡。”
只是,她的精力大不如从前,深度思考能力变差,打开书却刷起了手机,想写文章却聊起了微信,直播一小会就感到身体虚弱。
有时,她仍然会感到焦虑。对待焦虑,她认为应该像站在站台上看火车,“你只需要看到它,让它呼啸而过,但不会被它带走。”
朋友们都觉得,她更放松了。以前准备直播,她要反复磨课件,认真化妆,还要两个人配合,“负担很重。”最近,她简单化妆,在椅子上一坐,就开始对着手机直播,“反正也都有美颜。”
她将家庭教育视为后半生的事业,“向上够着天这条路对我而言希望不大,我就踏踏实实把脚踩到地上,把更多小孩接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她仍然关注公共事务,呼吁关注空难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转发上海疫情期间,骨癌化疗病人的求助信息,给素不相识的病人捐款。2022年3月,她应邀为天津市肿瘤医院乳房再造科的病友做分享,讲述一年多的心路历程,告诉更多病友“学会爱自己”。
“现在大多数人都不懂得善待自己,我们整个社会把人生硬画成一条线,尤其成功女性,好像就得事业有成,貌美如花,不能胖,不能老,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自我,就被带跑了。要去探索如何在这个时代中有一个妥善的位置自处。”在鬼门关走过一遭后,曹海琴觉得,“能多活10年,能让生命变长,什么都来得及。”
治疗初期,她想过自己的墓志铭,有“来了,爱过”,还有“我先走,你们接着”,但想来想去都不满意。她还想过提前举办悼念会,把亲朋好友都叫来,让大家把想对她说的话提前说完。幸运的是,这些设想都没派上用场。
她又有了一头茂密的头发,刚长起来那两天,头顶是一层薄而均匀的淡黑色,摸起来轻盈柔软,她说:“像有许多只蝴蝶在扇动翅膀,又像婴儿的胎毛,温柔而充满活力。”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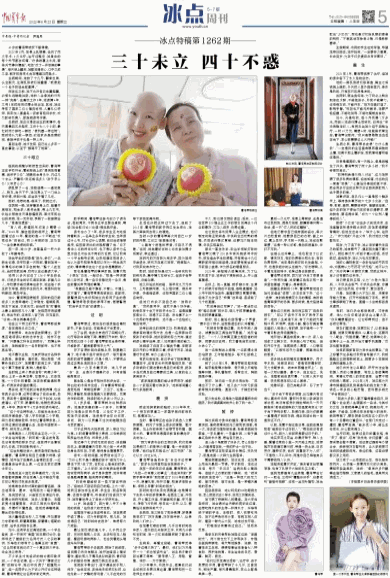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