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以海洋为媒介,没有明确的线路实体,但古人以一种悲壮的方式,把贸易的载体“船”,留在了这条航路的不同海域中。对不同海域、不同时间的沉船进行考古发掘研究,将这些点串联成线,这条线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我的一生,就是在将这一个个点接通成线。
作为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我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唯一幸运的是,我的年龄刚好和水下考古的发展节点同步。
我出生于1962年,也是在那个年代,现代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开始把便携式呼吸器应用到水下考古工作中,水下考古正式诞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现了古沉船“南海Ⅰ号”,开始筹备组建水下考古队。当时年纪大的考古工作者没有机会学习潜水,年纪小的又没赶上,我很幸运。
18岁到博物馆工作
水下考古的“黄埔一期”
我在广州出生长大,1980年高中毕业,就到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在广州的一个古建开放点——光孝寺,我当了4年讲解员,工作期间又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了一个在职本科。拿到学位以后,就转到博物馆的文博研究室当秘书,跟着那些老专家们转。
1985年,我跟着参加了一个考古发掘项目,就不爱在研究室坐着了。那时候年轻,觉得考古可以跑野外,满足我的探索欲和好奇心,于是就跑到了考古队。我正式参与的第一个考古发掘是石峡遗址,做了三个月,觉得很有意思;1987年夏到1988年年初,我又参与了乐昌古墓群的发掘,200多座古墓,基本是我一个人盯过来的。就这样在实践中,我对考古的理解越来越清晰。
1987年,沉船“南海Ⅰ号”被发现,当时广州救捞局把发现的文物移交给了广东省博物馆。我参与了接收文物,但当时完全没有水下考古的概念,只知道在南海发现了一艘沉船。
发现“南海Ⅰ号”以后,国家很快成立了一个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并开始做人才储备:一方面是“走出去”,把人送到国外去学;另一方面是“请进来”,1987年年底,请了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先生,到北京办水下考古培训班,讲了一个星期的课,我就是赶上了那一批。
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在理论上有了一些概念,知道什么是水下考古、怎么做水下考古,但还是觉得沉船、潜水,都是很遥远的事情。
没想到1988年3月,国家就办了一个水下考古潜水培训班。当时大家算了一笔账:让潜水员学考古,还是让考古人员学潜水?潜水员学考古要花4年,考古人员去学潜水只要花半年。中国有这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找几个去学潜水并不难。当时有三个报名的条件:一是年轻,不超过35岁;二是要从事考古工作;三是身体条件合格,尤其是心肺功能好。这三个条件我都满足。
我从小喜欢游泳,1986年在珠海做岛屿调查,有一次在庙湾岛,我跟当时的领队说:“我想从山这边游到码头去,走过去太远了。”领队开玩笑:“那你给我写个保证,出了问题跟我没关系。”我一听这话,应该是不想让我去游,就放弃了。后来听说国家要办水下考古潜水培训班,她专门来跟我说:“你不是想游泳吗,去学水下考古吧。”我就真的去了。
1988年3月到5月,我们在交通部广州潜水学校参加正式的轻潜水培训。从一个2米多深的游泳池开始练,之后又转移到潜水塔,3个月之内要下潜到40米。当时有9个学员,包括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这就是大家认可的水下考古的“黄埔一期”,算是中国水下考古的科班。
学校当时用的是一套国产的潜水设备,非常简陋,呼吸阻力大,安全性也不高。1988年6月,我们参加了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摸,在广东吴川考察一艘古代沉船。当时所有的潜水设备,除了一套轻潜装具外,其余的气瓶、呼吸器、面罩、脚蹼、压铅等,都是从湛江潜水运动学校租借的。
1989年,我们又在青岛参加了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水下考古培训班,有澳大利亚的老师来培训,用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先进设备。拿着英文教材和录像学了4个月后,我们发现国情不同,他们是在水质较好、能见度很高的环境下发掘,和我们的现有水质差别较大。
1989年年底,国家博物馆购买了一些潜水设备,统一由水下研究室管理。一直到2010年做“南澳Ⅰ号”发掘,我才有了第一套量身定做的潜水服,那是一家公司赞助的,手臂位置还印了我的名字。
后来,国家专门为水下考古建造了一艘“中国考古01”考古专用船。2014年,我参加了首航,在丹东海域进行甲午战舰致远舰调查。船上配置了工作室、文物保护实验室、仪器设备间、折叠潜水梯、减压舱、工作艇等,排水量近千吨。这样的考古专用船,目前在全世界只有三艘,法国一艘、韩国一艘、中国一艘。
今天,中国的文物保护理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没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南海Ⅰ号”根本无法花那么大人力、物力、财力去打捞、保护和展示。
录下“南海Ⅰ号”唯一影像
咸鸭蛋还看得见蛋黄
我是第一个在水下摸到“南海Ⅰ号”的考古工作者。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久、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南宋远洋贸易商船。从发现、调查、试掘、整体打捞、发掘到后期保护,到今天已经走过了35个年头。
2001年,我第一次潜下水做考古调查,刚开始水质还比较清,到了18米深度以下,突然就像有了一层黑雾,能见度越来越低。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船体本身的,只是偶尔能看到。我在水下录了20多分钟的录像,第一次让大家看到了“南海Ⅰ号”在水下的状态。也是因为这段录像,研究人员才发现船体保存得这么好,如果在水下原地发掘,绝对是个损失,这才提出整体打捞的方案。
水下考古绝不是一般的潜水打捞。打捞是一个快节奏的、计算投入产出的工作。而考古要计算的是,潜一次水能获得多少信息。水下考古首先要布置探方、测绘摄像,绘制出船的沉态。哪个东西从什么地方捞出来,都要在相应的空间位置标记,达到逆向复原的标准。水下测绘做得越精细,得到的数据越多,未来研究能取得的成果就越多。“南海Ⅰ号”从1987年首次发现,到1989年确定沉船位置,再到2003年决定打捞,历经8次调查。
然而,如果没有水下的能见度,这些工作都白搭。一般来说,离大江大河的入海口越近,水下的能见度越差。“南海Ⅰ号”就是在离岸不远的海域。除此之外,水质也受到海洋气候变化的影响,水下考古最好的时段是5月到8月,这个时候东北季风转西南季风,海况非常好,风平浪静。此时也是休渔期,鱼和人的选择可能有共通性,鱼的繁殖期肯定是海况很好的时候。另外,休渔期渔民不会出海,否则渔船拖网,海底的泥沙也会被搅起来。
而这块硬币的另一面是,水质越清,沉船往往保存得越差,水下淤泥越厚,文物保护得越好。就像易碎的物品,放在坚硬的桌面上和包在柔软的海绵里,肯定是后者得到的保护更好。
1999年,我去西沙群岛看过“华光礁Ⅰ号”古沉船,它搁浅在珊瑚礁的礁盘上,那边的水很清,有20多米能见度。尽管它和“南海Ⅰ号”的年代差不多,但经过长期浸泡,铁钉生锈,木板软化,船体已经坍塌。虽然测绘工作很好做,但船板是散的,已经很难复原。
“南海Ⅰ号”被很厚的淤泥包裹,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但我们没法展开考古工作,一动水就浑。所以,水下考古很难达到陆地考古的细致程度,想做到完美结合,就是把水下文物捞上来,按照陆地考古的模式做。当时整体打捞是没有先例的,我们通过理论计算,判断应该可以成功,但是理论和实践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确定了整体打捞的方案之后,2005年,岸上就开始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这个计划在当时也是冒险:如果沉船打捞失败,博物馆也就白建了。很幸运,我们都成功了。
2007年12月21日,“南海Ⅰ号”起吊。在20多米深、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底,将载满易碎瓷器的古船完好打捞出水,就好比用铁篮子从水底捞出生鸡蛋一样难。沉船从水底拉上来,加上船体、船货、泥和沉箱本身的重量,是5500吨。那次打捞成为当时的“亚洲第一吊”。
12月22日上午10时,“南海Ⅰ号”出水,采用古代“滚木”移重的方式运抵博物馆。进了博物馆,我们就把墙封了,马上把海水灌上,让沉船又进入了水下的状态,这也是对文物最好的原生态保护。2013年,经历两次试掘之后,“南海Ⅰ号”正式开始全面保水发掘,就是“放一点水挖一点”。一直到今年,相关考古工作才接近尾声。
最终,我们发掘出18万件(套)文物,总数超过广东省博物馆的馆藏量。现在回想,如果是在水下发掘,船上发现的咸鸭蛋、羊头、坚果、杨梅和稻谷等文物——咸鸭蛋还看得见蛋黄,可能都留不下来。在陆地考古,淤泥可以慢慢清除掉,但在水下没法清理,只能靠抽泥器,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会被抽进泥管,就漂走了。
在“水族馆”工作
和管子里的大眼睛对视
水下考古和陆地考古有很多不同。首先是工作效率,陆地考古一天能在现场工作七八个小时,但水下考古一天只能潜一次水。“南海Ⅰ号”尽管不是非常深,我们队员潜下去也只能工作40分钟左右;其次是工作经费,同样规模的发掘,水下考古可能是陆地考古经费的10倍以上,我们要租船、要在船上吃住,还有油费……都是开支。
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工作的安全性上。陆地考古会晒黑,但不至于危及生命;水下考古如果超过潜水极限或者遇上紧急情况,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在工作中会保证一定的安全系数, 潜水要考虑水下环境、能见度、水深、水流等因素,如果环境差,安全系数就会放大一些。下水之后会遇到什么情况,我们会提前做预案和提醒。
我给队员们的要求是,工作可以不做完,但到了时间,必须严格按照程序离底上水,不能说“我再坚持5分钟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做完了,可能身体受到的影响比这5分钟完成的工作要大得多。因此,我们会把安全时间控制得很精细。
在水下工作,有时候就像在水族馆里一样。我们看到很多生物很漂亮,碰上了又会很倒霉。比如水母,被蜇一下皮肤就会像被烙铁烫过一样发红,紧接着变黑。有毒的生物都是比较漂亮的,想多看几眼,但又要避得远远的,很矛盾。十多年前,我下水时膝盖被海胆扎了一下,两三天后膝盖就红肿得没法弯曲,还发烧,赶紧打针吃药才脱险。
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能见度不好的近海沿岸工作,生物多样性没有这么丰富,但也有有趣的事情发生。2012年,我们给广东汕头的“南澳Ⅰ号”明代古沉船做了一个原址保护工程,在海底罩了一个用直径88厘米的大管子焊成的十字限位架。结果那里就变成了人工鱼礁。有一次我凑近一看,管道里有一双很大的眼睛盯着我,一会儿就缩到里面去了,应该是一条很大的鱼。之后,我们连续回访了4年,每一次去都能看到它。
原址保护是我们近些年做过的三种水下考古模式之一。“南澳Ⅰ号”海底的淤泥很浅,且周边有礁石,沉箱下不去,目前没法整体打捞。我们把船上的文物打捞发掘后,就对船体进行原址保护。
广东佛山的西樵山矿坑遗址,我们又用了最小干预的模式。那里是清代采石矿的一个遗址,后来被水淹了,古代采石的完整场景就保留了下来。那里水很清,水下测绘也顺利完成了。
最小干预是考古的最高境界,考古本身是一个破坏性的研究,挖完一个遗址,遗址其实就不存在了,只是发掘的过程可以让我们提取有效信息来复原遗址与历史。并不是每条沉船都需要发掘,它在水下就是一个遗址,保护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连续4年中秋和国庆
在“中国考古01”上过
近年来,考古和传统文化都越来越火,“中国节日”系列晚会、知识考古类节目《隐秘的细节》,还有正在河南卫视、优酷播出的《闪耀吧!中华文明》,都是解读中华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尝试。前段时间,我去参加录制了《闪耀吧!中华文明》,在考古现场为观众讲述“南海Ⅰ号”的前世今生。
我以前很少面对媒体,后来觉得我们开展考古工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权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而且宣传项目成果,也应该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之一。所以,只要有需要,我就会亲自去面对公众,讲好我们的考古故事。
对年轻人来说,考古现在是热门学科,考古单位也都在扩编。从最早3名队员赴日本培训到现在,我们已经培养了近200名水下考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类人才,并且开始反哺国际、辐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了。现在,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都设置了水下考古的课程,尚未形成专业,但也有在筹备中的,我相信最终必定会落实。
跟年轻人聊天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在从事考古工作时能正确认识自己。没有一份科研工作比考古更幸运,考古是不求回报的。
我是属于比较“笨”的,把水下考古做到了“底”,一直做到今年退休。从18岁到博物馆工作,到现在40多年,很少有工龄像我这么长的人。曾有连续4年的中秋和国庆,我都在“中国考古01”船上度过,一出海就是一两个月,看“海上生明月”,吃烧烤、喝啤酒,是不是很浪漫啊。
船上有一间首席专家室,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在用,现在是时候休息一下了。不过如果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只要力所能及,我还去。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崔勇口述整理)
崔勇(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南海Ⅰ号”考古发掘领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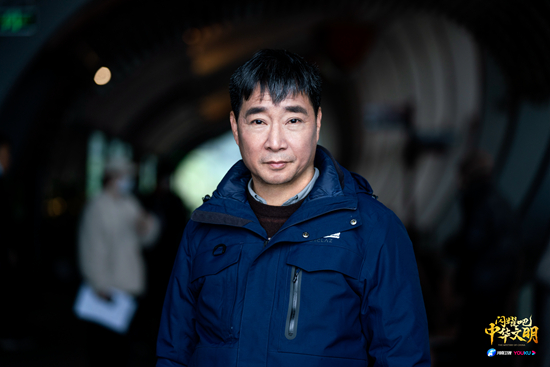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