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没想明白该以什么状态活着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死”了。
家里的长辈年岁渐长,我面临关于“死”的选择越来越多:老人生病,是待在家保守治疗,还是去医院做手术?该不该把体检报告的数据清楚告知老人?该为老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采访过一位老爷爷,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因心脏疾病入院,结果和老伴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多月,老伴在病床前天天写日记记录疫情下的医院。老两口好不容易盼到能回家,老爷爷却因突发心梗去世了。
这绝不是老两口预想的人生结局:死在医院里,没有子女相伴。
在医疗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死得好”“死得顺心”却成了难事。最常见的是老人躺在病床上,身体各处插满了管子,心电监护仪屏幕上的曲线慢慢变成直线。电视剧是那么演的,医院里也能看到相似的场景。
徐舒也是这样送走她的母亲:承受肺癌晚期治疗的疼痛,最后病情加重住进ICU,以极端痛苦无助的方式走向死亡。于是,这位曾经的大学老师、服装设计师,开始在海淀医院安宁病房当安宁疗护志愿者,为生命末期患者服务,并写下新书《重启生命》。
所谓安宁疗护,是在缓解不适和疼痛的前提下,给患者创造舒适、有尊严、有品质的临终生活。它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缓死亡,而是充分尊重患者个人意见,让他们做回主,决定该怎么死。
在安宁病房,志愿者跟着医护人员一起,给患者洗头、理发、做芳香疗护。看着患者在精油辅佐的抚摸下渐渐放松,进入睡梦,徐舒发现,临终前的时刻也不一定总是痛苦。
绝大多数患者,提起如何利用有限时间迎接死亡时,最多的用词是“回家”“不痛”。疼痛固然能用药物止住,但回家的路并没有想象中轻松。
徐舒见过一个老人想在家里离世,但家人不同意他出院。安宁病房邀请了他的儿子、儿媳妇,和医生、护士、心理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家庭会议上,儿子和儿媳妇愿意老人回家,但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回家后遇到疼痛和病情变化,家人如何及时处理?此时办出院,后续床位紧张,再次入院有没有困难?老人突然没有气息,家人如何判断他的死亡?如何联系殡仪馆,开各种手续办死亡证明书?
这些问题如此具体,又很实际。医护人员挨个解答了家属的疑问,表示后续会持续支持处理老人回家后可能发生的诸多情况,打消了家属的顾虑。于是,老人回家了,几天后,他在家中去世。
能在家里离世是件很奢侈的事。这不仅考验着老人和家属对于死亡的理解、家属对尽孝的认识,还有社会层面上对死亡的态度。比如,有些邻居会担心,楼道死了人不吉利,或是死过人的楼,房价会跌。
谁都知道死亡只是人生最正常不过的结局,像这样的邻居,反映了整个社会面对死亡的态度,依然是讳莫如深、避之不及。
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就讲了一个老太太生怕儿女没有兑现办土葬的承诺,于是假装死亡,想考验儿女们在葬礼上的表现。这场荒唐的葬礼铺张又不合实际,成了一场闹剧。
现实生活中,我见过有人把父母的葬礼当成一个舞台,要演出尽孝的模样给亲戚朋友看;有人把父母送到医院,然后拒绝探望,留老人在医院孤零零地迈向生命终点。
我对死亡也有过误区。我和妈妈讨论过死亡的话题,她说,有那么一天时,绝对不要送进ICU,不用抢救,就顺其自然地离去。我当时大力批评她厌世的态度,保证一定花最多的钱送最好的医院,延长和挽救生命。
但最近,我对待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自己都没想好要怎么过日子,怎么能强势地干预父母的决定,要求他们必须以我的预想过完最后的时光呢?
学会“善终”,是每个人必修的人生课题。但我们容易忽略,家属的哀伤也是需要抚慰的。安宁病房开设了针对家属的生死教育课。在老师引导下,徐舒重新拿出母亲的遗像,对着照片诉说了3个小时。那是她与母亲最后的告别。
我想,这样的生死教育课还可以开进课堂里,让年轻人也可以思考如何死,或许能帮助他们决定如何生。
魏晞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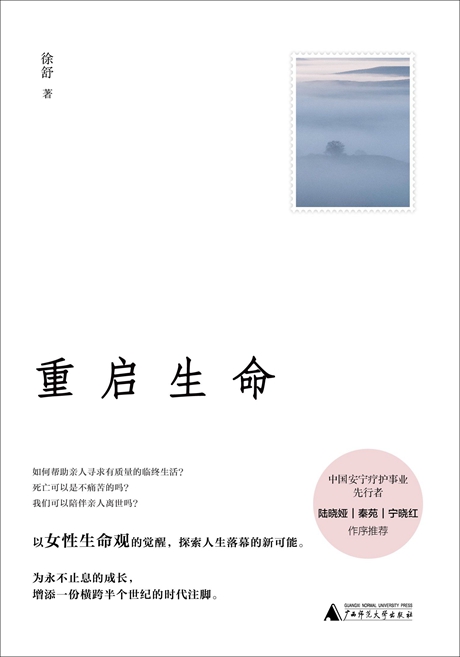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