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前,外公进了ICU。在他已经包好了给孙辈重孙辈的红包、选定了年夜饭的酒店,计划好了开春后的生活,他脑干中的血管瘤却毫无征兆地破裂了。老人瞬间昏迷,抢救后依靠机器生存,没有醒来的迹象,直到今天。
等我回到家,家人才告知这一切。我再次见外公,是在ICU每天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十几张床位,每张病床上都躺着一个家庭的悲伤。看着毫无知觉、插满管子的外公,我很难接受这样的见面。
第一次直面“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这句话的残酷。其实自从离家上大学又留在外地工作,与老人的见面机会就不多了,但终究觉得还有下一次。对生命的认识,在ICU里能得到一次升级,可如果到了这一刻才知道一些事情,终归还是晚了一些。
翻译过《沉思录》的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早在1996年就出版过一本《珍重生命》,给孩子讲生命与死亡。20多年来,书不断增订再版,一代一代的孩子出生、长大,面临着同样的困惑,有时候是恐惧。比如,即便我们万分小心、一切顺利,在生活中还是不得不面对各种死亡;而如果死亡终将来临,我们又该如何活着?
我的生命教育最早来自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这可能也是大多数中国孩子的经历。在我的家乡、南方的一座小城,扫墓称为“上坟”——确实是要上山的,在植被茂密的山头,披荆斩棘地找路。与其说是祭奠,从气氛上这更像是春游,家族的人难得聚在一起,带着吃的喝的——后来发展为肯德基麦当劳——让祖宗也尝尝鲜,还要去摘满山的映山红……
中国古人是有智慧的,把纪念逝者的清明节放在草长莺飞的春天,一岁一枯荣的原上草让踏青扫墓的人也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仔细想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突如其来、没有告别的死亡,或者历经痛苦之后的死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关于死亡,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作者是德国安宁疗护医学的领军者吉安·波拉西奥教授。他曾是神经外科的专科医生,但在接触病患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如何保证患者生命终末期的生存质量,成为一般的医疗措施无法解决的难题。
减少过度治疗、完成生前预嘱等措施,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生命更好的把握。越来越多的人——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自己要有机会来决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以或者不可以使用哪些措施。比如,我不愿意切开气管维持永远不会醒来的生命。
也许,死亡也像爱默生不朽的诗句:如果我的小船沉没,它是到了另一个海上。
我见过不少人,在退休直至死亡的二三十年,乃至三四十年,这段占据人生三分之一时长的漫长时间里,每天的日子是如此单一重复,用“几十年如一日”来形容并不夸张,生命中那些值得提起的故事也停留在几十年前。
于是,我鼓励年轻时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妈妈多出去玩玩,对天天健身但依然练不出腹肌的爸爸不吝赞美,我希望自己在老去后依然有跟上时代的勇气与能力,有独处的空间,有老朋友可以聊八卦,如果还能黄昏恋也未尝不可。总之,那时候,我只是老了,但还在好好活着。
有部名叫《不虚此行》的电影,讲的是一个编剧以写悼词为生,在这个过程中,慰藉他人,也治愈自己。工作原因,十余年来,我也写过很多名人讣闻,其中不少在其生前有过直接接触,最后一次提及却是去世的消息。
有人生不逢时,在退休后才开始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幸好老天假年;有人去世前还在孜孜不倦写自传,可惜这部传记永远没有结尾了;有人跨越3个世纪,见证了什么是沧桑巨变……
我曾经对外公作过一个简单的“口述史”记录。20世纪30年代生人的他,讲到小时候是如何读私塾,羡慕同学的“鸡牌”德国铅笔;十几岁没有条件再读初中,作为长子给家里开的花布米店干活儿,背上一根“六尺竿”去乡间收布;他骄傲地说起自己如何打得一手好算盘,走南闯北,第一次吃到山东的大葱和馒头是多么好吃……这是诸多体验的一生。
我作为旁观者,渐渐地也有了一个小目标,健康生活、保持围观。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提前告别。多部电影中有“生前葬礼”的桥段,我也和朋友讨论过,得出一致结论,死后最想干的事——如果能的话——就想看看周围人的反应。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葬礼的,也听不到大家对自己的评价。所以,倒也不必特地办“生前葬礼”,但告别确实很重要,与周围的人告别,也与自己告别。
最后,悄然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蒋肖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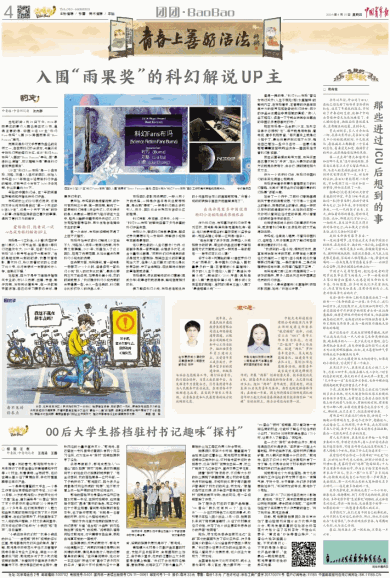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