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关于父亲,总会有太多的话题。那个被你叫爸爸、老爸、爹、老头儿……的男人,是不是有很多被你忽视的故事?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月”(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中国青年作家网,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背起旷野的男人
闫佳(24岁)
我曾经分享过很多家庭温暖小故事,那些故事里刻意忽略了爸爸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他不值得说,只是他那自私又自我的女儿曾经很嫌弃他。
小学时,嫌弃他赚不来钱,别人家都是砖房、楼房,而我们家是土坯房,同学从门口经过的时候,我都要假装看不见;别人接送都是摩托车,而他是自行车,好面子的我怎么也不愿意坐上他的后座——即便那个后座承载着我未上学前的各种欢乐。
初中时,嫌弃他没文化,大字都不识几个,而且喜欢吹牛,穿着邋遢。
高中时,嫌弃他是个残疾人,坐在轮椅上的他仿佛让我也“矮”了半截。那个骑着电动车两小时就能逛完的小县城里,随处可见的就是同学,我害怕别人问我:“是你爸吗?”
长大后,我懂得越多,对他的鄙视也越发猛烈——觉得他肤浅、大男子主义以及自私自利。和他说话,我越发带着一种优越感——我很少和他讲话,因为讲话便意味着争吵,我奉行“有理说理,要有逻辑”,而爸爸吵架全凭吼,仿佛声音越大,就越有理。
我可以孝顺,可以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爱他,是因为他是父亲,但是不会敬他。
我知道自己这样很讨厌,但请原谅青春敏感要面子的少女。
爸爸经常念叨:年轻人不要信命,要信自己!别人说这话,我肯定觉得是心灵鸡汤,唯有我爸说这话,我深信不疑——他是个韧性极强的人,无数次死里逃生。他的主治医生都说,我爸是他见过的求生欲最强的病人!
我想也许是他的责任感使然,毕竟他还有妻儿等着他。
爸爸从12岁担起了养活弟弟妹妹的责任。对于这一责任,他对我说:“唯一后悔的就是让你四姑丢了命。你四姑很聪明,跟你一样,要是好好地长大了,说不定我还能供她上大学呢。”
记忆中第一次看到硬汉一般的父亲有泪,就是因为四姑。他眼里噙着泪告诉我,那年四姑才13岁,不幸得了疟疾,他背着她跑了八九公里赶到大夫家的时候,四姑已经没了气息。彼时,他不过才20岁出头。妈妈说:“你爸一直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一辈子不吃喝嫖赌,赚了钱就上交,想给你们最好的教育,砸锅卖铁送你们上大学,你不能不敬他。”
前段时间我陪爸爸去西安做检查,医生说了一系列让我听着就害怕的病。我送他去做检查,等在外面的时候惶恐不安,害怕他真的有什么事。
但我又不断安慰自己,他是我那无所不能、超级有毅力和韧性的超人爸爸。
爸爸曾经做过无数种工作,因为没有文化,几乎都是苦力。他说年轻的时候,不要钱,只要人家管顿饭,他就给人家干活,辗转在各大矿场、石场卖力气。我记忆中有两年的时光,他在家附近的石场装石头,一车20元,他一天要装五六车,一直是石场装车最多的人。
他总是拼了命地卖力流汗,别人都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拼?能不能给人留点活路?”他回答说:“我家3个小孩呢,不拼怎么行?”
再后来,他考了爆破证,一个同乡带他去了外地。他曾骄傲地告诉我,爆破员不是谁都能做,得胆大心细,但他从没告诉我爆破员的工作那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炸破的石头压到身上。
第二年,他便出事了。那时我才初二,只知道爸爸受伤了,妈妈去照看,甚至抱怨说,妈妈走了就没人给我做饭了。
在我受不了一点挫折要死要活的时候,爸爸只是平静地告诉我:“你这么不惜命,是因为你没有死过,你在死亡边缘徘徊一次,你就只想好好活着。”他总是平静地告诉我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将近10个人被压在了矿井下,他能闻到鲜血的味道。在他被送去医院的时候,意识模糊,梦见了从他记事起村里所有去世的人,那些人在向他招手。他还梦见了爷爷,那个一辈子也没有和他说过几句话的爷爷对他说:“滚回去。”
我没有继承爸爸的勇敢。我怕黑,我害怕死人,但爸爸不同,他身上总是有一种无畏的勇敢,他的字典里仿佛从来都没有“怕”字。
后来他一年总是要住几次院,因为医院的床太小,他害怕妈妈休息不好,从来不让妈妈陪同。有次,我去医院看他,同病房的奶奶说:“你爸是我见过最乐观、最乐于助人的残疾人。”原来,康复科的病人大多腿脚不便,爸爸竟一个人帮五六个病房里腿脚不便的人买饭!
爸爸前几年忽然迷上了种花。我们兄妹三人给他买了很多的花籽,本来以为他只是在家里的小院子种一下,没想到回家的时候,发现从村口到我家的那条200多米的小路上全是姹紫嫣红。
我问我妈:“咱们这儿怎么忽然重视绿化了?”
我妈撇撇嘴:“你爸每天准点起来,从轮椅上溜下去,坐到路边,把那路边的杂草一棵一棵地拔起来。人家每天还有任务呢,今天10米,明天10米。”
我哭笑不得——爸爸总是带着一丝执拗的可爱。
老妈抱怨:“他拔完之后,还逼着我拉了几车的土倒在路边,方便他种花。”
我笑得要死,觉得爸爸真是可爱。
我上大学以后,家里只剩下爸爸妈妈。怕他们寂寞,家里养了一只猫和一条狗。爸爸总是好心肠,路上见了野狗也要招招手,野狗们慕名而来,家里最多的时候养了4条狗,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狗。猫猫狗狗都和爸爸亲近,妈妈常说,感觉自己不受欢迎了。
去年,爸爸突发奇想,想买个残疾人专用的电动车。在他的百般哀求下,妈妈给他买了车。他可开心了,计划每周带妈妈去一个旅游景点。偏僻的小县城,大家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要。妈妈说,好多和爸爸情况一样、年龄相仿的人,都觉得年纪不大出了“这种事”,非常丢人,不愿意出门,还会迁怒于家人。但爸爸不嫌丢人,每天还乐呵呵的。
我每次受到打击时,总会看一看爸爸的抖音账号。他的抖音质朴无华,却能让人感觉到他在很认真地记录生活。虽然是个残疾人,但是他生活可以自理,能劈柴、做饭,养狗养猫、侍弄花草、锻炼和唱歌。
除了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他几乎都是乐呵呵的,一直在努力把平淡乏味的生活经营得多姿多彩。他像一株有着蓬勃生机的向日葵,总是给予他人热爱生活的动。他总是感叹:“这个社会真好,要是我也出生在这个时代该有多好。”他向我们奉献着他的所有,而我只不过是站在他的肩膀上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我没有资格揣着优越感对他不尊敬。
爸爸还曾经被记者采访过。
一年冬天大雪纷飞,路上积雪很厚。天空停止了飘雪后,肃静的冬雪世界里,他坐着电动轮椅,抄着扫帚,从我家院子里一直扫到了国道上。正巧遇到了报社的车子,那人停下车,看到他是个残疾人,讶异不已:“大叔,你怎么在扫雪啊?是谁安排你扫雪吗?”
他仰起冻得绯红的脸,有点蒙:“你们说啥?”
记者重复道:“是你们这儿的干部安排你扫地吗?”
爸爸摇头:“没有啊。”
“那你咋在这儿扫地?”
“这路上的雪要是不扫的话,过两天会结冰,车子走在上面不安全。”
记者大概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回答吧,他笑道:“你这也太有奉献精神了。”
爸爸挠头:“什么奉献不奉献的,我就是闲得没事做。”
回家后,他后知后觉地告诉妈妈:“我好像要上新闻了,人家说我有奉献精神,还给我拍了照呢!”
妈妈笑他痴人说梦,后来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见报。
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事挺神奇,不过是做了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居然被夸赞了一番。他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却一直尽己所能在为这个社会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昨天,我忽然发现爸爸有了白发,在感叹时光残忍的同时,我更揪心于自己多年对他的疏远和不敬。
我想,每个人大概都会因为时代观念以及经历不同对自己的父亲有过些许的不满。但是,请记住,你的父亲曾经也是潇洒的少年,他们之所以成为父亲,是因为他们用大部分的自我,担起了我们的人生。
——————————
哑巴(小说)
余修杰(27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硕士生
过了白河滩,就是石桥村。
班车没有规律地一颠一簸,一点一滴地磨掉车厢里回乡的人们的热情。
边杰没有热情。晃晃荡荡半袋子胃酸,伴着没消化的午饭,随着车厢抬升砸落。为了不浇灭车厢里仅剩的热情,边杰决定半路下车走回家。
边杰3年没回村了。自从上了大学,一个崭新的、精致的世界向他展开。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边杰兴奋之余,又带着一丝畏怯——怕被同龄人闻出自己身上的泥土味。不过,好在他的姓氏给他带来了便利。不常见的“边”姓,给同学带来了新奇感,边杰也顺道挤进了新世界。
3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边杰还沉浸在新世界的探索之时,父亲的一通电话打碎了他的美梦:“再不回家过年,就断了你的生活费。”
边杰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就像飞上天的风筝,飞得再高,线头总还在父亲手里。仓促收拾好几件换洗衣物,赶在除夕前一天,边杰赶回了家。
农村建房子,总是靠着大路。
城市的路给房子带来的是喧闹,农村的路给房子带来的是热闹。
边杰的家也靠着大路,是一栋三层小洋房。一楼是大厅和父母的房间,外加一个小矮楼作为厨房。二楼则留给了边文、边武和边杰3个儿子住。随着大哥和二哥成家出门,准备立业,边杰在外3年,二楼也就空了3年。至于三楼,就是一个架子,空空荡荡,也没装修。
村里讲究排场,人家建三层,我也建三层,谁也不比谁差。
三楼的房间没糊腻子,露出里面的红泥砖头,像被剥开的皮肉。伴着一年又一年的爆竹声声,结成一道所有人都淡忘了的疤。
下车好一会儿,边杰才从晕车里缓过来。周围的山垄田地看着陌生,新修的路弯弯绕绕。边杰靠着手机导航,总算是找到了回家的路。
到了院门口,父亲靠在大门旁边,正坐在小竹椅上。听见动静,父亲朝着门口望来,眉毛蜷在一起,在额头像是打了个结,看了两三秒,才缓缓舒开,而后又拧巴在一起,把头转向另一边。边杰拎着行李箱,缓步走到父亲旁边,小声叫了一句“爸”,就快步走进屋里。
母亲是在傍晚才知道边杰回家了的。打开房门就是一通数落,不外乎是一些不要爹妈、不要家的话,边杰在电话里已经听过好多遍了。在外3年,边杰学会了如何应对母亲的啰嗦——只要静静地听着,听着就好,这种沉默,带着某种反抗,又带着某种怜悯。讲了一箩筐,母亲看边杰也没个声响,丢下一句“晚上记得去你萍姐家订婚宴”就走了。
石桥村基本都姓边,村里头大家或多或少都可以算上亲戚关系。萍姐叫边萍,就住在隔壁,是边杰儿时在村里为数不多的玩伴,边杰总喜欢围着她转。但过了几年,边杰发现自己不过是一颗卫星,萍姐终归还是找到了她的太阳。
农村的婚礼总是扎堆在春节前后,也只有这个时间,才有足够的人手可以帮忙。
订婚宴是在祠堂举办的。边杰到祠堂的时候,宴席已经开始了。刚落座,正想埋头扒饭,旁边一个大姨就认出他来了。
“这不村头老洪头家的阿杰嘛,啥时候到家的啊?”
一口夹杂了半嘴红烧肉的家乡话,边杰咀嚼了一下才听明白。老洪头就是他父亲,边洪,在村里头同一辈分里年龄最大。
“姨姨好,是的,刚回家。”
见到女性长辈叫姨姨,见到男性长辈叫叔叔,这是边杰在无数次记不清是哪个亲戚后,总结下来的经验。
“孩子真俊啊,读书还好。当年考上大学,老洪头满村报喜来着呢,逢人就聊,半句话不离这孩子。”大姨把话围桌传了一圈,像是发现了一个稀罕物件,同桌的人也乐得有了谈资。还有一个看起来更大的姨姨,一拍头,说小时候还帮他把过尿呢。
突然成为焦点,让边杰有点坐立不安,只能嗯嗯啊啊地应付着这些不熟的亲友们。
“这孩子,还真是进了城就忘了自己哪来的了。”
“那可不,他和咱可不一样,名牌大学生,有出息着呢。”
“没记错的话,这娃3年都没回村吧,不知道的以为是回家旅游来了呢。”
“老洪头这怕是表面风光心里苦哟。”
……
窸窸窣窣的话顺着桌面漫过来,边杰只能就着一大口菜,一起咽下去。
宴席中场,萍姐和她的未婚夫向宾客们敬酒。边杰远远地看着那张陌生的脸,总和记忆中的她对不上。她像一棵催熟的油菜花,带着一种过分的明艳和臃肿。赶在敬酒到这桌前,边杰就悄悄地走了。
回到家,父亲还在院里,坐在小竹椅上。“回来了?”“嗯。”
父亲右手搭在膝盖上,仰着头,看着边杰。边杰就定在原地。
那一弯月亮挂在夜空中,旁边的启明星熠熠地闪着。
父亲还是把手收了回来,头颅垂下。边杰又等了两秒,快步上楼。
当晚,边杰做了一个梦。他在一片虚无里面悬着,无边无际。看不见来路,望不见归途。
农村的天气总是偏冷些。边杰立在门旁,这样想着。
今天是除夕,按照村里习俗,在上午需要祭拜一下祖先。
父亲在大门口点燃一把黄纸,再在第一把黄纸上铺开三四把黄纸。底下的黄纸火焰被压下去,只有浓烟从里面出来。还没完全烧完的黄纸,被燃烧的热气冲起来,飘飘摇摇,落进大厅,落到院子里,落到院墙外的柏油马路上。
父亲抽出6支香,在黄纸堆的火苗上点着,走进大厅。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母亲的牌位,在条案上摆着。父亲各点3支,拜了三拜,就算结束了仪式。
关于这两位老人,边杰没有印象。往年,也只在清明的时候,边杰才会想起他们。每年清明,村里每家每户都会上山扫墓。坟山就在村后头,连着后村的几亩地。每次上山,父亲在前面领路,边杰在后面跟着。两个人在田间走过,扒开杂草丛,钻进细细密密的竹林里面。烧纸、上香、放爆竹,祭拜、下山、种庄稼。这时候的父亲,比平时更少言寡语些。可能父亲想对他们说的话,都种在了庄稼里,在祭祖的时候才会无话可说。
到了中午,边文、边武驱车赶到,带着大嫂、二嫂,还有边文的儿子边铭和边武的女儿边筱。小一辈的名字总是更愿意找一些生僻字,至于他们是不是更难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则不在起名的考虑范围内。
哥哥们、嫂子们打过招呼后,就去收拾屋子了。边杰帮着他们带孩子,领边铭和边筱出门看看。
“小铭和小筱都读几年级了呀?”
“叔叔,我上三年级啦,小筱读二年级呢!”边铭不怕生,用普通话,脆脆地回答。
“我明年就上三年级了!”边筱带着不服气的语气说。
农村,是方言的自留地。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自然也就不会说几句家乡话。
“那都是大孩子了呢。叔叔带你们去石桥那边玩怎么样?”
“好啊!好啊!谢谢叔叔。”边铭就拉着边杰出发了。
边杰愣了一下。“谢谢”,真是熟悉又陌生的词。
石桥本地话里没有“谢谢”,只有“难为”。村里面乡里乡亲,谁有困难都会捎带手帮衬点。也只有遇上过不去的坎的时候,才会上门求人。被求的人抹不开面子,一般也都会能帮一点是一点。求人的人会千恩万谢,一句又一句地重复着“真是难为你了”,以示对方的大度和自己的歉意。
在边杰印象中,父亲鲜少说“难为”这个词。就算有一年村里发大水,淹了家里好几亩地,一家人也是紧巴着熬了过去。唯一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边杰高一时体检查出了肺结核。父亲知道消息后,一晚上没说话,第二天带着边杰,拎着东西就去村主任家里了。后来,在村主任的介绍下,边杰看了当地最好的医生,病也就慢慢好了。边杰也在父亲的低声下气中,懂得了“难为”这个词的重量。
石桥是很早就有的,村子也因石桥而得名。然而自从修好了大路,渐渐没那么多人走石桥了。不过,要下田地,还是要走石桥。
村里的田,都在石桥那头。
到了石桥,边杰就在桥边蹲着,看着边铭和边筱在田里面撒欢。没下过田的孩子,对田野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两个小孩在田地里,东踩踩西拔拔,享受着没有父母管束的时光。
边杰就在桥边看着他们玩,待到石桥下的小河被远远的太阳烘成暖暖的橘黄色,就喊着他们赶紧回屋了。
除夕晚上的菜,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碗又一碗、一碟又一碟的菜往桌上端。红烧肉、清蒸鱼、白切鸡、松花鸭、烤羊腿……边铭和边筱没感觉这顿饭有什么特殊,吃了几口,就钻进一楼卧室看电视去了。
饭桌上,边文、边武和父亲热络地聊着。从亲戚往来讲到国家大事,从谁家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说到谁家老人今年又去世了。边杰插不进话,也不想聊,吃了两口饭,也就借着帮忙照顾孩子的由头,进了卧室。
卧室里,两个孩子捧着碗,在看动画片。边杰坐在凳子上,心不在焉地看着动画片,过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最后还是坐了下来,耷拉着脑袋,像是一只泄气的皮球,又像是一个放弃抵抗的犯人。
大厅里吃到尾声了,父亲打头,边文、边武跟着进到卧室。边杰浑身紧绷了起来。
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一沓钞票,带着皱痕。他解开绑着的皮筋,从里面抽出3张来。
“小铭、小筱,来拿压岁钱了。”父亲操着家乡话,摇着两张红色钞票说。
“谢谢爷爷,爷爷新年快乐!”边筱抢声喊着。
“谢谢爷爷,祝爷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边铭慢一些,也多说了一段。
他把钱放到两个孩子手上,一人一张,两个孩子再谢了一遍,举着钞票向各自的母亲炫耀去了。
父亲转向边杰,又看了其他两个儿子一眼。从那一沓钞票里面又抽出两张,一共3张放在边杰手里。边杰看了父亲一眼,又低头转向地面,把钱抓在手心,把手垂在脚边。
父亲等了一会儿,见边文、边武没有动作,长叹了口气,转过身。
边文、边武掏出钱包,拿出刚从银行取出的新钞,各自数了一沓给父亲。
“爸,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完成了仪式,没有多余的寒暄,他们也就出了房门。
边杰松了一口气,把钱放进口袋。快步上楼,回到房间。
路灯渐次关了,一楼还在播着春晚。边杰躺在床上,没有睡觉。
不同于手机里面的转账,那3张红色的钞票,那么分明地放在他的手上,像是某种未成年的证明。边杰接下它们,带着某种屈从的意味。
“阿杰。”父亲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边杰直起上身,看着门口。
父亲走进来,从口袋拿出一沓钞票,放在边杰的床上。
崭新的红色钞票,在吊灯的映射下闪着光,散发出一股油墨味。
边杰看着床上的钞票,又看向父亲。
他张着嘴。
他不说话。
窗外,烟花声响起。
新的一年到了。
——————————
父亲与牛
吴臣祥(23岁,藏族) 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科学学院硕士生
公鸡打第一遍鸣时,我就听到了窸窸窣窣的扫地声音。早已经起床的他,开始扫除昨晚的积雪。昨天父亲就打算去附近的县城卖牛肉,在联系好买主后,晚上便叫来了帮手。由于买主想要现场宰杀,所以我们晚上便要把牛装到车上以便明天早点出发,在费了好大一番劲后,终于把牛装到了车里。等到把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已经到了夜晚。
村里的人家不多,晚上的灯光早早就熄灭了,但是黑夜里并非伸手不见五指,乌蒙蒙的月亮照着飘荡着的细细雪粒,点点月光使得寒风也温柔了些。舅舅说这样子的雪应该是下不了太大,但飘了一整晚的雪落到地上也有一尺多厚,厚到足以对出行造成巨大影响——一个买家的电话已经让昨晚的计划彻底泡汤。又联系到了新的买主后,父亲打算直接在家将牛宰杀,再拉到交易地点去。
杀牛这件事并不容易,一头牛五六百斤,没有三四个成年人是按不倒的。加上寒冬腊月的天气,脱下手套不小心摸到装肉的铁盆就会被撕下一块皮,但是牛肉的切割和牛皮的剥离又必须要脱下手套。
自我有记忆以来,父亲每天都在跟牛打交道,从寒冬腊月到三伏酷暑再到寒冬腊月。冬天,山上的枯草容易被积雪覆盖,牦牛在山上找不到吃的,它们便会从遥远的大山来到家门口,等待父亲的喂养。我常常感叹这种生物的神奇,离家这么远还记得路。
到了夏天,牦牛受不了炎热的高温就需要我们给它剪毛。父亲甩出的绳索总是能精准地套住牛的犄角,然后他再走到牛旁掰住牛头,一头五六百斤的牦牛便会在巧劲下倒地,动弹不得,最终不得不接受它的“剪发仪式”。我最喜欢这个活动,不仅是因为它在生机盎然的夏天举行,也因为看着牦牛在圈里狂奔与人们博弈,我就会感受到一种充满野性和力量的生命力。
瘦小的牛犊总是会受到全家人的关爱。有一次母牛产仔,寒冷的天气会使初生的牛犊难以存活,我和父亲便接替着把牛犊从山巅抱回了家里的火炕。我们用麦麸做成糌粑的样子来喂小牛犊,最终帮助它顺利长成一位“牛母亲”。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家中就有30只小牦牛在受特殊的照顾。
到了腊月,年味愈来愈浓,人们也会出门采购年货,牛肉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父亲这时候就会联系亲戚朋友推销自己的牛肉,毕竟一年的心血都会在这几天收到回报。寒冷的冬天使得户外活动格外艰难,好在父亲的手法熟练,牦牛喘了几口粗气便一命呜呼了,不会受到额外的折磨。在舅舅等人的帮助下,牛肉和牛皮都被快速分离,饶是这样,也硬是从天蒙蒙亮一直忙到中午才宰杀完毕。
父亲和舅舅、哥哥们开着车去县城卖肉了,下午5点多带着剩下的50斤牛肉返回,一路大雪飘扬。虽然大雪跟着飘洒了一路,但是整个卖肉的过程还算顺利。由于屋内外的温差,窗户上结出一层冰霜,父亲说好似开放的花儿一样引人注目。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自己在园子中待了这么多年其实总共有3个问题困扰着他: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是为什么要写作。“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是他对绝情生活的无奈体悟。在园中的漫步思考让他接受了不公的命运,转而开始寻找他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和这个世界对于他的意义。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是智慧和悟性吗?这是他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但是他立马就否定了。
父亲可能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每天都在忙忙碌碌,为了所谓的明天努力。我也从未问过他对于命运的思考,他只是一天又一天地忙碌着:春天喂小牛犊,夏天剪牛毛,秋天牧牛,冬天杀牛。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他没有经历过史铁生的断腿之痛,相比而言更像是我们普通人的写照。虽然生活单调又重复,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的不公,只会在某天看到我趴在书桌上奋笔疾书的时候,说一句“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不要像我一样吃苦”。
他的生活是苦的吗?这很难说,他只是不想让我干体力活罢了。春夏交替,寒来暑往,时间没有一点停留地向前流逝。所谓的命运只不过是人生中的必然,从生向死是一种必然,年幼到衰老是一种必然,生老病死无一不是命运。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努力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才是自己活着最大的意义。父亲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作为丈夫的命运,在努力地支撑自己的家庭,在有限的时光里表现出了自己的意义。世上的不幸和苦难有很多,但是很多平凡的人都在奋力地、平静地活着,追求着自己的意义。史铁生依靠自己的双手书写文字,父亲依靠自己的双手喂养牦牛,工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工作,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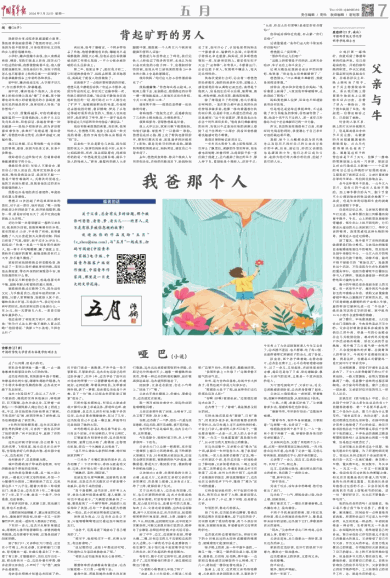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