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家最常见的荤菜食材,鸡蛋的吃法有很多:可以和青椒混炒,可以和紫菜一起做汤,可以油煎,可以水煮……各种吃法,各有各的风味。过去,母亲常常给我做的,是蛋花粥。
晨曦微露时,母亲已起床,简单洗漱后,淘米下锅,煮粥。拨开昨晚封堵的煤炉口,添一个新的蜂窝煤,火渐渐燃起,转身就去洗衣。她的一天从洗衣做饭开始,日复一日。待太阳初升,闹铃响起,我睁着蒙眬的睡眼,望着窗外或蓬勃的新绿,或萧瑟的枯黄,在母亲的催促声中忙不迭穿衣、洗漱。
八仙桌前坐定,等着吃早餐。母亲拿出一个碗,单手拿一个鸡蛋,碗边一磕,手指对向一张,裂口处,蛋黄拖拽着蛋清落下。筷子搅拌,蛋黄蛋清彻底融为一体,不分你我。炉灶边,刚煮熟的、正冒着腾腾热气带汤汁的稀粥舀一勺,倒入碗中,把蛋液固化、绽放成花。筷子不停搅拌,蛋花和稀粥彻底融为一体,不分你我——是谓蛋花粥。
热粥浇淋烫熟的蛋花,色泽不似油煎那般是浓郁的金黄,而是浅浅的、鲜嫩的明黄,仿佛三月大地初开的油菜花,薄薄的,细细的,碎碎的,裹挟着、掺杂在粒粒晶莹透亮的大米上,漂浮在纯白、醇郁的米汤上。
搁一勺白糖或自家菜地种的甘蔗榨的红糖,或邻村养蜂人处买的蜂蜜,一碗蛋花粥,就具备了甘香甜蜜的滋味。幼时的我嗜糖如命,父母怜爱,家中白糖红糖常备。白糖未及融化时,在蛋花粥中,仿佛一个个小泡沫;红糖则会把粥染成土黄——如田野里的泥土颜色。调羹一勺勺送入口中,蛋花的清香,稀粥的淳朴,糖的甜,纷纷抢占着味蕾。
爆炒、油煎,味道好则好矣,但蛋花粥清淡的吃法,更便于肠胃吸收。在过去的日子里,母亲并不明白这些,也许现在仍不明白。大字不识几个的她,生于农村,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从小帮衬家里放牛、放羊、养猪,嫁为人妇后,操持一家人的身衣口食,帮着父亲下地干活儿,用半生辛劳拉扯孩子们长大。这种独特的鸡蛋做法,我在别处不曾见过,或许出自母亲的家传。在乡村,绝大多数的饮食文化,通过口口相传、耳濡目染,代代承袭至今。
近日,母亲心血来潮,早餐时给我准备蛋花粥。昔日的煤炉,早已变成燃气灶,高压锅内,新煮的稀粥正热。她舀一勺,冲入蛋液打底的碗中,蛋液飞溅成花,搅拌中,稀碎的蛋花和稀粥彻底融为一体,不分你我。搁一勺白糖,糖粒渐融,白色的蒸汽升腾,在不绝如缕的甜香中,恍如回到了旧日的时光。
刘开栋 江西省上饶市实验中学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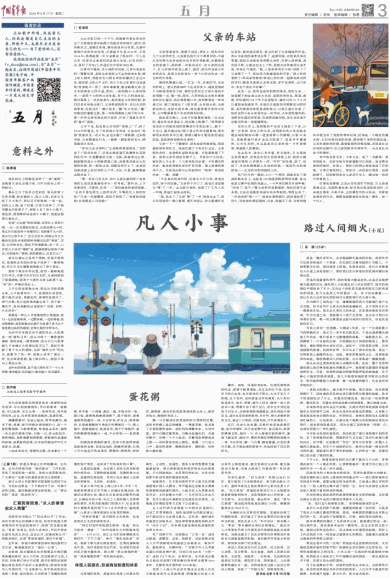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