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芳说自己的肚子仿佛被安上了拉链,时不时就要打开。从2013年第一次手术至今,她已经开腹5次,清除不停来袭的“泥石流”。
54岁的徐友芳患有一种罕见病,名为“腹膜假性黏液瘤(以下简称PMP)”。跟它交手多年的医生解释,带着肿瘤细胞的黏液会在患者腹腔四处侵袭、生根,发展出更多黏液,最终吞没、硬化人的器官,正如泥石流一样。
致病原因不明、没有特效药——1993年,英国女演员奥黛丽·赫本就死于该病。3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患者依然无药可用,只能不断接受开腹手术,清理肿瘤和黏液,延续生命。中国约有3.52万人确诊PMP,形成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病友群体。
距离上次出院不到半年,最近,徐友芳又住院了。她体重只剩30多公斤,几乎无法进食。
“估计我等不了了。”她说,“你说我还能等到吗?”
她在等一种药。在PMP患者腹腔的灾难现场,有人正在抢时间去做药,试图挡住命运的泥石流。
“泥石流”四处侵袭,和腹腔脏器争抢生存空间
在深圳湾实验室,孙正龙博士很忙,电脑一打开,通信软件和邮箱的新消息提示音就频繁地响起来。桌上的一张白纸记录着他最近4天的9项事务性日程。忽然,他发现自己漏掉了一家医院的来访事宜,9件事变成了10件事。
他步速比一般人快,把每一场必须发生的对话精确地卡进日程表。“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对他来说是非常具体的——早一天把PMP特效药做出来,就可能有患者因此活下去。
面对“泥石流”,必须再快一点。从2018年开始,孙正龙已经和它斗了6年。如果他赢了,全世界PMP患者将迎来第一种特效药。
清华大学长庚医院医生李雁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能给PMP患者做手术的医生。据他介绍,我国每年新发病例数约4500人,致病原因尚未确定。
曾有学者提出PMP可能来源于阑尾肿瘤。如今,这种说法得到了临床的认可,绝大部分PMP患者是因为阑尾肿瘤增大导致阑尾穿孔或破裂,含肿瘤细胞的黏液释放到腹腔内,种植到腹膜、肠系膜表面并继续产生大量黏液,形成PMP。
“泥浆就是黏液,石头是肿瘤细胞。”李雁说,“泥石流”四处侵袭,和腹腔脏器争抢生存空间,重力作用还会促使其在盆腔内聚积,形成黏液湖。最后变成坚硬的凝块,“就像泥浆凝固,患者的腹部硬如磐石”。
化疗药物对肿瘤有效,但会被黏液挡住,无法施展。
随着疾病发展,患者会出现进行性肠梗阻。最终,他们会因不能进食或排泄而死亡,一些患者则死于多次手术带来的并发症。
孙正龙想找到一种药物,能攻破包裹在肿瘤外的黏液,让化疗药可以直达肿瘤细胞。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如果能将黏液溶解,不论是手术难度还是化疗难度都将显著下降,患者的生存期和生存质量则会显著提高。关注药物研发进展的李雁说,“这将是跨时代的变革”。
然而,除了科学难题,孙正龙还要面对罕见病创新药研发的共性问题。有专家曾分析,和其他常见病相比,罕见病患病人数太少,药物研发成功概率过低,即使成功也很难收回研发成本,制药企业、投资人基本没有积极性投资开发罕见病药物,“科学上有意义、现实中有需要、经济上基本不具可行性”。
人类已发现的7000多种罕见疾病里,只有5%有药可医。有人说,创新药研发逃不过“双十定律”——需要经历十年时间,需要花费十亿美元。一名美国的罕见病医药科研人员曾坦言:“我们做一个药物最少要5-7年,风险也很大,十个项目只有一个能成。”
没有资本的青睐,也没有顶尖团队支持,孙正龙几乎是单枪匹马面对PMP的“泥石流”,数次受挫。在没有加入深圳湾实验室之前,他的研究经费基本都要“自掏腰包”。
“太奇怪、太震撼了”
徐友芳如今很瘦,佝偻着背,尽管底气不足,语速仍然很快,尽力地提高声音。她求生的意志坚强,20岁离开安徽老家,一个人风风火火闯北京,做过保姆、保洁和服务员,在清华大学附近包下铺面卖麻辣烫。她说那时在五道口做生意要面对暗流涌动的地下江湖,人够狠辣才能站得住。她在北京结婚生子,又回老家盖了房子。
2013年,徐友芳在老家陪儿子读书,被当地医院误诊患有卵巢癌,开腹才看到一肚子黏液。2015年,她疾病复发,回到阔别十几年的北京,大医院轮着跑。有医生劝她回家陪陪家人,“做不干净,还会长,没意义”,她不甘心。
孙正龙最初关注到PMP,是因为身边有人确诊。幸运的是,这位患者确诊、干预早,目前身体状况平稳。博士就读基础生物学方向的孙正龙当时加入病友群,想着要做点什么。
“我非常震撼。”孙正龙形容初次研究PMP的感受,“这个病的表征太奇怪了。”他阅读了能找到的全部基础研究文献,加起来也不到百篇。
那时,他还在苏州的一所科研机构研究显微成像技术。最初,借助生物学、基础医学、光学和力学交叉的学科背景,他把打击PMP的目标放在探清黏液的生成机制上,做了两年都没有结果。
两年间,他发现这些黏液把肿瘤细胞紧紧包裹住,化疗药物无法穿透屏障,杀不死肿瘤细胞,只能用手术清除黏液。
“手术取决于医生的技术和耐心,如果稍有不慎遗漏了哪怕一颗‘种子’,肿瘤细胞很快就会孵化,对患者而言就是复发。”孙正龙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能做这类手术的临床专家很少,一次手术要12-16个小时,费用超过10万元。
2015年春节后,绝望的徐友芳偶然找到了许洪斌。作为航天中心医院黏液瘤科主任,许洪斌也是国内少数几位对PMP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之一。此后9年里,他为徐友芳做了4次手术,把别的医生断言“只有3个月”的生命延长至今。
为了看病方便,徐友芳又在北京定居下来。2022年,她病情加重,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辞职从上海到北京工作。
如今,徐友芳和丈夫租住在北京城南一处两居室里。每天下午,丈夫会串好肉串,拿到夫妻俩经营的烧烤店去。去年,徐友芳还能在店里帮忙,手术后伤口尚未完全愈合,她还坚持准备家里人的饭、独自去航天中心医院换药。
徐友芳在日记里写给儿子:“亲爱的儿子,因为手术,我又一次去了阎王地府一趟,经历的疼痛折磨,让我只无尽地从你那里索取,还变本加厉地挑剔和无尽地要求,以至于忘记了我是谁,也丝毫不懂得感恩。跟你说声对不起,请你原谅!”
她也写给爱人:“雄哥……你真的辛苦了,辛苦得连我都心痛之至啊!”
这个爱拼敢闯的女人现在绝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记一些日记、药方,想生命会延续到什么时候。10年前她的目标是活到儿子高考、上大学、工作,如今是希望能看到儿子结婚。
徐友芳的儿子深知做“那款药”有多难,他期盼着,又说服自己别过于乐观。他怕听到母亲“我应该等不到”的诉说,忍不住向来访者打听“那款药”的情况。
这个年轻人希望满足母亲更多的愿望,他从不抗拒别人介绍对象,着急地相亲。尽管他不太想留在每天通勤4小时的北京,但又为了母亲的期盼坚持着。
“泥石流”随时可能进攻,他不敢不防守
2015年,在一次国际医学论坛中,中国PMP病友群的组织者刘晖曾听一位外国学者介绍他们正在研究的一款化解黏液的药物。刘晖的父亲在2008年确诊PMP,2009年接受手术治疗,她因为父亲建立病友组织。2019年,父亲去世,她多方了解到,几年前听说的那种药在试验阶段就停了,“有人说副作用太大,有人说化解黏液的程度不够高”。
孙正龙曾关注过上述药物的研究状况,他自己面对的困难也不少。
最初,他找不到黏液的临床样本,辗转联络到一位上海的专家,从医院采集黏液标本做溶解测试。“做了好多年”,从毒性、药效、稳定性等多个标准来检验,他的尝试越来越接近于“有效”。
目前,李雁团队正在和孙正龙团队共同研发,实验结果超出李雁的预期,“不可思议”,从小鼠实验的结果来看,药物对黏液的溶解率高,副作用小。
此前,在理想情况下,李雁的手术方法能“管7-10年”,现实往往令人遗憾。有的患者确诊太晚,有的已经经历不规范的手术治疗,“再做起来的难度相当大,有的人反复做,三五次的都有”。
李雁说,国内能真正做好PMP手术的医生仅5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若患者选择就近就医,90%的PMP会被误诊,最常见的就是像徐友芳一样被误诊为妇科肿瘤。这位医生一方面期待药物,另一方面,他更在意降低误诊率、提高手术技术、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
李雁对记者表示,培养可识别、治疗罕见病的医疗队伍并不容易,多年来他一直在尝试,让病人能就近得到治疗,如果不能,起码让医生能意识到:“他可能是某种罕见病。”
针对一些医学生认为罕见病人数少,李雁建议,“去看看我的门诊,门庭若市”。
在科研立项之前,孙正龙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合作伙伴,还面临一些具体的困境。他太缺钱了——研发药物需要各类基因测序、构建细胞系等实验,一个实验成本就大几万元。起初,他“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一分钱都没有”。
孙正龙试过申请科研经费,找专家和企业,介绍研究成果,有人曾当场打断他:“不必做这个,你这个病才3万多人,就算全没了,对国家有多大损失?”有人会听他把话讲完,然后说:“这个项目很好,很有科学意义,前期结果也很好,但是很难产生实际价值,因此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方向。”
为了把项目继续下去,2020年,孙正龙离开了工作4年的中国科学院苏州医工所。换了城市和单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显微成像,同时寻求做PMP创新药的空间,领导批评他不务正业,学生质疑“做这个我能不能毕业”,最好的朋友也劝他放弃。
作为PMP病友群群主,刘晖当时很忐忑,她当然希望孙正龙能继续把药做下去。她几乎是除了研究者本人,对这个项目了解最多的人。平常,她不敢总问,怕给孙正龙压力,也怕打扰他。但实验每取得一点进展,孙正龙都会告诉刘晖。
听到研究中的纠结和压力,大多数时候,刘晖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孙正龙,她很清楚“如果他不做这件事,可以很滋润地生活”。
2019年父亲去世后,刘晖仍然在竭尽全力运营病友组织。群里有患者本人,还有患者的父母、儿女,刘晖见过最小的患者只有4岁。
她发自内心地希望孙正龙把药做出来,留住那些生命。她和群友商量,在群内筹一点钱,做个姿态,“尽管知道需要的是天文数字,但我们能筹一点,起码孙博士能有往前走一步的动力”。
然而孙正龙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对刘晖说,得病已经悲惨得不能再悲惨了,不能再要他们的钱。
当时,孙正龙已经决定去深圳湾实验室,“人跟着项目走”。他希望这个因改革开放而释放巨大能量的城市能容纳罕见病创新药的研发。
他总被问为什么坚持,答案是“看到PMP患者极其悲惨的生活状态,就有了研究的动力”。
PMP的一种残忍是,它让患者后期的生存状态变得“不体面”,面对前去拜访的记者,消瘦到只剩一把骨头的徐友芳说:“我不怕我今天就死掉,我怕我未来活着的每一天”。
不等怜悯和施舍,而是站出来
孙正龙对徐友芳很熟悉,他还能叫出很多患者的名字,提到“阿绍”时,他有些激动,“985大学毕业,设计院工作,结婚生子,阳光幽默”,他紧接着说,“想尽一切办法生存,国内外的医生都看了,孩子不到两岁他就去世了。”他顿了顿,补充道,“没有药,完全无解”。
刘晖说,2014年,28岁的阿绍确诊PMP,后成为病友群的核心志愿者。他还自发组织诊疗试验,寻找治病良方。
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名誉主委、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原副院长丁洁曾说,罕见病患者不是被动等着你去怜悯,等着你施舍,等着你治疗,他会站出来,他是个主动者。
在罕见病领域,患者是推动科研和临床治疗发展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曾经发起“冰桶挑战”的病痛挑战基金会理事长王奕鸥是一名罕见病患者,现在从事罕见病领域的社会支持工作。在一次论坛上,她提到患者要推动罕见病药物的研发,需要向企业和科研工作者说明临床急需性、患者分布等,关注伦理审查与科学审查、知情同意,共享疾病权威的研究者信息、诊疗中心信息给企业,积极参与研究的设计与执行。“当我们的需求没有被听到,我们需要更好的政策,我们就要去倡导。”
孙正龙正在研发的特效药并非PMP病友组织第一次与科研人员合作寻找可用药。
2014年,刘晖与结节性硬化症病友组织的志愿者交流时,偶然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生理学系教授张宏冰的联系方式,张宏冰长期关注结节性硬化症,发现了雷帕霉素在该病上的治疗效果。
雷帕霉素在部分良性肿瘤上有较好的疗效,PMP严格来讲也是一种良性肿瘤,在刘晖的联络下,张宏冰从研究PMP的专家许洪斌那里拿到临床样本,在实验室开展雷帕霉素治疗PMP的动物实验。
遗憾的是,疗效不确定。
这次尝试仍然让PMP患者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广泛联络专家,向医生和科研人员科普自己的疾病,自费出席国内外学术论坛,寻求被研究的可能性,甚至通过他们搭建专家与专家联系的桥梁。
阿绍病情恶化的那些年,正是孙正龙铆足了劲儿做研究的时间。阿绍离开的时候,孙正龙的研究有了些眉目。
2023年年中,孙正龙在深圳湾实验室正式组建了专门从事PMP研究的实验室,刘晖也准备组织疫情后的第一次医患线下会面。她希望孙正龙能在这次会面中,详细地和大家讲讲他的研究进展——患者在,专家在,医药企业也在。
现在,孙正龙和清华大学长庚医院、航天中心医院、广州肿瘤医院都建立了合作。他获取临床样本更加容易了。
他几乎每天工作14小时,项目每3个月作一次汇报,“没有成果很可能会终止”。除了负责PMP创新药物的研究项目,他还是深圳湾实验室生物影像平台的负责人。
好消息是,药的事目前看上去一切顺利,孙正龙团队最近刚刚跑通药物量化生产的渠道。但对创新药研究而言,仍然有一道大关卡要过——临床试验。
政府投入撬动资本和产业的投入
孙正龙算了一笔账。从今年年初到9月初,研究花费大约144万元。实际上,初步估计,临床前试验要花4500万元,到了临床试验的阶段花费估计是3亿-4亿元。
显而易见,光靠科研经费不可能支持如此庞大的一笔支出。“罕见病的募资非常困难。”孙正龙说。
近年来,研究罕见病领域的专家学者并不少,拿深圳湾实验室来说,新成立的罕见病高精尖研究联合中心是实验室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最大的问题则是资金的持续性。
“这件事必须要坦诚地去说,我们要理解市场规律,不能用所谓的慈善要求进行道德绑架。”清华大学药学院研究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药物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杨悦认为,药物研发需要钱,企业需要看到市场预期。“如果用其他的研究经费来补是没有持续性的。”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洪允提到,罕见病药物研发机制非常复杂,“尤其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我们在用国家的经费和企业合作(结合),我觉得有可能加速罕见病药物的研发进程,推动更多创新疗法惠及广大罕见病患者。”
罕见病药临床试验这几年数量不断增加,《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3年)》提示119项,比2022年的68项大约增加43%。
王洪允表示,所有的创新药研发都是非常艰辛的,罕见病药物研发除了正常的行业形势,不可避免地更依赖国家政策。杨悦说:“最关键的是,政策需要让企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预期。”
为了得到药企的支持,一些科研人员在研究罕见病药物的同时,希望能做到“广谱化”,找到药物对其他病症的疗效,努力追求更大的市场价值。
在采访中,孙正龙也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专利保护的担忧。2022年,国家药监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进行研究,形成修订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它首次提出给予罕见病新药等药品市场独占期,目前注明7年。
全世界都在探索激励罕见病药物研发的方式。美国FDA推出了一种“优先审评券”,发给研发出某些热带疾病、罕见病药物的企业,这张“优先审评券”药企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卖给其他制药公司,用于不符合优先审评的任何一款药物,审查周期缩短4个月——相当于,市场回报高的产品,可以将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公益属性更强的罕见病药物研发中。
2014年,罕见病药企BioMarin的第一张优先审评券以67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2017年6月,有企业以1.3亿美元购买优先审评券,加快HIV维持疗法的审查,该疗法于当年获得批准。同年,一种偏头痛生物制剂花1.5亿美元购买了资格被优先审查。
近年来,我国在药品保障和诊疗方面也为罕见病和创新药提供了绿色通道。去年,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审评工作规范(试行)》,可以被加快审评的药品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我国“罕见病目录”中的207种疾病。
对疾病自然史的研究,是人类认识疾病,进行诊断、治疗以及开展药物研发的基础。同样在去年颁布的《罕见疾病药物开发中疾病自然史研究指导原则》为推动和规范我国罕见疾病的疾病自然史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技术规范。该指导原则指出,我国多种罕见疾病缺乏可靠的疾病自然史研究数据。对罕见疾病,寻找患者加入疾病自然史研究可能存在一定挑战。鼓励在多地区、多人群中开展疾病自然史研究,特别是计划开展国际多中心研究的药物,通过对多地区人群的疾病自然史研究,有助于评估不同地区间潜在差异的影响。
在日本,药物安全与研究组织 (OPSR/KIKO) 负责为罕见病药物筹集研发的资金,制定减税的政策,另外对研发提供相关帮助,政府每年为罕见病研究小组提供约1000万-3000万日元的直接资助,也有税收的减免政策。
“第一步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必须要有药。”杨悦说,针对罕见病患者,政府要有所投入,从政策上要特殊对待。政府投入只是一个撬动的力量,引发投资和产业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不能用“慈善”绑架企业,要求药品定价必须便宜,让大家买得起。要把“有药”和后续的“便宜”“可及”分开考虑。首先要激励资本投入其中,后续再考虑“可及”的问题,“这在国际上是有经验可循的”。在促进罕见病诊疗和药物研发方面,我们要给企业参与的机会。杨悦说,“这种机会不是用砍价的方式获得”。
如今,孙正龙希望试验能进行得顺利一些,各类科研基金对罕见病项目研究的支持力度可以再放宽松一些。至于“几个亿”的事,他先不想了。为了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双向通路,在今年的国际罕见病日,深圳医学科学院、深圳湾实验室、北京协和医院三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罕见病高精尖研究联合中心。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作了“从罕见病到基础研究”的主题报告。一周后,她在微博上转发相关信息,并配文“一个都不能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雪儿 记者 秦珍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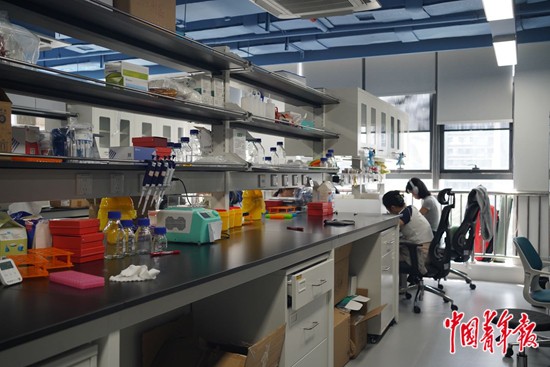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