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中,古厝的墙是殷红的,在梅雨季节,红墙常常冒汗,被雨滴勾出一种母性的和蔼与庄严,在一种无法言说的混杂气氛中令人倍感亲切又“肃生敬意”。
6月底的晋江,空气中总有一种湿凉的气质。
院里一落雨,红墙便成了我们兄弟姊妹的画板。自然,湿润了的红墙在我们眼里是学校残余颜料的好归宿,省了跑去后院提水润笔的麻烦,好方便我们把力气用在创造红墙这幅“惊世大画”上。
儿时画画的时机总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除了梅雨这一不可缺少的天时条件,最关键的是要避开母亲那一双如监控般的眼睛。每当我带头开始学起毕加索的抽象笔法,总要被母亲掀起裤子在大院里大庭广众之下打屁股以示惩戒。挨了打,我就在院里哇哇大哭,对这面红墙望而生畏,但不过几日,觊觎它的心又再次被噼里啪啦的雨声勾了起来。
那天,母亲要出差,又正好落了雨,屋里的孩子便从清晨就开始暗暗谋划着这幅“骇世”的红墙大画。一切准备就绪,我便如山大王般召唤家里众孩子挪桌子、拿椅子。我疯狂地向颜料板挤着从学校带回来的为数不多的颜料,拿起平常清扫桌子的毛刷,向那堵红墙用力一挥,红墙一瞬间便沾染了阳光的金黄。向旁边一扫,是一条金色的大道;冲着红墙颇有气势地一点,点出清源山上初升的红日。我咬着画笔,用大刷子尽情地铺画着世界的多彩与美好,那是专属于年幼的我眼中的花花世界。
正画得兴致高涨,下方突然传来爽朗的笑声,“妹妹啊,画得不错!阿公上次教你的《题西林壁》,你来画怎么样?就看你这小鬼理解多少了!”我回过头,阿公戴着眼镜举着报纸,原本贫瘠的脸上干涸出的许多褶子被灿烂的笑容占据了上风。
“来啊!放马过来!”我转过脸,注视着金黄的红墙,心中不免生出一阵得意,靠着记忆的头一句,蘸取了相适的颜料,只待阿公一声令下。“横看成岭侧成……”一句诗还未念完,我就照着脑子里记忆的图开始了自由创作。一高一低的山,在金黄的墙面上衬出勃勃生机,灰白的颜料被幼小的手勾勒出了不同造型的山峰,有远处的小山墩,有近处的大山腰。儿时的我在阿公的吟诵中仅仅听明白了所谓的“山”,懵懵懂懂之下,哪管什么意境和哲理,这面大红墙最后成了灿烂的山峰像,山峰被阳光沁染上了生机,与原诗中所写的沉重石壁截然相反,现在想来,这是独属于童年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阳光。
侧身一转,提笔一点,我签上自己还未练熟笔画的大名,随后从桌上跳下,跑至远处望向这面红墙。山峦起伏,阳光明媚,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我踮起脚拍了拍阿公的胳膊,忽然只觉一只温暖的大手揉搡着我的头发。“不错,阿公再去帮你画龙点睛!”话罢,阿公转身就拾起了院中书桌上的毛笔,蘸了蘸墨水,在我的“杰作”上将诗提了上去,我本想故作深沉地吟诗,摇头晃脑地诵到一半,却仅仅看得懂前两句。身旁的表兄弟一脸惊诧,想必是被我的画作与吟诵震住了吧。
还依稀记得那日梅雨过后,忽然放了大晴天,金黄的红墙在太阳的照射下格外耀眼。阿公与阿嬷都夸赞我绘画的超高天赋,但纵有天赋的滋润,也盖不住母亲回家时看到红墙变“黄墙”的怒火,我再次在院里挨了一顿打。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忍住了在眼周围打转的泪水,看着金灿灿的红墙,心中也得到了一丝慰藉。
3年后,我们大包小包搬离了古厝,我和母亲收拾到最后。关门前,我在院子的背面最后一次看向我的杰作,金黄的颜料在雨水洗涤下变得斑驳,山峰也不复以往的朝气,那时我并不知古厝红墙的命运究竟会去往何处。10年间,我与时光同行,奔忙于学业、生活,牵引记忆的绳索延展到了10年后的一天,趁着回家敬香,回到了当年的古厝。
儿时的家变为了老年活动中心,从大门一眼望去,依旧能看到儿时放学归家时红墙上雕刻的大“福”字。我绕至背面,是13年来仍然矗立着的山峰,只不过这面红墙已不再是我与阿公的独作,岁月赋予了红墙时光的印记,为它绘上了四季生动的轮回变迁。我拿出了画板,坐在那把当年阿公坐过的椅子上,在阳光下绘制着这堵记忆中的红墙。本想学着儿时幼拙的模样描摹出墙上的山峰,但总归不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
默读红墙上残留的诗句,一墙之隔,墙外是古厝的肃穆,墙内是专属于童年的快乐与幸福。古厝的红墙,绘制了我童年的天真与未来生活的色彩,在13年后的今天,温暖我,指引我,照亮我……
古厝的红墙,红了17年,还是殷红。
红墙的杰作,至今已13年,颜色淡了,却依旧在时光中如灯般不眠地亮着……
庄思鑫(17岁) 福建省晋江市英林中学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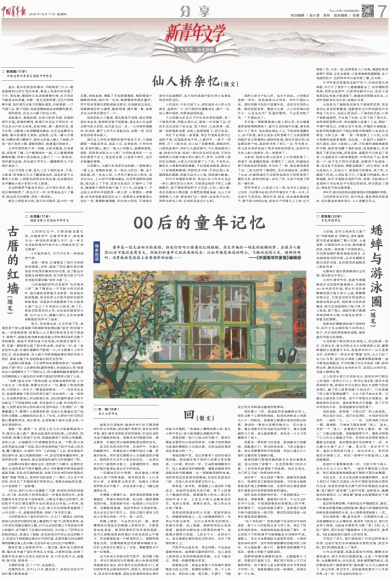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