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中的小人物,书写历史的另一面
闫珍珍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1月03日 08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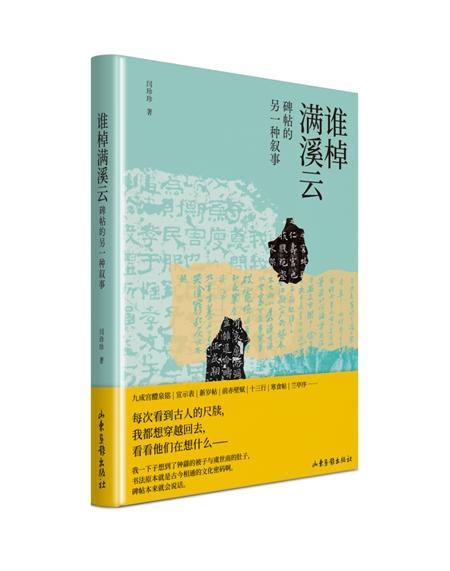
古人把书信叫作“尺牍”。一片小小的木简,承载了太多情感。碑帖的涵盖范围就更大了,它可能是古人的公文、书信,也可能是为纪念某人或某事而立的刻石。数千年以后再看,它又成为文学、历史、书法、美学等多种元素的载体。
最近出版的《谁棹满溪云:碑帖的另一种叙事》一书,以文本和图像为载体,将地上之材料如史书、诗歌、散文,与地下之材料相结合,赋予碑帖更为生动的人文意义。大到王朝的兴衰更替,小到文人的细腻情思,乃至普通农夫的思乡之情,都在历史现场中一一还原。
一个秦国农夫和他的兄弟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国发动了对楚国的灭国性战争。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四号秦墓木质套棺的陪葬箱内出土了两块木简,正背两面均有墨书文字。记录了这场战争前,两名士兵给家中的问候。
墓的主人叫“衷”,写信的人,是他的兄弟“黑夫”与“惊”。发信地址是“黑夫”与“惊”作战的地方淮阳(今河南周口附近),收信地址是他们的家乡安陆(今湖北云梦)。某次在山东博物馆看到这件文物,在一旁展出的,还有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兵马俑复制品。主办方特意把湖北文物和陕西文物放到一起展,让历史的现场似乎就在眼前。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往往是被大人物书写的,而像“衷”这样,能将墨迹保留到两千多年后的小人物,屈指可数。通过这些墨迹,我们猜想,“衷”的一生会经历什么?是不是像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无数小人物一样,为徭役等而发愁。也许有幸活到暮年,弥留之际想与兄弟合葬在一起,却发现找不到任何“黑夫”与“惊”来过的痕迹,除了这木简上的墨迹。
文本和图像都是传播信息、表达感情的媒介,而有时候,这两种媒介还可以互文,成为我们了解古人的“双重证据”。如果没有秦简的出土,我们可能以为,隶书就是秦代以后才有的,但“睡虎地秦简”让隶书的产生追溯到战国晚期。
“隶书者,篆之捷也”,尤其是“黑夫木牍”,有些字出现了特别长和夸张的波磔(书法右下捺笔——编者注),整个字还往右下倾斜,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汉简。
他用一生让王羲之“穿越”到唐朝
在西安碑林,有一件小人物完成的名碑——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它的撰文者是唐太宗李世民、太子李治和玄奘法师,而作者是来自东晋的王羲之。是小人物怀仁,让王羲之“穿越”到了唐朝。
关于怀仁的生卒,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知道,他是弘福寺众多沙门中的普通一员。集书开始的时间也没有具体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是长安众多僧侣里写王羲之书体最好的一个。他也许被玄奘西天取经的经历深深打动,也许见证了玄奘回长安时“四民废业,七众归承”的高光时刻,让他的信仰更加坚定,所以接受了“集字圣教序”这份高难度的工作。
说这份工作难度高,原因有二:一是集字只不过是一种收集和模仿,士大夫们瞧不上这份工作,不愿去做;二是对怀仁来说,集字的难度不只是从丰富的王羲之书迹中寻找字形,还要根据章法的需要重新创作,夸大或缩小某一个字,以求得行书中的节奏变化和行气。
好在怀仁那时的集字来源非常可靠——贞观十三年(639),李世民命褚遂良等人对王羲之书迹进行了鉴定整理,统计出内府共收藏右军书二千二百九十纸。
然而,从李世民完成《圣教序》,到怀仁集字摹勒上石,中间却隔了25年。是集字太难,耽误时间太长吗?并不是。看看这25年的波谲云诡、物是人非:写完《圣教序》后第二年(649),李世民就龙驭宾天;永徽六年(655),李治打算废黜皇后王氏,改立昭仪武氏,褚遂良冒死劝谏被降职,在流放中绝望死去,《同州圣教序》是他死后追刻;武则天如愿当上皇后,显庆五年(660),李氏王朝已然是武氏天下;麟德元年(664),玄奘油枯灯灭,走完了65岁的一生。
又8年之后,怀仁终于实现了愿望,把相隔三百多年的王羲之和李世民、李治、玄奘放在一个碑上。等怀仁集字完成时,碑上所提及的人,大多已经去世。怀仁这一生,人们只知道他做了这一件事,但这件事足以让他载入书史。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在宋之前并不被重视,文人士大夫都不屑于学,称之为“院体”。直至明清时期,王羲之真迹毁佚殆尽,这个碑才被学者重视起来。可能正因为不被重视,让它躲过了战乱和掠夺,让我们今天仍能在西安碑林见证这场神奇的“穿越”。
“二王”家族里的寻常小事
清代人把书法分为帖学和碑学,帖学是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圭臬的传统名家书法,而碑学大多指无名小人物的平民书法,如康有为所言魏碑“虽穷乡儿女造像”,无不佳者。就有这样一个帖,虽是出自“二王”一门,却有龙门石窟造像的碑影,它就是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
《万岁通天帖》是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荟、王慈、王僧虔等王氏七人十帖装裱而成。这些信札,从东晋到南梁,历时二三百年。唐代以来便有不少书家,从《万岁通天帖》中揣摩六朝人的笔法。直到清代之后,越来越多的碑刻墓志出土,人们才发现,这个家族的书风演变与整个书法史息息相关。
启功先生曾用《万岁通天帖》与《龙门二十品》作对比,他说:“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我们未曾见过龙门石窟那些造像未刻前的样子,也没有看过洛阳那些墓志的书丹,但王氏一门的书迹给出了想象:也许,那时南北的文化交流,并不像地理上那么割裂,而南朝的书风传到北方,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漫长。
其实,《万岁通天帖》不只是王家人笔法的传承,这些信关乎生老病死、悲欣心情、寻常问候,既有书体演变的轨迹,又是他们生活过的痕迹。
其中,《姨母帖》是王羲之在姨母去世后,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只有短短十几个字,却表达了无法言语的伤痛:哀痛摧剥。《初月帖》是王羲之到达山阴后给朋友的一封回信:“过嘱。卿佳不(否)?”——“你的嘱托我收到啦,你怎么样呢?”古人问候的方式跟我们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还有王徽之的《新月帖》,就是叮嘱那个收信的人“好好吃饭”。“卿佳不”“食不”……看完《初月帖》再看《新月帖》,原来古人在难过的时候,问候也不过是“吃了吗”。
(作者系《谁棹满溪云:碑帖的另一种叙事》一书作者)
闫珍珍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1月03日 08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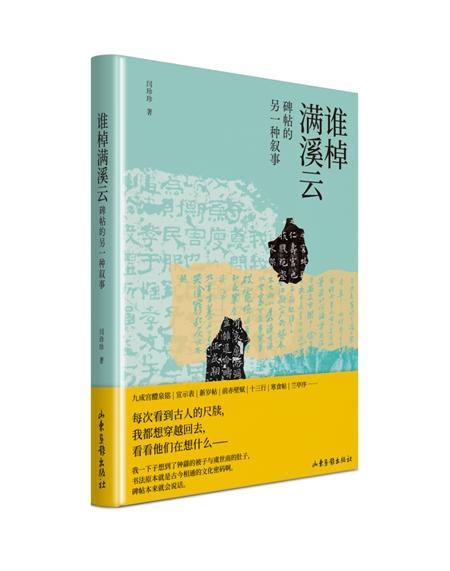
古人把书信叫作“尺牍”。一片小小的木简,承载了太多情感。碑帖的涵盖范围就更大了,它可能是古人的公文、书信,也可能是为纪念某人或某事而立的刻石。数千年以后再看,它又成为文学、历史、书法、美学等多种元素的载体。
最近出版的《谁棹满溪云:碑帖的另一种叙事》一书,以文本和图像为载体,将地上之材料如史书、诗歌、散文,与地下之材料相结合,赋予碑帖更为生动的人文意义。大到王朝的兴衰更替,小到文人的细腻情思,乃至普通农夫的思乡之情,都在历史现场中一一还原。
一个秦国农夫和他的兄弟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国发动了对楚国的灭国性战争。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四号秦墓木质套棺的陪葬箱内出土了两块木简,正背两面均有墨书文字。记录了这场战争前,两名士兵给家中的问候。
墓的主人叫“衷”,写信的人,是他的兄弟“黑夫”与“惊”。发信地址是“黑夫”与“惊”作战的地方淮阳(今河南周口附近),收信地址是他们的家乡安陆(今湖北云梦)。某次在山东博物馆看到这件文物,在一旁展出的,还有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兵马俑复制品。主办方特意把湖北文物和陕西文物放到一起展,让历史的现场似乎就在眼前。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往往是被大人物书写的,而像“衷”这样,能将墨迹保留到两千多年后的小人物,屈指可数。通过这些墨迹,我们猜想,“衷”的一生会经历什么?是不是像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无数小人物一样,为徭役等而发愁。也许有幸活到暮年,弥留之际想与兄弟合葬在一起,却发现找不到任何“黑夫”与“惊”来过的痕迹,除了这木简上的墨迹。
文本和图像都是传播信息、表达感情的媒介,而有时候,这两种媒介还可以互文,成为我们了解古人的“双重证据”。如果没有秦简的出土,我们可能以为,隶书就是秦代以后才有的,但“睡虎地秦简”让隶书的产生追溯到战国晚期。
“隶书者,篆之捷也”,尤其是“黑夫木牍”,有些字出现了特别长和夸张的波磔(书法右下捺笔——编者注),整个字还往右下倾斜,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汉简。
他用一生让王羲之“穿越”到唐朝
在西安碑林,有一件小人物完成的名碑——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它的撰文者是唐太宗李世民、太子李治和玄奘法师,而作者是来自东晋的王羲之。是小人物怀仁,让王羲之“穿越”到了唐朝。
关于怀仁的生卒,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知道,他是弘福寺众多沙门中的普通一员。集书开始的时间也没有具体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是长安众多僧侣里写王羲之书体最好的一个。他也许被玄奘西天取经的经历深深打动,也许见证了玄奘回长安时“四民废业,七众归承”的高光时刻,让他的信仰更加坚定,所以接受了“集字圣教序”这份高难度的工作。
说这份工作难度高,原因有二:一是集字只不过是一种收集和模仿,士大夫们瞧不上这份工作,不愿去做;二是对怀仁来说,集字的难度不只是从丰富的王羲之书迹中寻找字形,还要根据章法的需要重新创作,夸大或缩小某一个字,以求得行书中的节奏变化和行气。
好在怀仁那时的集字来源非常可靠——贞观十三年(639),李世民命褚遂良等人对王羲之书迹进行了鉴定整理,统计出内府共收藏右军书二千二百九十纸。
然而,从李世民完成《圣教序》,到怀仁集字摹勒上石,中间却隔了25年。是集字太难,耽误时间太长吗?并不是。看看这25年的波谲云诡、物是人非:写完《圣教序》后第二年(649),李世民就龙驭宾天;永徽六年(655),李治打算废黜皇后王氏,改立昭仪武氏,褚遂良冒死劝谏被降职,在流放中绝望死去,《同州圣教序》是他死后追刻;武则天如愿当上皇后,显庆五年(660),李氏王朝已然是武氏天下;麟德元年(664),玄奘油枯灯灭,走完了65岁的一生。
又8年之后,怀仁终于实现了愿望,把相隔三百多年的王羲之和李世民、李治、玄奘放在一个碑上。等怀仁集字完成时,碑上所提及的人,大多已经去世。怀仁这一生,人们只知道他做了这一件事,但这件事足以让他载入书史。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在宋之前并不被重视,文人士大夫都不屑于学,称之为“院体”。直至明清时期,王羲之真迹毁佚殆尽,这个碑才被学者重视起来。可能正因为不被重视,让它躲过了战乱和掠夺,让我们今天仍能在西安碑林见证这场神奇的“穿越”。
“二王”家族里的寻常小事
清代人把书法分为帖学和碑学,帖学是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圭臬的传统名家书法,而碑学大多指无名小人物的平民书法,如康有为所言魏碑“虽穷乡儿女造像”,无不佳者。就有这样一个帖,虽是出自“二王”一门,却有龙门石窟造像的碑影,它就是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
《万岁通天帖》是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荟、王慈、王僧虔等王氏七人十帖装裱而成。这些信札,从东晋到南梁,历时二三百年。唐代以来便有不少书家,从《万岁通天帖》中揣摩六朝人的笔法。直到清代之后,越来越多的碑刻墓志出土,人们才发现,这个家族的书风演变与整个书法史息息相关。
启功先生曾用《万岁通天帖》与《龙门二十品》作对比,他说:“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我们未曾见过龙门石窟那些造像未刻前的样子,也没有看过洛阳那些墓志的书丹,但王氏一门的书迹给出了想象:也许,那时南北的文化交流,并不像地理上那么割裂,而南朝的书风传到北方,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漫长。
其实,《万岁通天帖》不只是王家人笔法的传承,这些信关乎生老病死、悲欣心情、寻常问候,既有书体演变的轨迹,又是他们生活过的痕迹。
其中,《姨母帖》是王羲之在姨母去世后,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只有短短十几个字,却表达了无法言语的伤痛:哀痛摧剥。《初月帖》是王羲之到达山阴后给朋友的一封回信:“过嘱。卿佳不(否)?”——“你的嘱托我收到啦,你怎么样呢?”古人问候的方式跟我们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还有王徽之的《新月帖》,就是叮嘱那个收信的人“好好吃饭”。“卿佳不”“食不”……看完《初月帖》再看《新月帖》,原来古人在难过的时候,问候也不过是“吃了吗”。
(作者系《谁棹满溪云:碑帖的另一种叙事》一书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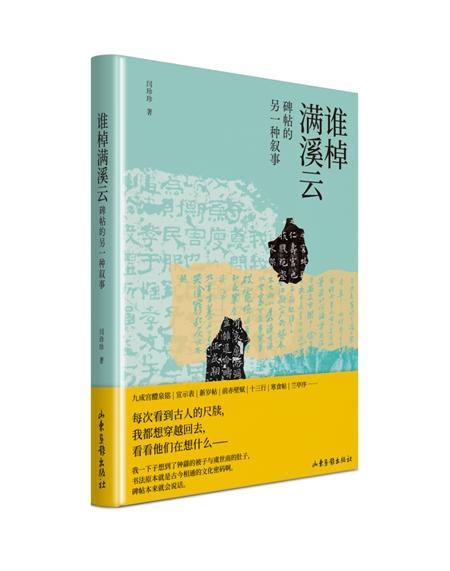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