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卡洛琳接起电话的时候,她的丈夫托马斯·萨金特正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准备出门,他要搭乘火车去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研究生们在等着他上宏观经济学理论课。
然而,这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早晨,电话里带着“瑞典腔调”的人为托马斯·萨金特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这位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同获奖的还有他的老同学、老同事——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教授。
比起西姆斯的“惊喜”,萨金特显得很“淡定”。“我还没备好课。”这位68岁的老教授说。他既没有马上将喜讯“昭告天下”,也没有对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任何获奖感言,而是按时登上了纽约开往普林斯顿的列车,并伏在车厢的小桌上认真备完了课。
“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讲不好课,学生们是不会饶恕我的。”萨金特说,他让随后而至的所有采访电话都“扑了空”。
这份“坚持”早在50年前就显露无遗。那时,17岁的高中生萨金特正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提前一年毕业,去俄勒冈州立大学攻读;或者再等一年,就能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而托马斯的父亲正好有机会在俄勒冈州开一家公司,全家都能搬去,“我不要去俄勒冈,我要去伯克利。”如今91岁的查尔斯回想起儿子当时倔强的表态,禁不住笑出声来。全家人“一路向北”搬迁,而那个 “有主意的年轻人”则沿着他的学术道路奔跑下去。
在一些学者看来,萨金特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实至名归,是“终于给他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霍德明博士称,萨金特、西姆斯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结合方面,是获得学界肯定的。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直言“对评选结果感到遗憾”,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就表示,“今年诺奖没找到重点,只得给了两个时效性不强、早晚都该给予承认的纯技术方面的贡献者。”
这个颇具争议的大奖惹得众经济学家唇枪舌剑,萨金特的父亲却认为,获奖“对托马斯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在以往的生活中萨金特获得过很多奖项——从初中的溜溜球比赛第一名到伯克利后备军官训练队优秀军校学员奖,而且“他玩棒球,是全能型的”。
如果为“全能型”的萨金特涉足的学术领域画张地图,那绝对称得上是横跨文理。他在伯克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研究经济学和在几所大学任教的过程中,这个“一直逃避数学”的青年学者渐渐意识到了数学的重要性。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投入数学学习,甚至已经当上教授了,还常常到数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堂上去旁听。
萨金特努力让“外行”的记者们了解自己的研究,“我们基本上算是‘数据历史学家’”。而在跟诺贝尔基金会官员的对谈中,萨金特干脆更加简要地表示,“我们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人物,靠观察数字来努力搞清楚正在发生的问题。”
萨金特这种平实、通俗的风格在严肃的经济学理论界是出了名的。在被问到他的理论可否预测资产价格时,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市场价格集合了所有交易者的信息,所以很难预测。”而回到母校伯克利作演讲时,他直言“觉得毕业演讲都太过冗长”。在一张他与银行家的合影中,他身着夹克、卡其布裤,在西装革履中显得格外醒目。
不过,萨金特对学生的要求从不“休闲”,尽管他讲到兴起就会一屁股坐到讲台上。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教授回忆自己的老师“是个科学家”,教书一流,说话时学术性很强。面对学生提问,他往往会抛出一些复杂的方程式,一般人很难弄懂。
曾在芝加哥大学上过萨金特课的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建甫也说,萨金特是一位自律甚严,上课从头到尾都在写板书的教授。这位教授年轻时还服过两年兵役,至今哪怕出差在外,他也要到酒店的健身房锻炼。
“他非常严格,即便是研讨小组,学生也不得无故缺席,还规定讨论时不得胡乱引申。”一个学生回忆道,在要找工作的那个学期,萨金特会把所有学生组织起来,一个个进行模拟面试。有学生私下请教论文撰写中的问题,他也会坚持用正式“答辩”的方式解决。
“那时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一批学生。”萨金特说起与西姆斯的同事生涯时表示。
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朱胜豪博士,曾听到西姆斯演讲,而萨金特一直坐在台下,多次对老同事发问。“两位大师似乎不为名声所累,”朱胜豪说,“在面对学生时,他们都相当和善。”
在纽约大学,萨金特和妻子卡洛琳组织了一个论文研讨小组,他负责学术,妻子提供食品饮料,还用自家的炉子烤制风味蛋糕。小组讨论几乎风雨无阻,地点有时在学校,有时就在萨金特自己家中。
第一次在小组发言的朱胜豪被萨金特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语法错误。讨论结束后,他又被叫到了办公室。“在美国工作,你的英语要提高。”萨金特说,他帮朱胜豪报了语言课程,还替他付了几百美元学费。
除了严谨和亲善,许多学生都知道,老萨最爱“讲故事”。在普林斯顿大学宏观经济理论课上,他会讲起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22岁骑在马上打英国人,边打边想出了美国经济框架。而讲到“社会主义福利模型”,他会说起洛克菲勒和经济学家兰格的一段往事,感慨“那时的芝加哥真是个社会主义的天堂”。从打野鸭到钓鲑鱼再到选红酒,萨金特什么都讲。 他的学生至今还记得这位“文科出身”的经济学教授的名言:“《安娜·卡列尼娜》开篇讲,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告诉你们,静态模型都是相似的,随机模型各有各的不幸。”
即便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新闻发布会上,萨金特也没忘记对“严肃的问题”做一些“幽默的化解”。在西姆斯回答完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后,话筒被推给了萨金特,结果他“搪塞”了一句:“我以为你会问欧元的问题。”一阵笑声和掌声过后,记者配合地又问:“那欧元会怎样?”这一次,萨金特直接把话筒推给了身边的西姆斯,并带着调侃的语气说:“你觉得呢?”又引来一阵哄笑。
然而,幽默回避似乎更加说明萨金特对现实问题的无奈。他和西姆斯都坦言,他们的研究并不能给当下的金融混乱带来便捷的解决之道,因为目前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还在不断地发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快刀斩乱麻”,但他们一直力图“找到解决这些混乱的核心”。
“近期什么事情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肉价吧!”浙大经济学教授史晋川用“猪肉”来解释萨金特“理性预期学派”的要义——今年猪肉价格大涨,养殖户以此判断明年价格还涨,只考虑一个因素,这就是静态预期;聪明点的养殖户不仅看今年,还看去年,还总结去年预测今年时的偏差,这就是适应性预期;更聪明点儿的养殖户在这两者基础上考虑,想到价格已经这么高了,肯定有更多人养猪,猪多了,价格就会下降。于是,第三个养殖户没有“跟风”,避免了价格大起大落带来的损失,这就是理性预期要达到的效果。
然而,在理性预期学派接连被诺贝尔经济学奖青睐之时,世界经济却在不断陷入困局。萨金特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试图证明,政府干预是“无效的”。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这即是中国人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的最佳政策是干脆“不折腾”,无为而治。
他还曾经用林肯的一句名言对理性预期作出解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为拯救华尔街那些贪婪的‘肥猫’一再推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又给美国和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危机。这时,两位美国学者以‘宏观经济领域的因果关联’研究成果而获奖,岂不是一种幽默?”评论家苏文洋坦率地说起诺奖对现实生活不起什么指导意义。
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则认为,经济学诺奖的终极目标是获奖者对学术圈自身的影响,而这种影响90%来自方法论的突破,10%是思想的进步,今年明显属于前者。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一直坚称,他们从不根据近期事件选择得主,奖项跟政治更没有关系,但萨金特的获奖无疑显示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理性预期”的重要性。
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经济在目前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应采取何种政策的提问时,萨金特只是耸耸肩,称对于他并不熟悉的领域,不会妄加评论。
“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许小年在微博上不客气地说,“一句学以致用,害得中国没了学术。”
10月10日下午1时20分,普林斯顿大学会议厅里,参加诺奖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占据了坐席前两排,而后面则挤满了慕名前来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萨金特在经久的掌声中落座,掌声又持续了近半分钟,他有些局促地微笑着,向台下招手。
他似乎更享受另一种掌声。在某一堂宏观经济学和《百年孤独》“串讲课”即将结束时,他向学生们告别,“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我看过许多学生,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超出我教过的平均水平,我想说,不要放弃研究。”说着,他拍掉手上的粉笔灰快步向门口走去,学生们集体鼓掌,直到他走进楼梯再也听不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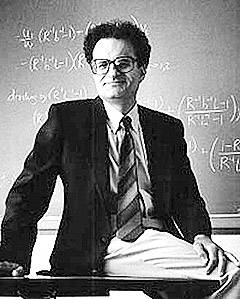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