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历史和故事,可能为很多人所不知。
1990年3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出访美国、新加坡等地。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朱市长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此时,上海的金融官员对市长的时间表闻所未闻。
6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受命空手上任,“感到自己就像浪涛中的一叶小舟那样无助。” 35岁的尉文渊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后者彼时正沉浸在炒卖国库券的快乐中。而全上海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3家——万国、申银和海通,比较成形的股份制企业11家,够上市资格的则仅仅6家。
上海即将开市的消息,让深圳心急火燎。过去的一年,深圳一直在向中央申请开办证券交易所,迟迟未得回复。尉文渊紧锣密鼓,深圳人决定加快脚步。
12月1日,深圳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开市。说是开市,实际上并未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批文,开市仪式也低调得多。匆忙开市的深圳交易所甚至没有电脑交易系统,第一天成交股票8000股,采用的竟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纯手动模式。
3年后,深圳股市首次闯入国际市场,与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股市行情。当时,中国没有证监会,国家体改委时任副主任刘鸿儒在交易所里惴惴不安。上午9点,他和同僚们死死盯着蓝色大屏幕,这时出现海外投资者第一次叫价,可惜没有成交。过了大半个钟头,所有人如坐针毡,第一笔交易最终成交:南玻A股两千股。
微小的交易让刘鸿儒心得意满,他跟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吧。”好多人围在一起拍了个大团圆。更多的人只是在看热闹,他们不解地嘀咕:“不是在拍电视吧?”
但是,渐渐地,人们知道了股票的力量,只是能沉得住气的人很少。名为康柏华的股民被套15天,选择上吊自杀。他永远不会知道,仅仅一周后,股市一飞冲天。
中国股市诞生的过程如此仓促忙乱,却不妨碍这个市场日后的波诡云谲:各种“系”翻云覆雨,“ST”股票的出现更激起无限忧虑与激荡。
基于上市公司盈利状况,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和金融专家设计了一套警告制度,对连续数年亏损的股票进行特别处理。很长时间内,被挂牌ST成为上市公司的“耻辱柱”,那意味着盈利不佳,提醒投资者敬而远之。然而,退市机制的粗糙让ST成为利润滋长的最后一公里。ST股票将胆小者吓退的同时,引来大批觅食者:神秘散户、股市高手、知名大牛、企业高管、商界大佬,连番上演令人目眩的财富神话。
饶有趣味的是,ST投资客中的成名者多以夫妻档面貌示人,其实不过为多开账户,掩人耳目。《妖股》中说:“最牛散户”叶晶、刘芳夫妇在ST金泰上大赚两千万,媒体穷追不舍,竟然发现刘芳对“丈夫叶晶已将账上股票悄悄炒到千万”毫不知情。
同属“千万级别”的,还有任淮秀夫妇。2006年,ST盐湖还叫S*ST数码时,连续三年亏损,面临退市,人民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任淮秀5元抄底,最终与做公务员的妻子股票账户收入5000万。而后媒体爆料,“五千万教授”正是S*ST数码重组顾问,个中故事,意味深远。
人前风光,人后究竟有多少没落和隐秘,不为人知。可是,书中披露的ST公司高管恩怨情仇、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较量、宏观政策和产业规划的变更,似乎预示某种更大的力量操纵掌局。而本书作者作为潜伏股市多年的财经记者,尽管表述节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深深忧虑和思考,还是令人寒凉。
不过,有趣的是,大佬与散户也会相中同一只股票,与其归结为巧合,不如说他们被同样的利益所吸引。谁又能想象,刘芳夫妇大赚千万的ST金泰,会成为羁绊昔日首富黄光裕的绊马索。
十年前,红极一时的“K先生”吕梁黯然离场时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是大家宠庄爱庄的年代。无股不庄,无庄不股,中国股市赌性十足,换手率堪称世界第一。中国股市违规操纵比比皆是,黑幕重重,人称上市圈钱,公司偷钱,庄家抢钱。”这么看来,生物界的丛林法则同样适用资本市场:一群小鱼后面跟着若干大鱼,大鱼无影无踪,却无处不在。
因此,十年后,当初的大庄家退隐江湖,新庄家春风吹又生,唯独散户命如蝼蚁。
2011年夏末,美股暴跌,引发全球股市一路下行,让香港影片《窃听风云》成为距现实最近的隐喻。一句台词说得好:“我的命,我自己操盘。”然而,在那个收盘、复盘的游戏中,每个人都是环环相扣的“被操盘”者。“自己操盘”的结果,只能是出局。
这,就是《妖股》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游戏系统的规则。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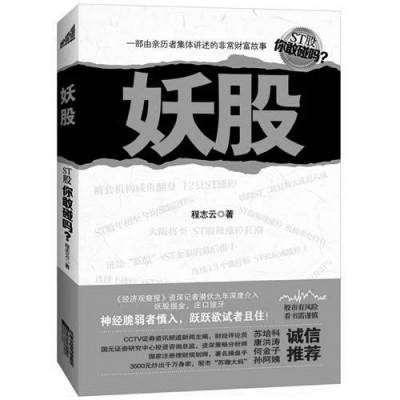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