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向左边比了下手势:“他这边,再向更远处延伸,我们称之为议事规则,是民主。”
她看向另一边,又比了比:“从他再往后推,是南塘,是中国农村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纠结。”
左边是身穿浅灰色西装的袁天鹏。几年前,他留美归来后翻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这是美国最广受承认的议事规范,“大到国民大会,小到小学班会”都可使用。
另一边坐着安徽阜阳南塘村村民杨云标。
这是4月25日,新书《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研讨会正在人民大学一间会议室里举行。
坐在中间的寇延丁本人,是“下乡”的记录者,也是连结这两端的“媒婆”。如今,人们只需要翻开书,就能知道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洋规则”和“土问题”如何走到了一起。
2008年,袁天鹏带着自己翻译的大厚书走进南塘村。那本582页的著作对如何提出议事事项、如何听取和发表意见、如何提出动议和如何表决,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它本质上就是会议上的法治,其核心原则就是要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
不过,当这一大段话碰上南塘,最终只变成一件事:这辈子没少开会的中国农民开始重新“学开会”。他们学着破除“领导说了算”的老观念,学着如何在平权的会议里高效地作决定,学着如何尊重自己的权利也尊重他人的权利,学着如何在面朝田地的生活中真正实践“民主”这个大词。
“对于我们经常思考民主现状问题的人,这一棒子是有力度的。”研讨会主持人、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说。他甚至还干脆地表示:“如果以后谁要再问我民主怎么办,我就直接把这本书递给他。”
从美国带了两斤民主回来卖卖
当然,起初这事看起来可没那么顺利。
2008年10月,袁天鹏带着“洋玩意儿”议事规则进村。按照当地一位官员的说法,这算是“从美国带了两斤民主回来卖卖”。
培训会在南塘村兴农合作社的一楼大厅举行。三层楼房刚刚盖起,乡亲们骄傲地称之为“大楼”。不过,大楼内部装修尚未完成,大厅的砂土地面凹凸不平。听众大多数是兴农合作社的骨干——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很少有人学历高过初中。他们挤坐在红色的长凳上,有人煞有介事地戴上老花镜,从塑料袋里掏出笔和一沓稿纸;还有人朝地上吐了口痰,然后直起脖子准备听听美国回来的专家讲些啥。
身高1.8米多的“归国专家”穿着灰色抓绒衣,打开自备的投影仪,以及“与这种环境格格不入的苹果小白本”。南塘没有“幕布”,PPT内容只能显示在几张粘在一起的大白纸上。
这与袁天鹏往日在城市里的课堂完全不同。那时,他大多西装笔挺地站在讲台上,把术语和英文挂在嘴边,语速飞快,“用逻辑分析推进课堂内容”。
“罗伯特”是课堂的主角。1863年美国内战时期,身为工程兵军官的亨利·罗伯特帮忙主持一场会议,没想到却把会给开砸了。他决心下功夫研究议事规则,并于1876年出版《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书,“在总体原则上,以国会的规则为基础;在具体细节上,以一般社团组织的需求为对象;不仅仅要包括组织和运作会议的方法,包括官员及其职责,包括各种动议的名称,还要系统地阐述每种动议的目的、效果、可辩论性、可修改性……”
可当袁天鹏对着话筒讲出“罗伯特议事规则”一词时,一位花白头发的大妈用阜阳话大声奚落了一句:“啥罗伯特,就是萝卜呗!”
台下“哄”地爆发出一阵大笑声。
对袁天鹏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当他试图让村民们自己商议并表决出一套课堂守则时,有人提出上课应不准睡觉。但立刻引发了大讨论:反对者称,如果实在特别瞌睡,就可以睡;折中者认为,睡觉也行,但不能打扰别人。
气氛挺热烈,但讨论迅速偏离了方向。一个村民说起了解决办法,“一人发一个大辣椒”;戴着解放帽的老支书挥舞着双手,激动地分析了原因:“睡觉不睡觉在于领导讲话,讲得好了根本不害困!”
接下来起身发言的大妈将争论往回拉了拉:“这些客人来到这里,给我们办这个学习班,我们有理由也好,没理由也好,再困也要坚持,不能睡觉。”最后,她坚定地总结,“一句话,睡觉是错误的,不能睡觉!”
有人紧接着问:“给老师提意见可以吗?上课的时候看到有人睡觉,就要改变方式讲这个课。”
又跑题了。
袁天鹏或许对这种开会方式感到陌生,但在杨云标看来,一切再正常不过。
这就是南塘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村庄。按照寇延丁在书里的描述,这里都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既没有自办企业,也没有特色农产品。
杨云标就在南塘村长大,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在大学修读了法律专业成人教育课程,取得大专文凭,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是个白领。1998年,他回老家准备复习律师资格考试,却发现乡亲们上访总是碰壁。于是他彻底回归农村,和乡亲们一起解决问题。效果不错,这里的上访越来越少。2004年,他索性带着一帮六七十岁的骨干成立兴农合作社,并在其中设立老年人协会、农资统购统销部、酿酒坊等部门。
在农村生活,他这样看待农民的维权:“他们反抗并不是为了多要一点钱,而是希望获得尊重。我们天天说,自己一定要民主。”
为此,杨云标一度认为,只要是开会,“参加的人越多越好,发言的人也越多越好”。可“民主”却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到来,相反,“开会”简直要把一切都毁了。
他总结了南塘开会的几大问题:“开会不就是个侃嘛”,最后离题万里;提意见时,往往对人不对事,谈不拢就骂人、拍桌子;更多时候是一片沉默,大家主张“听领导的”。
“开会成了一件特别折磨人的事情。”杨云标紧紧拧着眉头说。
因此,当致力于NGO发育的朋友寇延丁向他介绍有这样一种“教人开会”的议事规则,并可以解决“跑题、野蛮争论和一言堂”时,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请袁天鹏来南塘。
孙中山早就“结识”了罗伯特
袁天鹏此前没见识过农村的会场。但在北京邮电大学读书时,他是学生会主席,还是“全国优秀学生干部”,没少开会,更知道“不公平、没效率”是中国会议的特色。1999年,他赴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留学,在那里发现了完全不同的开会方式。
入选学生议会后,议会秘书递给他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初次相遇并不愉快,袁天鹏吃惊地发现,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单词,他“似乎都认识,但内容却看不懂”。
进入会场,他看不懂的就更多了。议会主席虽然坐在中心位置,却不能表态,“像个拍卖师一样点了这个点那个”。主席得为每位发言者计时。当一人结束发言后,主席会问:“有没有反对意见?”在一群高举的手臂中,反对意见优先,这使得争论双方能够平衡登场。
如果发言中攻击他人,会被主席立刻打断。因为“规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不许质疑动机——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
袁天鹏实在接受不了这一点。在他参加的会议里,许多意见背后都有私利作祟,“那是明摆着的”。
不过,美国同学给出了看上去挺在理的答案:“一来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二来会议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所以指责他人动机毫无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矛盾。”
经过每周一次的“议会训练”,袁天鹏渐渐熟悉了这种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为依据的会议。开会时,由议员提出供讨论和表决的事项名为“动议”,如果另有议员表示“附议”,即“同意讨论”,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话题。赞成者、反对者轮流发言。当然,这种发言并不是非黑即白,人们有时还会设计出与最初动议差别颇大的“修正案”。
表决仍是关键时刻,赞成票多于反对票意味着动议通过。若打成平局,则说明动议被驳回。他们并不计算弃权票,因为弃权者两种结果都能接受,并且“不想用自己的一票影响结果”。
这样的会议符合亨利·罗伯特的说法,议事规则的精神在于“要让强势的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面”。
比起工科老本行,袁天鹏更着迷于这些规则。他在2006年着手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并成为美国最大的议事规则推广机构“美国议事专家协会”唯一的中国会员。
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少为中国人所知的议事规则,其实早在1917年就已进入这个国家。
那一年,孙中山在研究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基础上,又参考了美国女权运动者沙德的《议事规则》,撰写了五卷著作。
在序言里,孙中山写道: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自合议制度始于英国,而流布于欧美各国,以至于今,数百年来之经验习惯,可于此书一朝而得之矣……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
这本著作,最终被定名为《民权初步》。
精英们和农民们碰到的问题大同小异
将近100年后,袁天鹏在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时,希望能在股东、业主、NGO成员和农民等4个有代表性的方向同时进行。
事实上,就在进入南塘村的前几个月,他正在北京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制定议事规则。那是一家致力于治理沙尘暴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为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精英。(本刊2009年10月28日《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对此有详细报道)
SEE协会没有举办南塘那样正儿八经的培训。用袁天鹏的话说,“大佬们认为还不需要做这么个培训,你把规则列出来,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然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议事规则》第二章第4条引起了“大佬”的注意。这条规则写明:会议授权主持人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并执行程序,但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不得参与内容的讨论。
袁天鹏强调,主持人不能发表意见,应该保持中立。万科集团的王石随即发问,“为什么?”
“要有权力制衡,裁判员不能做运动员。”袁天鹏记得,自己当时只解释了几句,王石就表示接受。
当2004年夏天SEE的成员第一次相聚开会时,参会人员合计掌握着两万亿元总资产。他们成立组织的目标是,不能让“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毁灭自身”。
企业家们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南塘村,乡亲们遇到了和他们相同的问题,“为啥主持人就不能发表意见?”
曾任SEE协会秘书长的杨鹏在看过《可操作的民主》后发现,“南塘里面碰到的问题和阿拉善碰到的问题差不多。也就是,当使用这套自由人的平等的联合方式时,企业精英和我们农民们碰到的问题是大同小异的”。
但在南塘村,同样一个问题三言两语可解释不清。
在兴农合作社,理事会的主持人大多是理事长杨云标。在其他大会小会上,主持人则是各种各样的大领导小领导。领导不说话,那还不乱了套?
一个70多岁的老人摆了摆手,用浓重的阜阳口音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搞好搞不好,关键在领导!”
杨云标点了点头,“我们在电视里看开会,主持会议的都是领导。会议开到最后,还邀请领导总结总结,前面讨论一大堆都不重要,领导总结最重要。”
“但我们现在要讲的会议制度,跟这一点恰恰相反。”杨云标话锋一转,“怎么作出决定应该是大家的事,主持人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把会开好。但如果大家讨论秸秆项目,我杨云标有一肚子话要说,那对不起,其他人来做主持人,我就可以发言了。主持人不向着这一方,也不向着那一方,他是中立的。”
看大家还有点“懵”,袁天鹏干脆举了一个远在天边的例子。1787年,美国费城举行制宪会议,会议主席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会议开了100多天,可据说,华盛顿除了主持会议、分配发言权,一共只说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宣布会议开始,最后一句话是宣布会议结束。中间的一句话则是,“我们的会议记录咋保存?”
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袁天鹏的东北口音都飙出来了。
紧接着,他又“乘胜追击”地强调参会者的权利:“我们的规则说了,一旦我得到两分钟的发言机会,这两分钟就是要说完,只要不跑题,我讲错了也得等我讲完,这叫权利!”
他大声说:“所以啊,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牛的词抖给大家,叫做‘程序正义’!”
袁天鹏事后回忆这一段,忍不住笑了出来。一整套讲课内容推下来,按照惯例,他那时必须推出这个大词。在城市里,“程序正义”会触动大家,听众会叫好,甚至有时喊声“有深度”。最起码,眼神里也会“透露出理解的光芒”。
可寇延丁在《可操作的民主》中如实记录了讲者和听众间此刻的互动:
天鹏太兴奋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忍不住把老底儿抖出来了,做了一个托塔李天王似的姿态,还把这个pose定格了一下。也许他觉得“念到这里等一等,可能有掌声”。总之,好嘛,咔,僵在那里了。
弃权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我内心明明反对,却说我弃权,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4月25日的新书研讨会上,NGO人士梁晓燕回忆起,曾经有100多家公益组织走到一起,要组成一个自律联盟。创立那天,80多家组织的代表聚在一起讨论章程,而袁天鹏正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
会议中的分歧巨大,谁也没有退让的意思,“整个会场一片混乱”。梁晓燕甚至一度紧张地认为,“这件事情简直要瘫痪了”。但袁天鹏不断地重申议事规则,不断把与规则不相符的行为打断,不断受到部分参会者的抗议,也不断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内容最终在9个小时后被全部讨论完,结束那一刻,所有人都热烈地鼓掌。
4年前,当准备出发去南塘时,袁天鹏充满信心。他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本以为带些“摸爬滚打的衣服”就够了。睡在南塘的第一晚,蛾子、蚊子“砰砰砰”地飞来撞去,他连袜子都不敢脱。白天,他想来一瓶“冰镇可乐”,却被告知,这里可乐不多,冰镇的就更甭想了。“没有冰镇可乐,也没有空调,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他不由得哀叹。
进了村,杨云标成了助教,将袁天鹏的理论翻译成“乡亲们能听懂的语言”。
培训初始,杨云标设计了一出反映会议场景的小品,几个外地志愿者充当演员。有人戴上了解放帽,有人套上了旧军装,饰演主持人的那位还在耳朵上夹了支圆珠笔。
该次会议主要讨论村里要不要引进秸秆项目。还没议上几句正题,戴着解放帽的就把话茬拉走了,“秸秆是个好东西,还能养牛,我刚办了个养牛场。”穿旧军装的撇着嘴摇了摇头:“养奶牛都赔本了,现在奶粉里出现了什么三聚氰胺。”讨论热火朝天,可他们早就忘了“秸秆项目”的主题,话题甚至延伸到最近“四川橘子生虫”。
这还不算完,几个人的发言又臭又长,如果被别人打断,就会拍着桌子喊,“我再说两句”。他们从技术问题争到“别人媳妇儿”的问题,越说越激动,互相指着鼻子大骂,最后干脆推搡着肩膀要打架。
围在旁边的大妈看得笑弯了腰,大爷脸上的褶皱也笑得更深了。要不是杨云标提醒,他们完全没想起这只不过是自己开会的“情景再现”。
在袁、杨等人的引导下,乡亲们分组讨论,很快就为低质量会议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限制发言次数、发言人不要跑题、举手发言……
这还算是基本问题,当讨论到“弃权”时,乡亲们又闹不懂了。
袁天鹏先举了个例子:9人开会,4个赞成,3个反对,还有两个弃权,这事通过没有?按正常的议事规则说,赞成票多于反对票,理应通过。可有人质疑,9个人里4个赞成,5个反对,“该算没通过”。
很多人觉得,这么说也有道理,“如果他赞成,就不弃权了”。一位大姐站起来,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要是碰上件自己不打算同意的事,“我不同意,但我也不说我不同意,我就不说话!”
这正是杨云标让袁天鹏着重讲弃权票的原因。因为在他主持的会议里,他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赞成的请举手,没人举手;反对的请举手,还是没人举手。“让他赞成,他不想;让他反对,他不敢。”杨云标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就是农村的“老好人”们。
袁天鹏最后说:“弃权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我内心明明反对,却说我弃权,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民主和法治一定需要民众的素质,但这个素质是任何素质的人都可以培养的
距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袁天鹏、寇延丁、杨云标从复杂的规则出发,用最精简的语句写出了“南塘十三条”,学名《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
乡亲们制作了一张漂亮的纸板,将“南塘十三条”贴在上面。不远处的墙上,贴着“八荣八耻”。
但杨云标说,乡亲们很少会专门站在那里仔细地阅读一下“十三条”。甚至其中的很多规定,如今都在会议中慢慢消失了。
合作社理事会的会议里,杨云标仍旧担任主持人,但他既参与辩论,也参与表决。可谁也不“迷信这个领导”。如果普通理事不发言,那才会被看做“不正常”。
之前,合作社决定买一辆面包车。这么大一笔四五万元的投入可马虎不得,理事们个个较真儿。参会者抛出五花八门的问题:谁来管车?谁来开车?给不给司机工资?司机把车开到家里,公车私用怎么办?一位老人更是连杨云标没想到的“危险”都摆了出来:要是看车人丢了车,损失由看车人承担,还是合作社承担?
大家自动按照议事规则辩论,每人发言两分钟,共计两轮。最终得出一个与最初的“动议”完全不同的方案:一位正打算买车的社员可以享受合作社的无息贷款,条件是在还清贷款前要免费借合作社使用。
公共管理的一大难题就此解决。规则有用就行。谁会去想,这几经修改的方案在“萝卜规则”里的学名是“修正案”?
“议事规则并不是从技术上让我们获得了什么,而是给了我们对平等和民主的意识、观念。”杨云标如今这样认为。
有网站评选“公民阅读4月好书”,《可操作的民主》排名首位。微博里有人评论称,这本书就是“民主素质论”最有力的反证。因为它证明了,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也可以掌握复杂的议事规则,他们不再满足于鼓掌通过或直接投票——没有讨论不能投票,直接投票违反议事规则的精髓,相当于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但当袁天鹏被问起,他怎么看待“民主素质论”时,这位规则专家的回答却有点让人意外。“民主和法治一定需要民众的素质。”他毫不犹豫地说,“但这个素质是任何素质的人都可以培养的。”
与很多人一样,他曾经也认为,民主的生活就意味着“尊重我自己的权利”。
“人们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尊重别人的权利吗?”他反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兴奋地买了汽车,准备痛快地兜风。可刚上路就发现,这里有太多规则需要遵守。超速自然要吃罚单;灯火通明的夜晚忘记开大灯,也要被罚款;有的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就在各个方向都贴一张“停止标志”,每辆车在这里都得停一下,看到没车才可以继续行进。
“半夜3点钟,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也得停。”结果,尽管夜深人静,却“连兜风都兜不动”。
当从马路回到会场,“尊重他人的权利”就意味着必须在各种不同主张的人中寻求平衡,因为 “你不能说了算”。
最近也最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可操作的民主》新书研讨会上,主持人刘苏里对两位发言教授的观点“都有意见”,但为了遵守主持人的中立,他得把意见闷在心里,“我现在不能说”。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屡次举手示意,但发言请求也被驳回,“说好按顺序来,对不起”。发言时间更被严格控制,就连会议的3位主角平均也没说到5分钟。
“有几个人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爽的?”袁天鹏问。他认为,议事规则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人们去理解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
刘苏里后来在谈到这本书时认为,议事规则就是培养公民、民主意识的一个切入点,“很多会议的召开无非是为了保证程序的合法性。每个人都知道那是‘皇帝的新衣’,但每个人还是都要去‘裸’。可罗伯特议事规则自然会挑战这些潜规则,它是一种工具,我们通过使用它而培育一种意识。”
“如果你要割肉,这是一把快刀。”刘苏里说。
大家看到好的东西,就去推一推,我推议事规则,你推预算公开
可在研讨会上,并非只有赞同的声音。清华大学教授李楯就直言:“今天对不起,我要说点问题。”
“中国人是不会开会的,这个体制决定了,决策在会议之外。”这位教授以清华大学法学院为例,这本应是最熟悉规则的机构,结果却“最不会开会”,“前面东拉西扯,快到中午了才有人说,‘快吃饭了,咱们赶快把问题解决一下’。”
“如果没有整体外部条件,是很难从这(运用议事规则开会)做好的。”他认为。
在研讨会上,袁天鹏并没有获得充足的时间来回应这个问题。但会下,他承认,自己也一直在思考,“真正解决问题不开会,大问题开小会,小问题开大会”,这就是当下的现实图景。
但在那些可以集体决策的会议中,人们是不是就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呢?在袁天鹏看来,现状是,会议一旦出现分歧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将会议看做“没有效率,破坏团结,一塌糊涂的东西”。
他认为,议事规则作为一个工具,既能解决分歧,又能避免把解决过程误判为“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大家都建立了按程序来纠正错误的意识。今天可以纠正跑题,将来就能纠正更为严重的越轨行为。”
“我并不是简单粗暴地认为,议事规则,上!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袁天鹏笑着一挥手,“但我认为,不要再去讨论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要讨论先解决什么。大家看到好的东西,就去推一推。我推议事规则,你推预算公开,他推法官专业化……没有人知道哪个能最先取得进展。”
从2008年至今,“下乡记”的3个主角不止一次地被问到,他们在南塘村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
“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很忐忑不安地说没有什么成果,现在,也许我们会很平静地说就是没有什么成果。”寇延丁说。
表面上看,南塘一切如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最近,合作社打算给社里的每位老人发20只土鸡苗,将来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以贴补他们的生活。会议室里,7位理事和一位刚刚从贵州来到南塘的实习生围坐在一起,就是否通过这一方案进行讨论。
讨论有条不紊地进行,只是那位新来的年轻人每到发言时,就会不自觉地跑题。他在老家养过土鸡,因此,发言总是偏离方案的可行性,而谈论起养鸡的各种注意事项。
就像瓷器店里突然闯进了一头公牛,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议事规则培训的人都感到,新来者打破了规则,也打破了他们几年来开会的习惯。毫无疑问,“跑题”必须被制止。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南塘早已变了。”杨云标笑着说。
本报记者 赵涵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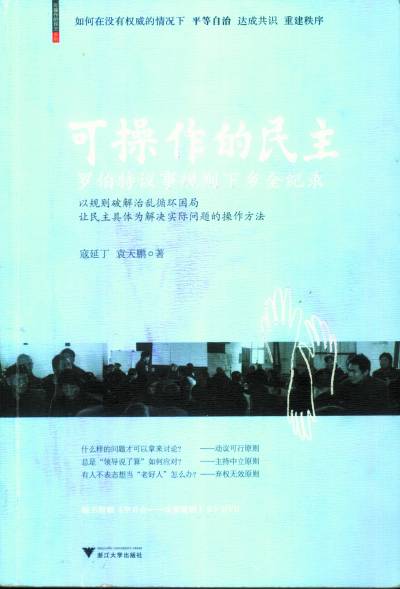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