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所言之“观念”,为国人的政治观念——她发现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她认为这实际是国人的“观念”转变了,变得有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了。
“观念”的力量不可小觑。她相信,“观念的水位”总有一天能积蓄到让船有反应。
刘瑜新作《观念的水位》之五部分、74篇文章中,第一、二部分的《观念·此处》和《观念·彼处》无疑是其重点。“此处”、“彼处”,十分易解,我们、他们,中国、外国。正如作者刘瑜在“自序”中言:“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间隔还是连贯地阅读当然不一样。我想差异便体现在她所说的“重量和清晰度”了。
《观念·此处》之《没来的请举手》中的那个问题——“你知道谁谁谁吗?”简直可说是一个最具“问倒力”的问题。比如,某人正在慷慨激昂、陶醉自得之时,你冷不丁地问他(她)一下,普遍的回答肯定是不知道。而“不知道”所指向的,即是那个被遮蔽世界的存在,也就是刘瑜所言的“没来的人”。她这样说:“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如果想知道那些不知道的,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她当然清楚这个告诫的微效。正如她在《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里说:“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肉,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我从这种“理性的无知”中,看到了与俄罗斯学者雷达里赫所言的“积极的不自由”相近的异曲同工:“许多人情愿不去了解极权本质的一切真相,不是害怕特务,而是害怕了解后带来的后果”。
《他也可以是我》中的“亲自倒霉”之说,可谓生动至极。文章通过分析那些要经过“亲自倒霉”才“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的人,讲解了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即:“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仅是‘我’的自由,而且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但,即便她从那些“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个体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的人的“愤愤不平”里,找到了隐隐乐观的理由,这种“我”即是“你”与“他”的常识,也还是亟待成为常识。
《观念的水位》一文是该书其中的一篇,被用作了书名。“观念的水位”几个字的确好。可是,究竟“观念”为何物?更何况还可以以标尺测之?简言之,我们平日里与人交流,心有戚戚焉或者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是基于“观念”是什么?阅文读书,心领神会、心悦诚服或者蹙眉憎笑、反感骇异,不是基于“观念”是什么?更有世间种种——网上谈不拢,招致互相拍砖、谩骂,国与国谈不拢,招致隔膜、冷战甚至引发战争,不是基于“观念”是什么?世间真要有一把观念的标尺倒好了,逢人遇事拿出来一测,不在一个水位,免谈!省去多少麻烦。我以为,刘瑜是文所言之“观念”,为国人的政治观念——她看到它们在“水涨船高”,因此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她发现“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她认为这实际是国人的“观念”转变了,变得有“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了。而“观念”的力量不可小觑,因为,“变革原因往往是意识形态静悄悄的解构与重构”。她相信,“观念的水位”总有那么一天能积蓄到让船有反应。
刘瑜研究问题不装。套用该书《贵族范儿》中她引用作家石康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洛克是根本不需要智力的……”,我以为说“看刘瑜是根本不需要智力的”也是相当恰当的。在该文中她写道:“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简单即深刻,不也正是她为人为文的写照吗?当然,正如她所说,“在陡峭的知识高峰面前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确实有些难度”。但这也正是该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如《宪法这只兔子》一文,开头她便写道:“在所有的政治词汇中,有一个大约是人见人爱的:宪政。当今时代,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政治派系,对‘依法治国’恐怕都少有异议。当然宪政里的法,指的是宪法。”她在“自序”中这样说:“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上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
《观念·彼处》中,其“彼”,除了英美,还有中东欧、拉美、非洲、亚洲等。无论是俄罗斯的“不自由的民主”,中欧一些国家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还是伊朗追求自由民主的“螺旋形道路”、委内瑞拉的瘸腿民主、洪都拉斯的宪政危机、在拉美破产的“新自由主义”,刘瑜写来不乱。她像是手握化繁为简的秘籍,越是复杂错综的乱局,她越能纵横捭阖,条分缕析。
《观念的水位》中处处使用了数据这把利器。如《素什么质》一文中,她用数据说明,如果“素质”即等于“文化水平”,那么中国人的“素质”其实并不低——“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的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于是她说,“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刘瑜写文,擅用数据。但有一项数据她无法统计:她的书、她的文、她所传递的观念,帮助多少人提升了“观念的水位”?
白英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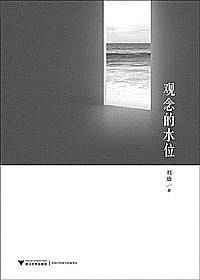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