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贵”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在上周之前的清华校园,薛其坤还不是一个多么引人注意的角色。不止一个见过他的人表示,几乎听不懂这位中科院院士与别人随口说起的科研内容。
事实上,他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4月9日,由这位教授领导,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与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组成的团队宣布,他们从实验中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他们的论文,3月15日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科学》上。
对普通人而言,“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并不仅是一个让人云里雾里的科学名词,它还意味着某种科幻小说般的未来生活:若这项发现能投入应用,超级计算机将有可能成为iPad大小的掌上笔记本,智能手机内存也许会超过目前最先进产品的上千倍,除了超长待机时间,还将拥有当代人无法想象的快速。
这一发现甚至令年过九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都激动了:“这是从中国的实验室里头,第一次做出并发表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那一时刻,我们看到我们深刻的信念,在大自然里果然是被实现了”
普通人几乎没人知道什么叫“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但1879年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的“霍尔效应”,实际上已经被应用在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测量磁场,测量运动事故,也可以生产新的器件,比如汽车的里程表、速度表,以及点火系统。
这一次,薛其坤团队的最新发现,在科学家眼中,更是一个极为美妙的现象。
在摆满仪器设备的实验室,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王亚愚试图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外界解释他们的研究。他手持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播放着动画:一个透明的长方体物件内,许多玫红色小颗粒正在横冲直撞。
“如果这是一个一般的金属材料或者半导体材料,那里面的电子运动是非常无序的。它们杂乱无章,互相碰撞。这就引起电子器件的速度降低,而且会使能耗增大。”
虽然肉眼看不到这些到处乱跑的电子,但谁都会在生活中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譬如,尽管有风扇“呼啦呼啦”地吹,工作多时的笔记本电脑却还是热得烫手,反应缓慢得像老牛爬坡。
但这些粒子却是可以被科学家们“管”起来,顺着一定规律在材料内老老实实排着队跑步的。
“如果我们在材料上加一个强磁场,非常强的磁场,电子运动就变得有规律了——它们在材料的两端,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样,这么反向运动,这时候,电子运动速度就变快了。”王亚愚教授解释说。
动画中,玫红色小颗粒乖乖地排在材料两边,一边的队伍向前跑,对面的队伍则向后跑,就像公路上遵守交通规则的往来车辆,在不同的车道里畅通无阻。
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量子霍尔效应被德国物理学家冯·克利青在研究极低温度和强磁场中的半导体时偶然发现。这一成果让他获得了198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只是,要让肉眼都看不到的电子像动画中那样规律地运动,需要极强的磁场:至少得是一个一人高,冰箱一般大小的设备。运作起来非常麻烦,而且极其昂贵。
显然,这不是一件能走出实验室的“降温提速设备”。
这也就是为什么薛其坤的团队在实验中观测到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这么重要、又是这么优美了:在零磁场中,材料的反常霍尔电阻达到量子电阻的数值,并形成一个平台,也就是说,在微观世界中,那些原本乱冲乱撞的电子们正循着“高速公路”畅通有序地运动着。这一次,没有强大的磁场。
这一场面证实了科学界等待多年的预言。
“这是量子霍尔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一位美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撰文称,“不需要外磁场的量子霍尔态的实验观测,使人们终于能够完整地研究量子霍尔效应的三重奏了”。
在得知这一结果的时刻,薛其坤的合作者,曾经预言过自旋量子霍尔效应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想起了老师杨振宁曾对他们说过的话:任何科学发现,都早已存在于自然界中。
“在发现的那一时刻,我们看到我们深刻的信念,在大自然里果然是被实现了,这种感受是科学家最最大的一种回报。”
那是2012年的10月12日,距离霍尔最初发现这种电磁效应已130年有余,距离薛其坤的团队开始实验,也已整整4年。
“吃饭,睡觉,做研究”
在同行中,已经有300多篇SCI论文发表的材料物理学家薛其坤以勤奋刻苦著称。他有一个“比‘院士’更响亮的名号”,叫“7-11”:早上7点进实验室工作,一直干到晚上11点。在进行实验的4年中,他的团队先后尝试了1000多个拓扑绝缘体样品。
磁性拓扑绝缘体,是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理想系统。要实现量子反常效应,对材料的要求非常高:这种材料必须具有拓扑特性,具有长程铁磁序,体内则必须是绝缘态。按科学家的解释,就好比要求一个人具有刘翔的速度、姚明的高度和郭晶晶的灵巧。
在薛其坤的指导下,研究者们用于实验的拓扑绝缘体样品是以“原子”为单位的:在100万个原子中,只能有一个杂质原子。这1000多个不到小拇指指甲盖大小的特殊实验材料,都需要在超真空环境中慢慢长出来。它们的厚度得是5纳米,高1纳米或是低1纳米都不行。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团队成员,每天都通过电话和邮件交流实验结果,隔两三周就充分讨论实验的所有细节。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负责测量反常霍尔效应的王亚愚教授形容,那时他们都“不大好意思见薛老师”。
但团队领导者薛其坤耐得住性子。他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小时候,母亲得到了一条珍贵的牛肉,舍不得吃,一定要等着出外上学的孩子回家,才把已经风干的牛肉慢慢在水里浸开,包了饺子吃。
很多年以后,这个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农村孩子还记得,年少时第一次进县城,如何被那里的繁华震惊。他对家乡记者描述说,那心情就像临沂人的一句笑谈,“蒙阴就像是北京一样,是个大地方”。
当时这少年心中的“最高理想”,就是在那个蒙阴县城中“找个工作,娶个媳妇”。这理想人生至少实现了一半,薛其坤后来确实娶到了一个蒙阴媳妇。
另一半人生也许有些超出他最初预想的轨道:在日本和美国留学,35岁晋级教授,41岁成为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是个科学家……只想有事干,踏踏实实做点事。”
在证实“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成果发布后,有网友在微博上对着“薛其坤”这名字大发感慨:当年这个人去他们学校讲座,没人听,他还被拉去充数——近几年,薛其坤曾在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作过以“个人成长的体会”为内容的报告。
他人看来几乎是一帆风顺的履历,在当事人心中则另有滋味:大学毕业后一次次想考研,第一次考哈尔滨工业大学,高等数学只考了39分,落榜;两年后报中科院物理所,物理考了39分,又落榜。
第三年,他终于考上了中科院的物理所。但之后的几年里,这个大龄研究生“整天处在维修仪器的苦恼状态中”。当年,物理所的设备不灵光,常常做不了实验。就算一次次做实验,但得到的数据也总是对不上号。
直到全无日语基础的他被送往日本东北大学联合培养,生活才逐渐顺利了起来。正是在日本导师樱井利夫的要求下,他养成了“7-11”的工作习惯。随后他被樱井先生推荐至美国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D.E.Aspnes门下做博士后,这位老先生也极有个性,每次实验室外出聚餐,年过六旬的他总会骑着摩托车,带上一个学生,顺着高速公路一路风驰电掣而去。
如今,当薛其坤成为整个研究团队的中心人物后,他也极其擅长发现每一个人的优点,为整个团队鼓劲儿。
留学经历还磨砺了薛其坤“流利的山东口音英语”:“俺没啥子能耐,别人上台不敢讲,俺胆子大,敢讲!”
与薛其坤有接触的人众口一词地描述说,这位科学家风趣幽默,精力充沛。他喜欢踢足球,爱看武侠小说,早年生活中令人愉快的消遣是在楼道里打麻将。而他的研究生们则提到,这位导师每次出差后回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实验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哪怕已经是晚上12点。
在就任清华教授之后的一次采访中,他对记者介绍说,自己的团队来自五湖四海,有着共同的志向。谁知对方问他:您的团队成员有什么共同爱好吗?
这位团队老大思索了片刻之后说:吃饭、睡觉、做研究。
上周,在“证实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布会上,杨振宁为这群中国学者的新发现补充说,有一点值得人们去思考: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全世界很多实验室都在钻研,为什么唯有清华大学与物理所的合作成功了?“我想这与中国整个科研体系的体制,跟中国传统的人文关系都有非常密切的直接关系。”
“这可能是我们两个人人生当中最最喜悦的那一天”
2012年10月12日晚上10点35分,薛其坤接到团队成员、博士生常翠祖的一条短信:“薛老师,量子化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等待详细测量。”
实验测量到的数据是一条漂亮的曲线,与理想情况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行为完美地吻合。
团队成员观测到的现象,是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下对拓扑绝缘体薄膜进行精密测量后获得的。也就是说,目前要谈论这种现象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还为时过早。毕竟,室温要比实验温度高很多,《科学》杂志上一篇文章也指出,实验材料在其他方面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但对为之付出多年努力的科学家们而言,这一结果已经足够令人惊喜。“这可能是我们两个人人生当中最最喜悦的那一天。”张首晟后来在发布会上说。在座的杨振宁听着这个学生的报告,也想起了1956年12月的某一天,吴健雄在电话中告诉他,她发现了宇称是不守恒的。
“我认为是从中国实验室里头一次,做出来了,并发表出来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这也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喜事。”他一遍遍地对着不同的媒体说。
这篇论文发表后,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想起来,在从前的一次“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上,曾有学生对薛院士提问:“您是否有志为中国赢得诺贝尔奖?”
“没有想过。”静静地想了一会后,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认为一个不想得诺奖的科学家不是好科学家。”学生不依不饶。
但薛其坤就是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在做科研时,没想过这个问题”。
本报记者 黄昉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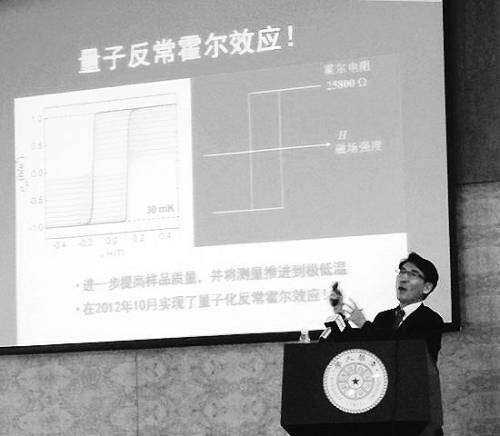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