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主席威廉·马丁,曾将中央银行的角色形象地描述为“在宴会开始时收走调酒杯”,然而,自2008年以来,从全球范围看,这场经济增长的“宴会”迟迟未始,于是,各国中央银行依然活跃在促进增长的“第一线”。自5月2日以来,随着欧盟、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越南等相继宣布降息,中央银行继续加码经济增长,但分析来看,本次全球降息潮的效果并不一定乐观。
首先,发达经济体后续进一步降息操作的空间是很小的。要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需要连续性的政策操作,而连续性政策操作的一个前提,是具备较大的操作空间,因为利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就难以再降。以我国为例,现行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意味着宽松操作的空间显著,货币政策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诸如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性质也类似。但是,发达经济体却有着显著区别。日本目前利率水平已接近于零,而欧元区本次降息操作后,基准利率已经降至欧元区历史最低水平的0.5%,英国目前的基准利率也是0.5%,美联储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也早已降至0.25%。这种状况决定了当前发达经济体进一步降低利率的可能性很小,不会形成持续的操作。
其次,发达经济体的痼疾可能并非单纯的降息操作所能解决。经济增长需要一个有利的货币环境,但一个有利的货币环境却不必然实现增长。为摆脱经济疲弱局面,欧盟、日本和美国都不遗余力地执行量化宽松政策,降息操作也多次出现。事实上,如果不是日本当前已经没有降息空间(目前日本隔夜拆借目标利率为0.1%),其降息操作的动能应该是最充足、最激进的,本次降息潮应有日本的加入。次贷危机后,发达经济体虽经持续刺激却仍陷入低迷(美国略好,日本和欧盟表现不佳),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在这场“经济宴会”上,始终缺席了两个关键角色:健康的财政状况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受制于巨额债务负担,欧盟和日本等难以通过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缺乏新的增长点,使经济始终缺乏持续动力。这两方面,都是单纯的利率调整难以解决的。虽然降息操作所引致的通胀上行,一定程度上对降低债务负担有积极作用,但却是以未来通胀治理成本的上升为代价的。这也就决定了,降息操作实现的增长效果可能并不会显著。
第三,公众预期不强可能显著降低降息的增长效果。理论上,宽松货币操作对经济增长能产生积极影响,这是相机抉择政策操作的基础。事实上,宽松货币政策要对经济增长起到作用,必须确保资金从金融体系流入到实体经济中去。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宽松和降息操作,虽然能决定金融体系资金的多寡,却不能决定资金从金融体系流向实体经济。决定实体经济投资需求的,还是各类主体(居民和企业)对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如果人们对未来增长前景不乐观,有利的货币环境也未必能改变各类主体的行为,也即出现信贷市场失灵。在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就曾出现这种状况:即便是利率极低甚至为零,私营部门也没有意愿借贷。从当前欧盟和日本经济运行特征来看,无论是投资信心指数还是消费者信心指数,都明显不足,这也印证了货币宽松效果未必就好。
第四,新兴市场的降息操作更包含着一定的被动成分。全球性的量化宽松,可能并未让发达经济体享受到显著的增长,却使得新兴经济体遭遇持续的通胀。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由于当前通胀率较低(3月,美国、欧盟和日本CPI月度同比分别为1.5%、1.9%和-0.9%),通胀风险较低,中央银行在促增长和防通胀方面容易权衡。然而,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推升了大宗商品价格,使得新兴市场面临巨大的资本流入,加剧了本国的通胀压力。主要新兴市场中,印度的通胀水平长期处于6%以上,巴西2012年通胀率也高达5.84%。发达经济体持续地降息,将使新兴市场资本流入的压力进一步增加,造成本国货币被动投放,引致国内进一步通胀压力,国内的跟进降息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这种流入压力,而且也对新兴市场表现一般的经济运行起到积极作用。由此一来,新兴经济体就顺势迎合了发达市场的降息操作,这也决定了政策效果未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
从2008年开始,各国中央银行都在为重启经济增长的“盛宴”而努力着,一次次的宽松、一轮轮的降息。可以预见的是,即便各国在政策发力方面从未间断,即便美国等经济增长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当前距离经济增长“宴会”开始、中央银行“功德圆满”地退出,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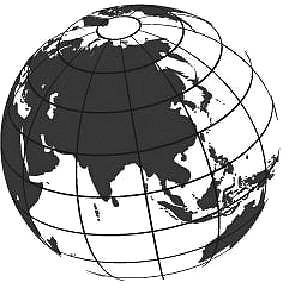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