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广州还有些湿冷。我跟一群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登上了白云机场的飞机。刚刚坐下,一位年轻的红衣女士拉着行李箱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她对着电话说,马上就下飞机。
我心里突然惊慌起来。高中生、飞机、旅行、年轻的女士、不祥的预感,所有的一切,仿佛把我拉进了《死神来了》开始的场景:高中生艾利克斯与同学登机前往巴黎,起飞前,他突然预感飞机将会在空中爆炸——结果被他不幸言中。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2009年,我正在武汉读大四。看了开头,我没有继续看下去,只是后来听朋友兴高采烈地讲起里面的故事,以及那种无可逃避的宿命感。电影里短短几分钟,已经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打开了我心中的潘多拉魔盒,释放的全都是对死亡的恐惧。
坐在车上,我开始怕另一辆车从侧面撞过来;走在路上,想象着天上掉下的大石头把我砸扁;睡在床上,我想着万一深夜失火如何逃生;看书学习时,怕突然猝死;吃饭时……我从没有这么强烈地畏惧死亡,生怕死神像夺走艾利克斯和他的朋友们的性命一样,也在不经意间给我的生命画上句点。
之前的我好像没有这么怕死。小时候看了太多的抗战剧和武侠片,里面很多“不怕死”的宣言赐予了我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很多次和小伙伴们爬到高墙上,坐在深井边,相互试探着问:“敢不敢跳下去?”答案从来都是“敢”一个字,虽然从来没跳过。
小时候不怕,因为不懂。而长大后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儿时的无知带来的无畏,在死神的长柄镰刀前立即土崩瓦解了。不仅如此,那时的无知,带来的是恐惧。
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摆脱那种宿命感和压迫感。它像一把刀,抵在我的背后,不知什么时候会刺透我的胸膛。也正是因为这把刀,让我不能停下脚步,只能一直向前走。
从武汉来北京之后,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试着像凯勒一样,把生命中未来的三天当作最最宝贵的三天,乃至最后的三天来规划和准备。于是,校园里多了这样一个身影:他背着十几本书和三盒方便面,在教学楼里一待就是一天;他一大早去图书馆排队,到晚上十点半闭馆才出来;他开始了自己的旅行计划,想着毕业前走遍全中国。
对自我的沉浸,让我在另一种紧张里找到一种对死神的解脱。虽然有时也会冒出奇奇怪怪的想法,但我知道内心那只老虎已经平静了很多。
“第二天能醒来,对我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很早以前在广州采访一位校友时,他说的话。后来,我才体会到他的意思。
有时候我问自己,面对子虚乌有的死神,到底是怕什么:怕死得难堪?怕死得痛苦?还是怕轮回?怕失去?我也说不清其中的理由。就像《死神来了》突然带给我的阴影,也是找不出原因的,如同突然被施了魔咒。
如果非要给个理由,那可能是觉得活着实在太美好了吧。就这样,我一边怕着,一边笑着;一边体味着死亡带给我的恐惧,一边感受着生活赐予我的快乐。
直到有一天,那是2011年7月的一个凌晨。写完老师布置的论文已经到了深夜,没有睡意。我打开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三傻大闹宝莱坞》,印度片,在电脑里已经存放了很久。
我觉得自己像极了电影里面的拉加。他害怕未来,手上戴着代表自己信仰的戒指,他为考试戴,为姐姐嫁妆戴,为工作戴……戒指比手指头还多。“你这么害怕明天,怎么能过好今天?”主人公兰彻责骂他。
拉加后来经历一次自杀,摔断了16根肋骨和两条腿,摔成了植物人。在好友兰彻和法汉的帮助下,才脱离了植物人的状态。获得重生的他,面对着自己最好的朋友,轻轻地摘下了手上的戒指,扔进了旁边的马桶里。
那一刻,面对着这个画面,我泪流满面。我跑到阳台上,锁上门,蹲在角落里,痛哭起来。我突然明白,那个一直束缚我的戒指——对死亡的恐惧——可以扔掉,也应该扔掉了。
两年来压抑在心里的东西终于被释放出来。开始得是这么突然,结束得也是这么偶然。渐渐地,天亮了起来,太阳照在我的身上,那么明亮,但是我模糊的双眼已经看不清。
飞机从白云机场起飞了。我从一开始的惊慌中慢慢走了出来,心里默念着伊壁鸠鲁的那句话: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只要我们还在,死亡就不在。
宣金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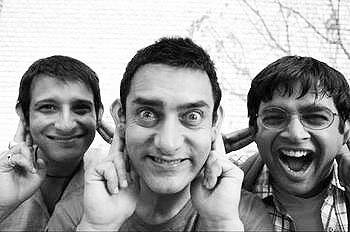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