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作家路遥去世的第20个年头。
当时,我的一个媒体朋友,曾专门撰稿《路遥:身后20年》,来纪念这位当代作家。
读后,我曾动念写一下路遥——这位曾影响自己整个少年时代的作家。一念之后,再动笔,已是半年后。
迟迟未动笔的原因很多,最好的借口是,越看重,越无从落笔。因为每次看到“路遥”的名字,我总会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路遥的小说。
记得那是1997年,我正读高二。下午的上课铃声响过,老师照例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我偷偷捧着一本小书读得津津有味。
上课看课外书,是违规的,轻则没收读物,重则通报批评。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正襟端坐,书放大腿,时而瞅下老师,时而翻动书页。
每逢老师眼光瞥来,我身体前倾,将书推入桌子下面。这本像魔法石一样吸引我的小书,就是路遥的《人生》。
当时,小说出版已经有15年了,但是,在家乡县城的中学内,这仍是最受欢迎的书。
路遥的《人生》,我至今只读过一遍,就是在这种战战兢兢,又欲罢不能的状态下读完的。清晰记得,书中的人物叫做高加林和巧珍。读书时,一度因为高加林的初恋表白而欣喜万分,因为他的挫折而胸闷气憋。
小说末尾,在事业和爱情方面经过一番坐山车式的遭遇后,高加林落魄地跨过大马河,回到高家村,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
那个场景,当时让我如遭雷击,一时间感觉自己就是高加林,窒息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想想,之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读完小说后,却发现,人生原来并不那么美好。
这是路遥给我的最初印象,但不是最终的印象。真正的影响,是在阅读了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之后。
1999年,我考入大学后,第一时间在学校门口的地摊买了《平凡的世界》,盗版。
不是支持盗版事业,实在是路遥的书太抢手,似乎没见在图书馆呆过。正版又买不起,逼着买盗版书。
从午饭后开始读《平凡的世界》,整个下午,整个晚上,不想说话,不想吃饭,不想出门,一口气将百万字的小说读完。
清晰记得,那时候流了三次泪。流泪最多的一次,是田晓霞死了。
当孙少平收拾好行装,前去赴和田晓霞的约会时,突然在报纸上看到田晓霞因救人被洪水冲走的新闻,确认田晓霞去世后,他依然赶赴一个人的约会。
路遥在这一章铺垫的太丰富了。初恋中的文学青年,对心上人的渴盼,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切尽在眼前,突然,心上人去世了。
转弯太快,猝不及防,情感一下子翻了几个跟头,翻得六荤五素,随着眼泪痛痛快快涌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一书时,在写到田晓霞去世后,也曾经痛哭流涕,喃喃自语:“田晓霞死了,田晓霞死了!”
并且,路遥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哀伤之情,打电话把远在外地的弟弟叫到跟前,只是告诉他这样一件事情:“田晓霞死了,田晓霞死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在和一些朋友交流时,我才发现,很多年轻人,特别是70后和80后,都会被《平凡的世界》打动。特别是有农村生活背景的青年,很容易入戏,身临其境。因为孙少平身上,有着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不甘平庸,希望摆脱贫困的奋斗与苦痛。
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近乎残酷的青春,近乎悲壮的打拼。
路遥就那样自然而然地进入我的生活,让我在“平凡的世界”里,品味“人生”,想象“路遥”。
然而,路遥似乎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对路遥的评价,似乎一直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简单地说,就是“文学的评价”和“读者的评价”。
有两个排名榜,盘点30年(1979年—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一个是“邀约12位知名评论家,从纯粹的文学标准出发,投票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10部作品并简述理由”,一个是“在评论家提名的作品范围内邀请网友投票选出最好的中国长篇小说”。
在“纯粹的文学标准”下,路遥榜上无名,而在网友的排名榜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得最多网友的选择,高居榜首。
我一直在想,假如路遥在世,未必会感到遗憾,因为他更在意读者的评价。
在个人成长中,我一直视路遥为情感上的“精神陪练”,视殷海光为理性上的“思想陪练”。
因为,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不是名牌学府,不是名师指点,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基于生存的“陪练”。
事实上,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作家和作品,那种“影响”,直抵生存深处的卑微的灵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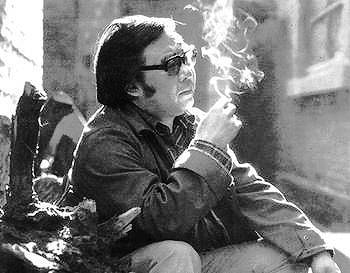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