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为主任研究员,科学家赵朝义的工作更像个裁缝。只不过,他量体裁衣的对象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国人。
犯罪现场留下的脚印是不是一个成年男子的?地铁扶手距离地面多高才合适?交通指示牌用哪种颜色最醒目?儿童免票身高为什么是1.2米以下?这些生活中毫不起眼的细节,都需要人体基础数据来支撑。
作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类工效学实验室主任,“裁缝”赵朝义需要测量的内容,也不只是肩宽、臂长或腰围那么简单,而是包括体型、力量、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项人体参数。
如今,新一轮中国成年人工效学基础数据调查正式启动。5年后,赵朝义和他的团队将用数据描绘出中国人的“新版型”。“类似‘人口普查’,但是我们的关注点不是中国人有多少,而是中国人长什么样,认知操作有怎样的习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基础标准化研究所所长罗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距离上一次类似的数据采集,已经时隔27年。赵朝义介绍,中国人早就“长变样了”,但相关行业应用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
“在中国,工效学受到的重视只能说刚刚开始。”在位于北京昌平区的标准院实验基地,赵朝义一边踱过走廊,一边皱着眉头说。
只有用中国人的体型数据才能设计和生产出适合中国人的产品
这座建筑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更像一座“现代人类生活博物馆”——空调机箱在走廊里一字排开,十几台洗衣机在玻璃幕墙后等待实验;桌面上堆放着十几种差别细微的小抽屉,旁边是花花绿绿的遥控器。一位受试者正在体验几只照明灯光颜色、亮度各异的冰箱模型。一辆红色小汽车则和它面前的环形屏幕一起,构成虚拟现实仿真场景。
世界上最顶尖的工效学实验设备就和这些日常所用的家电错落摆放着,用赵朝义的话说,他的研究“不是让人学会使用机器,而是根据人的习惯制造机器”,所涉及的行业包括汽车、服装、家用电器、运动器材、航空航天等。
人类工效学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学科,它将人、机器和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
但直到1988年,中国才有了第一个“成年人尺寸数据库”。上世纪90年代赵朝义读工学研究生时,全国只有一个工效学博士点,一些高校在其他学科下设置了相关课程,教材和教师都很稀缺。
“那时候,中国半数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都把原因归为人的注意力不集中,或操作机器不当。”赵朝义回忆。但几乎没人从工效学的角度质疑,有没有可能是机器的设计不符合人的操作习惯?
数年来,赵朝义向有关部门申请课题,常常被拒绝立项,理由是“连技术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舒适性”。来自企业的调研结果更加令他失望。一位国内汽车企业的工程师告诉他,直接把国外的东西拿过来改改就行,“什么座椅比较舒适?嗨!我们到座椅厂定做最贵的,肯定舒适!”
“要么照抄国外,要么凭经验,都没有科学依据。”赵朝义指出。另一位副研究员冉令华则给出了亲身经历:当她驾驶自家的小轿车时,方向盘的上缘刚好挡住仪表盘,而她调整座位——脚踏板又不合适了。
就连赵朝义进行科学研究,需要一套以中国人骨骼、肌肉为模板的“碰撞假人”,都只能作罢。眼下,“假人”都是美国进口,“人高马大”,完全不符合实验要求。
“技术可以引进,但数据无法引进。”这位研究员表示,“只有用中国人的体型数据才能设计和生产出适合中国人的产品。”
按照新一轮的人类工效学参数调查计划,每位被采集对象将提供200多项数据,包括160多项体型参数,以及力学、视觉、听觉和触觉参数,最终获得的数据将会达到400多万个。
最终,一部分数据将被作为国家标准进行发布。另一些数据将被企业使用,比如制鞋厂将了解30岁左右中国男性的足部尺寸,女士内衣制造商也能为胸罩的肩带和罩杯的设计找到力学和形态依据。
这些数据的应用范围远超过你我的想象。比如,刑侦人员根据犯罪现场的脚印,能够更准确推断嫌犯的身高。
中国人块头变大了,力量却减弱了
若想准确描绘“新版型”,科学家“裁缝”依靠的可不只是卷尺。主力军是一台“三维人体扫描仪”,足部、头颈部和手部扫描仪也将一同“上阵”。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维人体扫描仪。”冉令华就像介绍一位身份显赫的宾客。她打开电脑,经过简单的几步操作,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浅绿色的男性三维全身像。她按动键盘上的方向键,立体人像便在屏幕上徐徐转动。
这个人像就是由三维人体扫描仪制作而成。受试者只需站在其中,十几秒钟就能完成一种姿态的尺寸测量。参数将以三维成像的方式被输入电脑,人像身上会有标记,只要用鼠标点击计算,就能立即看到超过160项的指标。
不远处的墙上贴着一幅“马丁测量尺”的示意图。那是1928年德国人类学家鲁道夫·马丁发明的一套人体测量仪器和方法。1986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老先生”们就手拿这套尺子,集全院之力,用两年时间“丈量”出第一个“中国人体尺寸数据库”。
冉令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那时我们无法想象,今天的一项人体测量只需几十秒钟的时间。”
但直到几年前,这个数据库没有进行过任何更新。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大多5到10年就补充修订一次人类工效学基础数据。日本每年都会投入数亿日元,对国民的体形分布特征、活动能力、视听能力、触觉特征以及认知能力等进行持续调查研究,其成果会立即被用于产业界,“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工业产品的竞争力”。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业工程学教授史蒂夫·拉凡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近年来美国两次大规模人体测量先后于1998-2000及1999-2002期间进行。尽管美国人的体型变化不大,但在这位工效学专家看来,这些数据也已经有了局限性。
“更新数据是非常必要的。”这位美国人因工程与工效学协会(HFES)会员说,“这样企业和工业产品设计者才能充分考虑用户的需求。”
2009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北京、上海等4个城市进行了一次《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抽样测量试点调查》。这次调查采集了3000多份中国成年人三维人体尺寸,赵朝义发现,以往的数据已经不能反映中国人如今的体型。比如,“中国人胖了”,尤其是35岁以上的人群。
作为在标准院工效领域研究近10年的资深专家,冉令华也从中发现了变化,比如中国人虽然块头变大了,力量却减弱了,这意味着脑力劳动相比体力劳动的比重迅速上升。
新一轮人体工效学的“人口普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的。“这项工程确实太大了。”赵朝义说起项目,显得很兴奋。中国地域广阔,数据采集计划将分为东北华北区、中西部区、云贵川区等六个大区,每区都将设有两三个采集点。人的体型尺寸测量需要的样本量最大,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研究院为之设计的样本量最少是2万人,男女各一半,按照年龄分为四个阶段。
“重要的是做好前期工作。”冉令华说,包括抽样方案、技术方案等。但这些“技术活”在她眼里都好控制,“难的是组织管理”。他们计划和各个采集点的政府、高校、科研单位或相关企业合作,招募受测者、租赁仪器。当地没有仪器设备的,从北京运过去。
我们现在连查漏补缺都算不上,只是做一些原来根本没有的基础性工作
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赵朝义也随时关注着人体工效学的应用。在机场候机,他会考虑广播的音量和频率是否便于大部分旅客听清。看见女士穿着高跟鞋走过,他又会马上想到某国外品牌的设计,“同样的鞋跟高度,却能让脚觉得更加舒适”。去参加专家评审会,他站在讲台上环视四周,心里都禁不住有些紧张:“这会场布置和座位尺寸不舒适,影响专家情绪怎么办……”
在精心准备的PPT中,他专门用黑体字标出了这样一句话:“美国、欧盟的劳动保护、职业健康法规中明确规定企业和产品应符合相关工效学标准。”
但根据他的调查,在淘宝网,声明符合“人体工学”或“人体工程学”的商品有49259件,但大多只是作为“宣传卖点”,因为“连标准都没有,怎么去符合”?
“我们现在连查漏补缺都算不上,只是在做一些原来根本没有的基础性工作。”赵朝义强调。中国第一个“成年人尺寸数据库”,在数据采集时忽略了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人群,测量项本身也缺失很多。
在冉令华看来,最需要符合人体基础数据标准产品的人群,恰恰是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不久前,在一座公共建筑物的护栏前,她一岁半的女儿直接把头伸到了栏杆之间。
“我愿意相信这种安全护栏的设计有自己的尺寸依据,但它肯定没有考虑儿童。”这位妈妈焦虑地说,“未成年人是最需要安全保障的人群之一。”
2007年,中国有了第一个未成年人尺寸数据库。我国校车的标准制修订、校服设计、课桌椅工效学评价中引用了该标准中的数据。
但65岁以上老人的数据至今仍是空白,比如老人药瓶上的字号应该印多大,还没有一个标准。
赵朝义表示,他和他的团队“水平是走在前列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159/SC3会议中,日本、美国是标准的制定者,“我们经常被邀请参加会议,标委会对我们所做的未成年人和2009年少部分成年人的数据都非常认可”。
他欣慰地表示:“这几年我们实验室的发展,就是工效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见证,也是中国的工业设计不断‘以人为本’的过程。”他指着院子里不远处一块施工现场,一座新实验楼正在建设。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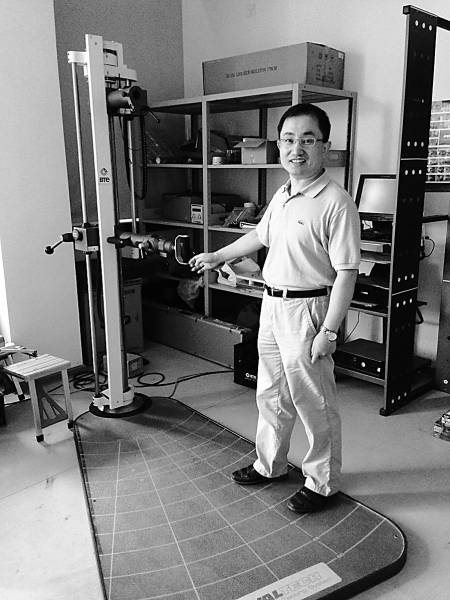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