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端康成的《雪国·千只鹤·古都》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到聂鲁达的《情诗·哀诗·赞诗》,诺贝尔文学奖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曾把奖项颁给了小说、剧本、诗歌、散文。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小说类别中,长篇小说尤其受到青睐,北京时间10日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爱丽丝·门罗,恐怕是唯一一位以短篇小说获奖的作家。
瑞典学院给门罗的颁奖词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而她也早有“加拿大的契诃夫”之誉。中国目前引进门罗的唯一一部作品,是2009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逃离》。这部当时并未引起普通读者关注的短篇小说集,如今一书难求,订购的队伍排到了11月。诺贝尔文学奖此次的青眼,是否能为短篇小说带来春天呢?
业内早已重视,读者尚未熟知
门罗的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出版于1968年,处女作就获得了加拿大重要的总督文学奖。此后,《我青年时期的朋友》(1973)、《你以为你是谁?》(1978)、《爱的进程》(1986)、《公开的秘密》(1994)、《一个善良女子的爱》(1996)、《憎恨、友谊、求爱、爱恋、婚姻》(2001)、《逃离》(2004)等相继出版。
从宣布门罗获奖开始,李文俊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采访电话,因为他是门罗在中国出版的唯一作品《逃离》的翻译者。这位年逾八旬的翻译家,还翻译过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的作品,并将其引入中国。
李文俊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普通读者也许没听说过她,但研究外国文学的人都知道她。《大百科全书-英美卷》中收录了她的作品,《世界文学》也刊登过她的作品。如,《一个善良女子的爱》、《熊从山那边来》。西方文学对她十分重视,像法国《读书》等很多刊物提到过她。”
《逃离》在2009年的首印数是3万册。李文俊回忆“反响一般,是严肃文学,不是畅销书”。如今在诺奖热潮中,《逃离》的责任编辑黄宁群透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在加印10万册,订单仍源源不断。门罗2012年最新的作品集《亲爱的生活》中译本也即将出版,这是她第一次描写自己的童年。黄宁群说:“不止一个人说过,门罗是英语世界文笔最好的作家。”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中国读者在其获奖之前之所以对门罗不够重视,与阅读习惯有关。他说:“中国社会百年来一直处于剧烈变化之中,读者愿意接受与社会问题密切关联的文学作品,希望从中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门罗讲的则是日常生活。她对女性心理的描写,是我们过去所读作品中缺乏的。但她和女性主义没有关系,并不颠覆男性话语。她采用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写作。”
加拿大小镇平凡女性的故事
82岁的门罗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第一次婚姻移居到维多利亚,第二次婚姻又回到安大略省,从此一直住在当地的一个小镇。
黄宁群介绍,门罗的小说一般以加拿大小镇为背景,讲述平凡女性隐含悲剧命运的故事——邻里间的恋爱婚姻、母女冲突等。“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平凡中暗流涌动,表现出女性的虚荣、惶恐、野心等,女性读者读之尤其会有感觉。”王安忆和张悦然之前都曾推荐过门罗。有人评价:“这不是小说,这是生活。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意外,有温情也有残酷,她只是安安静静地陈述出来。”
以“女性意识”著称的作家徐小斌最敬重门罗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爱情只能给女性带来伤痕,女人最高的需求,是爱之前心灵和身体的萌动。“这句话说得太妙了!”徐小斌说,“门罗最好的一点,就是善于找到生活中比较隐秘的东西。她让我想起一个长辈——从30岁开始写日记,写了60年,写的都是柴米油盐,但从平凡中能窥到整个社会的变化。门罗也是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写作。她的小说看似很平凡,但能突然给人一惊:‘哦,就是这种感觉!’”
门罗特别擅长篇幅稍长、接近中篇的作品。她曾说:“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稍长的短篇小说对我最为合适。”
徐小斌对《沉寂》这篇小说印象深刻,讲的是母女二人原本感情融洽,却不知为何女儿突然离家出走,多年后母亲得知女儿已经嫁人并过得很好,母亲很伤心,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不与她联系。小说至此结束,没有解释也没有后续。徐小斌说:“这不是一个严谨的故事,反而更贴近生活,因为生活本身就不完整。”
短篇小说更具艺术纯粹性
孟繁华原以为今年的诺奖会花落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但他觉得,诺奖之前一贯青睐从题材到思想都是“重型”的作家,这次有一个轻灵的、具有大众色彩的作家获奖,也是一桩好事。不然,“诺贝尔文学奖快成了长篇小说奖了,太单一”。有趣的是,门罗也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少女们和妇人们的生活》,但并没有得到关注。
长篇小说容易被改编成影视剧本,读者有需求、出版社有宣传,受到的关注自然多。但孟繁华认为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存在一个问题:对历史问题没有长期关注的热情,只对当下感兴趣,没有如库切的《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那种具有厚重历史感的作品。“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4000多部。一方面作家能即时地表现现实,这是优长。但另一方面,离现实得太近就过于即时性。”孟繁华说,“反倒是中短篇小说,没有市场诉求,在艺术上更具纯粹性。”
有“短篇王”之称的作家刘庆邦2008年访问加拿大时,原本安排了与门罗的交流,可惜她不愿抛头露面,于是失之交臂。此次门罗获奖,刘庆邦“深受鼓舞”。“这个奖是奖给全世界写短篇小说的作家的。”刘庆邦说,“有些短篇小说从理念出发,玩形式,思想大于情感。门罗不存在这个问题。她继承了短篇小说的传统,保持了故事的原初形态,难怪有‘契诃娃’之称。中国的短篇小说作家,其实一点都不差,可能与汉字讲究味道、气韵、情感有关。”
刘庆邦说:“时代在推崇长篇——作家重视长篇小说,觉得这才能确立作家的地位,读者也是读长篇小说较多。其实短篇小说的写作更难,从结构、信息密度、语言的精雕细刻,种种方面,各方面要求很高。但其社会利益、经济利益都很低——成名难,稿费低,不容易和影视剧本接轨。”尽管如此,刘庆邦从1972年开始写短篇小说以来,从未放弃过,他的240多篇作品汇集成《短篇小说编年》,也将于今年年底出版。
孟繁华说:“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数量很少,成就更高的还是中短篇小说,鲁郭茅巴老曹,都留下不少短篇小说经典。”现在,《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十月》等文学杂志都比较注意对中短篇小说的扶持,还有柔石小说奖、林斤澜小说奖、郁达夫小说奖等都以中短篇小说为评选对象。
“中短篇小说这些年一直在发展,但不能指望它大红大紫,一夜成名的时代已经过去。不仅如此,文学也在衰落,被更刺激、更新鲜的文艺形式所取代,比如电视剧、电影。但显然,文学不会死亡。”孟繁华说。
本报记者 蒋肖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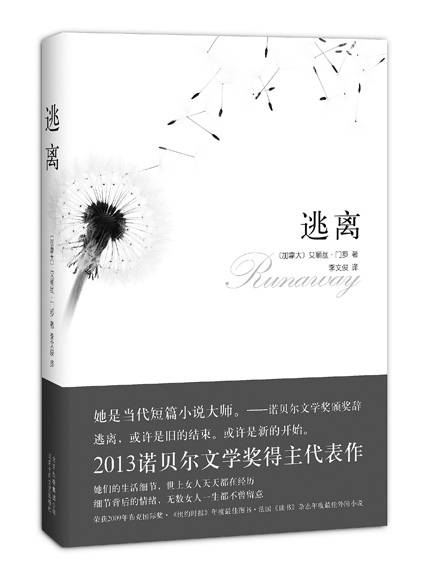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