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次不愉快发生在周末,母亲的电话打来时。近些年她和母亲已经很少通话了,从“周聊”变成“月聊”,频次还在继续减少。电视剧里常演的那种母亲,对着三十多岁不结婚的女儿或循循善诱,或寻死觅活,每一个都很像她的妈妈。
母女间的分歧,大龄不婚也只是个导火索。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是久不见面的母女情感的疏离,“总像有什么断了,搭不到一条线,一次电话也要烦上几天。”她说。
就像那天早晨,她接到母亲的电话,开头和结尾都跟上次没什么两样。“没什么事,就是问问你怎么样。单位就不用去了吗?”这是两年来母亲最关心的问题。那家垂死挣扎的公司,在两年中持续低迷,如今连办公室都要换在单元楼里,大家稀稀拉拉地上班,都在忙着找下家。
而母亲却很执迷。春节时回家,姑姑们争相找她谈话,从那些拐了几个弯的聊天中,她隐隐猜到,母亲对她工作的担忧。母亲猜她是得罪了什么人,别人都好好的,只有她干不下去了。
这引发了她巨大的反感,再听母亲问,“单位就不用去了吗?”她亦没好气地说,“还是那个样子,不过看来是好景不长了。”母亲“哦”了一声,再没吭声。她开始讲别的事,新近的工作,转型的辛苦与兴奋,母亲在那边咿呀哦的,提不起一点儿兴趣。末了,母亲说:“就不想找个人吗?”“暂时没有合适的。”她陷入沉思,电话已经被挂断了。
她在朋友的聊天群里问:到底,该跟母亲聊点什么?答案千奇百怪,聊新近的电视剧、聊做菜、聊广场舞、聊明星绯闻……如果这些她都不关心呢?一个人跳出来说:我跟她,什么也不聊。
如果有个孩子就好了,也许能聊聊孩子的成长,那样,母亲就会在她的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变得充满希望。现在这个打算重塑自己的人,使母亲陌生,她们隔着千山万水,谁也抵达不了谁的世界。
电视上在播《变形记》,比起那些在乡野里勤奋刻苦的少年,她仿佛更能触摸到都市叛逆少年们的青春。在他们肆意张狂地与父母对峙时,总有一个画外音跳出来:你就是不能理解我。
把这样的烦恼说给朋友们听,一位女朋友站出来说,讲个故事权当安慰你了。当年,阎连科动用所有积蓄,买了一栋别墅,后赶上拆迁,无论如何那别墅没保住。精神压抑时回到家,家里人正围着电视看《甄嬛传》,扭过头对他说,你也写点儿这样的,别净写那些有的没的。回城时弟弟送他,到了村口特意叮嘱:现在我们的日子都过得可以了,你千万不敢闹事,把日子过好就得了。弟弟走了,他一个人蹲到村口抱头痛哭。
女朋友的结语掷地有声:你终将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人家呢,“理想国”都被拆了,也没得到家人的理解。
那个上午,在这番话后,她还真的露出了微笑。要求两种生活状态的人必须彼此理解,是不是也是对亲情的极端要求?
李轶男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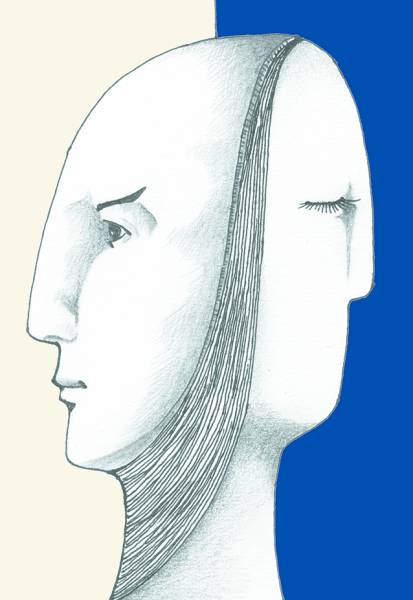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