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所谓好的社科类图书,一般都有两个特点:写得丰富扎实,文字有可读性。但我读这类书,特别看重在场感。且以清晰说理为强项,具有一流的叙事与描摹功力,知识与想象力兼备。就像德裔学者、多栖作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书,即使是讨论学理的问题,多少都含有个人体验,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书,虽是思想史,文字的质地却能造出一个三维空间,有一个好看的入口和深深的思想长廊。
我推荐的2014年度社科好书为:《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人类简史》、《 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致命的海滩》、《看不见的森林》、《自我颠覆的倾向》、《荣耀与丑闻》、《明亮的对话》、《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别把自己当造物主
过了2004~2006年这一分水岭,互联网商业,跟着技术革新进入一条超音速公路,我们念叨着“颠覆”、“迭代”、“互联网思维”,谈论着几个头顶着天文数字身价的名字,因为听到了不熟悉的名词觉得自己似乎又落伍了。可是谁也不会作这样的横向比较:我的智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比如,就算再给黑猩猩一万年的时间,他们也不可能进化到会使用手机的程度……
尤瓦尔·赫拉利,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一名教师,在他的《人类简史》里说,人已打破了自然演化的游戏规则,近10年的变化速度,是过去50年无法想象的,而近100年里的技术进步,超过了过去两千年。他说,这就很可怕了,人很可能控制不了自己生产和缔造出的东西。想一想这个常识:一个游戏者脱颖而出,把其他竞争者都远远甩在了身后,然后就宣布游戏结束,关起门来发展自己,任意摆布其他生命——这很可能是一条通往自取灭亡的路。
3年前,《人类简史》以希伯来语版问世,赫拉利自己将它译成了英文,畅销程度直追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它受关注,有作者自身的缘故:他生于1976年,这么年轻就这么悲观,为什么?
赫拉利很渊博,同时又有种不失天真的世界观。人跟其他生物之间在进化道路上的剪刀差之势,让他心生恐惧。现代社会太复杂,这让赫拉利焦虑不安。
他本能地提出质疑:越玩越复杂、高端,这样可以吗?他绝望也不乏幽默地跟读者说,嗨,忘了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吗?因为独霸了进化链的终端,我们就真拿自己当造物主,无视身上的动物性了吗?最近几年,科普书里不乏谈论同类话题的作品,例如谈自私的基因,谈两性关系的生物本质,但还少有像《人类简史》这样,从生命起源一竿子捅向“智人的灭绝”的。如果你站在赫拉利一边,那么面对任何当代的现象,你都会有种仔细一想,觉得恐怖至极的感觉。
每个人都是一片森林
人类学本该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可在中国,之前的积累几乎为零。现在,它也随着科普读物兴起的大潮,像一颗种子一样缓慢生长。
我愿推荐《看不见的森林》给所有人。虽则大体上看,它未脱沉浸于对外物的观察中,阐发环保思想的套路,但作者D·G·哈斯凯尔不是仅有普通的环保主义者情怀,他是一位生物学教授,思考着人类行为和环境的关系。他有一种除幻的自觉,即,不要幻想着把世界改回人类行为之前的样子。人固然改变、污染、破坏了自然景观,但这也是自然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例如,人类发明高尔夫球的游戏,正说明人是从大草原上的猿猴进化而来,如今“这些灵长类动物潜意识中依然向往着那些地方”。对待自身,哈斯凯尔的态度也更加温和。他认为,热爱世界,就得热爱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活泼嬉戏,只是,“我们最大的缺点是对世界缺乏悲悯之心”。
这是另一个角度。赫拉利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强调“自然离开了人可以运转得很好”。哈斯凯尔则说:“不要因为爱自然而憎恨人类,我们进入了一个连带的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里,所有的角色都是互相依存的,没有哪一环节能拥有完全的个体性。”
书名中的“森林”当然是一个隐喻。哈斯凯尔的森林存于每一只小昆虫身上,每一片落叶,每一粒沙和一滴海水之中。这些细小至极的东西,朝生暮死的生命,包含或折射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循环,便应了诗人威廉·布莱克那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森林各有不同,与之相仿,每个人也都如森林一般,身上包裹牵缠着重重叠叠的故事和经验。所以才有人说,对好的作家而言,一天的经历就能写上一辈子。
一个人一生可以出席很多重要时刻
威廉·夏伊勒既是好作家,也是经历丰富的人,因而论写煌煌巨著,舍他其谁?夏伊勒一个人覆盖了整个20世纪。都说读史鉴今,如果将来,有哪个物种要以“人类史”为鉴,应该会去研究夏伊勒的三卷本《 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
读后,最大的感触是,一个人一生可以出席那么多重要的时刻。就说记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卷: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夏伊勒在场。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他在场。当德军进攻波兰时,波兰人以骑兵去对抗坦克,他还在场,目击成千上万的波兰骑兵和战马葬身。除了运笔如神外,在无可抗拒的大局之下个人的抉择,读来也是可信可感。
夏伊勒的能动性还有一个表现:他希望把一个故事跟到底,不管它会发展到哪一步,不管他会看见怎样的事实,他只要看真实的样子,而不是他希望看到的样子。当他明白自己做不到这些时,他就离开。他的回忆录,因此也染上了一种壮阔的奥德赛色彩。夏伊勒的代表作《第三帝国的兴亡》里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这套作品里找到;在德国待了6年,目睹它从一个极有文化的国家沦为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恶,并且为它的过去致哀。
当“绝望”变成常态
跟着最好的写作者,你就有穿行于森林之感。夏伊勒健步如飞,费尔金斯也不遑多让,一部《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够让你屏息凝神一天半载的工夫。他们都是真正的记者,费尔金斯写出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地发生的最真实的事件,但费尔金斯还把情感隔离在视野之外,让战火中的人们自述自己的生存状态。读这本书,感觉他所描写事情有如发生在隔壁一般。“我没有办法哀悼太多亡灵”,费尔金斯写道,但他有办法把亡灵背后的故事说出来,这比哀悼的难度大多了。
在一些城市,生死一线,“绝望”是种常态。可是,一旦深入历史的细枝末节,你才知道可怕的事情原来如同身上的毛孔一般无所不在。在读罗伯特·休斯的《致命的海滩》前,你能想象这片天蓝草绿的大陆曾是令人绝望的地狱?同为大英的拓殖地,广袤的北美大地给人以自由,而同样辽阔的澳大利亚,情况却相反,巨大的空间却使流犯们熄灭了生的信心。
虽然休斯使用的全是搜集来的资料,包括流犯们的书信、日记、政府公文、政要回忆录、探险家和淘金者的笔记、民间传说以及民歌,但他写得犹如亲历者一般细腻入微。
不管后来的澳大利亚如何富庶,它的起源是一片卑微的混乱,凌辱流犯,屠杀土著人,还有野生物种的毁灭。人间地狱曾在这里出现,尤其是在邻近的两个岛屿上,局促的范围、简单粗野的人际关系,加上返家希望渺茫,催生了虐待狂和独裁者。白人管理者在这里进行监狱制度实验,流犯们粗鄙无文,手里的唯一擅长就是犯罪。
一个文明的澳大利亚,正是从这些混乱之中问世的,这又让我想到《人类简史》里反复重申的观点:人从动物中脱颖而出,并至少淘汰了其他六个同源的“智人”种族,方才延续至今。澳大利亚并非一步一步规划演进而成,服役期满的流犯艰难地以劳动立足,建立生存秩序,慢慢吸引到一些自由移民;而最后,流犯制度还得终结于偶然发生的淘金热:金矿让它作为流放地失去了意义——我们从中看到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结论,即终结暴力的不是文明,而是贪欲和利益。
让诗意的精神穿透一切
夏伊勒所感念的那个旧德国,也可在另两本新书里看到:《荣耀与丑闻》和《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两者都跟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潮有关。《荣耀与丑闻》的作者,德国著名学者、尼采和席勒专家萨弗兰斯基,用一厚册的篇幅来谈从赫尔德、席勒、费希特等开始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一路经荷尔德林、尼采、瓦格纳、海德格尔,最后谈到“丑闻”,即浪漫主义的兴起同纳粹德国之间遥相呼应的关系。这种关系错综复杂,论者莫衷一是,但萨氏的论述里有一点很明白:德国浪漫主义的开始就是趋于极端的,德意志的山水森林,中世纪的城堡和废墟,让知识分子们寄情其中,萌发了民族主义的苗头。他们高举想象力的旗帜,号召以幻想来掌权,“让诗意的精神穿透一切”。经浪漫主义的激荡,德意志人养成了良好的读写习惯,文化素质特别高,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着手在地上建立心中的理想秩序。
以赛亚·伯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里所说的3个人,都跟浪漫主义有关:维柯、赫尔德、哈曼。他们都是启蒙的敌人,启蒙运动是主“合”的,宣说一些普世真理,而批评它的人,自然主“分”,唯恐启蒙精神抹煞了文化的多元和特殊。赫尔德讲“每个民族有其幸福的内在核心,就像每个球体有它自己的重心一样”——没有什么企图,比同化不同文化的核心更为致命。这不只是审美层面上的,已经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上。由他开始,浪漫主义思潮塑造了德国人的性格。
博学多才的以赛亚·伯林拿思想史当一个智力泳池,在里面扑腾,萨弗兰斯基在书中也引用了伯林的观点。他们都或明或隐地认为,浪漫主义虽然在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但主要是“德国的童话”,因为它与德意志的“地之灵”结合得最为紧密,如同树栖于土,影响也最恒久。受浪漫主义熏陶的德国人,相信艺术高于一切,创作是文化精英的分内之事,他们看出去的风景都蒙着一层梦幻的色彩。这是一种文化现实,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它塑造了德国人身上一些讨人喜欢的特质,但也与其让人恐惧的另一面有关。
面对两条领带的选择
写书的人,都有问题意识。最难的不是收集对自己有利或不利的证据,而是超越自己的问题意识,做到不固执己见。这就需要读读另一个德裔学者、多栖作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书。
年初,他的一本《自我颠覆的倾向》令人惊艳,赫希曼用一个犹太故事阐明他眼里的一个人性特点:一个犹太母亲送给孩子两条领带,作为他的生日礼物,第二天儿子便戴上了一条,本以为可以取悦母亲,想不到母亲大发雷霆:“另一条领带呢?你把它放到哪儿去了?难道你不喜欢它吗?”
领带的故事可以是个应用广泛的隐喻。我们讨论任何历史和现实,都会想着,如果当初没有选择一,而是选择二,是否会更好?或者,因为选择一被证明是好的,就认为选择二一定是不好的。他说,他只要不戴上第二条领带,就不知道是否真能讨得母亲的欢心,而所有的学术研究和问题思辨,也都必须依靠后见之明,对未发生的事指指点点,预测未来,实属无益。因此,人们必须在事前就调整问题意识,兼及问题的正反两面,这就是“自我颠覆”的来源,它不仅不痛苦,反而是种巨大的诱惑。
《自我颠覆的倾向》也是一本别致的自传,虽然偏于学术的一端,但赫希曼回顾人生的几个片断时,总是持有的犹太式自嘲态度,以及一旦产生一个想法,旋即为它找来相反观点的习惯,是学人写作中特别罕见的。我想这是一种良好的思维习惯。
同样,旅美华人徐贲的《明亮的对话》,也是在帮助我们建立基本的思维及对话的习惯。这本书写得特别用心,对种种逻辑陷阱的阐释,可以帮助读者避开许多话语误区。如同人类学一样,有条理地、有见地的分析和对话,同样也缺失于我们的基础教育。可惜的是,它只能得到成年人的阅读,而且,许多需要它指导的人大概不会读它,因为他们还未意识到自己的言思需要受一番训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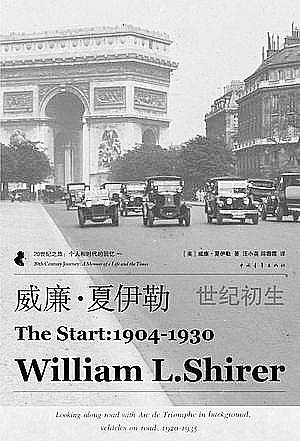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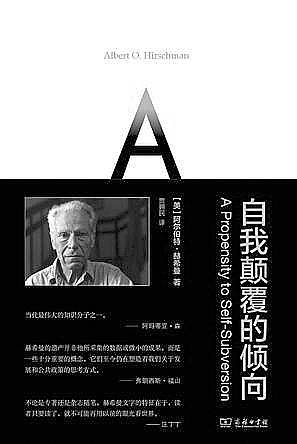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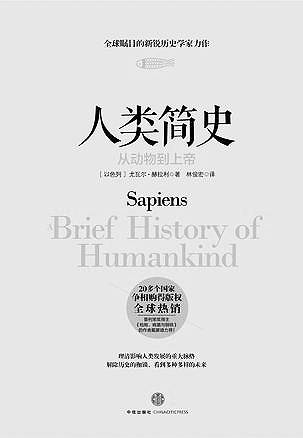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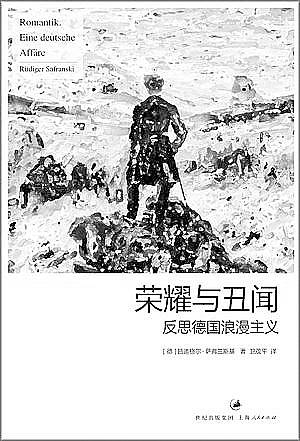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