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波的小说《蒙古里亚》是一个穿插了几条线索——历史和现实,神界和人界,西方和东方,草原和煤矿,佛陀和萨满的复杂故事。“我”是故事中人,却也是个外来者,一个从草原之外来的观察者和叙述者。他离开草原多年,现在,他飘荡的魂,正栖息在芨芨草尖上回望故土。他看到了什么呢?
当他向历史深处望去的时候,他先是看到了一个人,一个叫亨宁·哈士纶的丹麦学者、探险家,他把他比作飞进草原的一只鸟。那是1926年12月,蒙古高原,寒风刺骨,雪暴横扫大草原。就在此时,这个叫哈士纶的人,离开了生活习惯的城市,以中国瑞典共建的中国西北科考团后勤队副队长的身份,进入了这片蛮荒世界。他和他们来干什么?这是“我”的疑问,恰恰也是这部小说的起点之一。
当然,对“我”来说,鲜活的生活也许更具吸引力。这首先是因为,他本人就是这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他就会发现,他被生活裹挟其中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小说中很重要的一对男女此刻就正在不可阻挡地走进他的生活,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他将这一切解释为梦的启示。这时他刚刚从一场白日梦中醒来,在山顶的古敖包旁,他梦见了去世多年的大爷爷。事后我们知道,他此行飞回草原,是来寻找自己灵魂的,而这位大爷爷,恰恰与他要寻找的灵魂有关。不过,在梦中,大爷爷并未就灵魂之事给他明确的答案,而是提醒他该去关心一个叫约苏模尔根,又叫特勒约苏的人了。稍感匆忙的是,他刚从梦中回到现实,这个人就让他撞个正着。
小说便沿着这两个向度展开了,像一条大河的两个源头,在草原上缓缓地流淌,最终汇合在一起,成了蔚为大观的景象。这两条线索有一个共同点,主题都是寻找,而哈士纶的寻找和多年后“我”的寻找殊途同归,都指向一点,即蒙古族的精神信仰,这是他们在叙事中能够交汇融合为一体的前提条件。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很显然,哈士纶的故事为作者成功介入蒙古族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便利。他是要感谢哈士纶的,因为,多年之后,他不得不借助这个西方人提供的线索,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听上去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但如果不是他们冒死抢救和保存了蒙古族的文化遗产,避免这些充满了东方神秘色彩的古老文明毁于戈壁的沙尘和历史上的革命、战乱,“我”的寻找灵魂之路也许还会曲折、坎坷得多。
哈士纶终其一生都行走在蒙古草原上,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他追随着蒙古牧民,在漫无边际的大草原上游荡、迁徙、冒险,近距离观察牧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并且身体力行,切实体验。他们把他当作最可信赖的忠实朋友,向他讲述先人历史中的传说和神奇往事,为他唱出自己心爱的歌曲,向他吐露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发现,他们信仰的佛教或萨满虽然有很神秘的东西,常常使他感到惊诧,但其中也有人类共同的对美和尊严、荣誉的渴望。他愿意理解和感受这一切。他相信,信仰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这里,没有没信仰的生活。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历尽千辛万苦,深入亚洲大陆,如果仅仅是为了搜集蒙古族的音乐,我们还看不出他的寻找和“我”的寻找有哪些内在的联系,如果我们把他的行为放在东西方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其特殊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实际上,进入20世纪以来,欧洲思想文化界的反思,已经把目光投向东方,或者说,是把东方作为西方的重要参照。他们看到,科学昌明以来,唯物派哲学大兴,高悬起一种物质主义的、简单机械的人生观。宗教本是从情、意两个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现世的道德便以这信仰为基础,现在却被“技术”打得落花流水。其后果就是享乐主义越发得势,人的敬畏之心也没有了,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可能地享受这几十年的快活,一切都由客观规律做主,人也就不必承担善恶的责任,又何妨尽我的手段来满足我的欲望。
于是,神秘的东方就成了他们想象中上帝为人类灵魂保留的一块圣地,他们纷纷来到东方,其实是想从这里找回自己,重建一种精神信仰。至此我们也就理解了“我”的寻找何以会和哈士纶的寻找重叠,最终走到一起,尽管这里显然有一个东西方发展的时间差。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在这里,霍伦煤矿既是人的欲望的一种象征,也是现代科学的标志,它代表着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进步和堕落,都属于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作者在叙事中以历史映衬现实,使现实获得了一种历史纵深感。就像哈士纶最终找到了萨满博额阿拉坦嘎达苏一样,“我”最终也被告知,其灵魂竟是大爷爷的重生转世。我把这理解为作者的善良愿望,他试图以萨满博额认识世界的方式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很显然,两种世界观、人生观的竞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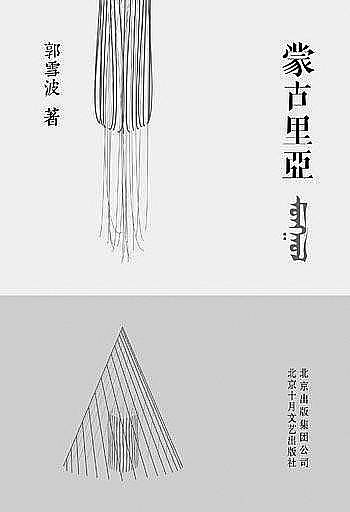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