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的人生中,我一共上了12年语文课,读过24本教科书,学过的课文几百篇,但当我搜肠刮肚想要回忆起它们的时候,记忆就像开久了的可乐,冒不出一丝气泡。
只有一篇是例外,名字就透着股诱人的气味——《十八岁出门远行》。18岁,远行,多么容易拨动一颗青春期的心。
那是一篇带星号的课文,意味着老师不会精讲。我是在晨读时看到它的,没有几页纸,不记得有配图,读完觉得作者余华好酷。
用“酷”来形容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词汇实在匮乏,习惯了用“爱国主义”“怀才不遇”“忧国忧民”来形容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余华到底想说什么,我说不上来,但又似乎感同身受。
现在闭上眼,我脑中还能浮现那幅画面:“我”走在热气腾腾的柏油马路上,四周空无一人,“我”想搭个便车找旅馆,后来汽车抛锚,老乡涌上来抢车上的苹果,“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是血,最后剩下遍体鳞伤的“我”和汽车,司机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竟对“我”大笑不止。
读完感觉余华这个神经病在做梦,可我也好想像他一样做梦啊。他说过:“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
而我呢?学生时代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长期霸占着文科的年级第一。不早恋、不上网、不打游戏,梳着一丝不苟的马尾辫过着毫无生趣的青春。连站在操场旁心思迷乱地张望男生打篮球,都觉得是浪费时间的自轻自贱。与我的青春一样毫无生趣的,是印象中的语文课本。但我已经习惯把自己困在其中,研究文章的深刻内涵和自以为是扣在作者头上的思想感情。
但余华是语文书里的“异类”。当我读到他的文字时,脑海中浮现的是宇宙星辰、空旷草原、无边大海……
那是对一个闭塞的庄重的严谨的少女最初的鼓动。那时的我快18岁了,却从未出门远行,我被父母和老师包裹在单一的世界里,用最笨拙的方式获取最简单的胜利——是的,如今回头看来,没有比拿好成绩更显而易见的途径和立竿见影的效果了。后来世间的种种,都非努力和恰当的方法就能换来结果的简单事。
而余华似乎已经站在高处睥睨到了这一切,为我温吞的青春感到不齿,“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文章里“父亲”对他说。
余华在文章里梦呓般反复在说的是,“走过去看吧”。这部写于1986年的余华的处女作,像是一部公路片,对于躁动的无知的年轻的生命来说,“走过去看”是唯一的告解。他不断怂恿我去试试呗,管他呢。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马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后来我也背起了背包,南下到千里之外的城市读书。那时我已经20岁,拥有朴素的世界观和毛茸茸的面颊。青春期的迷茫在我身上留下尾巴,我依然不知道该找寻什么,但就在一次次“走过去看”的过程中,我这个近视眼像戴上了眼镜,世界逐渐清晰了。
那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走在南方城市的校园里,看到的夏天是街上的花伞、五颜六色的裙子和姑娘光洁的大腿。
当我再一次想起余华时,已经是大学的尾巴了。那时的我,在一个更南方的城市实习,每天穿着上班服,拎着公文包走在潮湿又闷热的空气里。在一个久违的空当,我决定去附近的岛上爬山。
因为不是公共假期,岛上几乎看不到游人。7月的太阳毒得吓人,树叶纹丝不动。我走在狭窄的山径上,周围安静得听得见伸着舌头的野狗的呼吸声。我到底在干啥?
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岛,第一次爬那座山,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我不知道是不是走错了路。我喝光了矿泉水,热得快要昏死过去。我突然想起余华和他的贴在海浪上的马路。
心情忽然开朗了起来。“走过去看”本身就足够有趣了,为什么一定要赋予它某种意义呢?我已经不记得后来怎样走完了那座山,我没有遇到汽车,没有遇到抢苹果的人和难以捉摸的司机,但那次飘忽忽的行山,越来越像自己做过的一个梦。
再后来,我不再做一个面目可憎的极致的唯物主义者,我知道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我开始理解“我”不是宇宙万物中心。
后来的后来,在一段采访里,我终于看到了类似的情绪,那是与法国国宝级女星让娜·莫罗的一段对话:
“您可以讲个您生命中福至心灵的典型故事吗?”
“我8岁时,第一次拥有一辆自行车。一个公共汽车司机——当时我发疯似的爱他——把自行车从汽车上卸下来。他拆开车轮和车把上的包装,对我说:‘你可以骑上去了。’我还从来没有骑过车。那里有一个很陡的石子坡,我像飞一样冲下去。车飞着,飞着,我不知道刹车在哪儿,不知道该怎么停下来。我倒在地上,膝盖流血,几乎昏迷,但我想:他说得对,我可以骑车。于是,车轮转起来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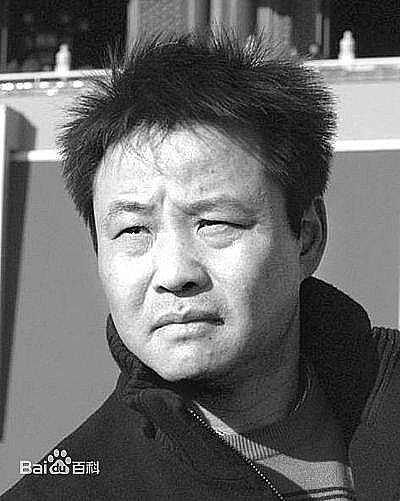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