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这个词用在徐爷身上,其实并不恰当。一来这是北京土话,放在天津人身上,多少有点拧巴;二来,其实徐爷不算老炮儿,老派绅士倒算得上。
可是,不知为啥,看完《老炮儿》以后,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从另一个角度,倒能讲得通——年轻时很“玩儿闹”,在玩儿的圈子里有一席之地,能折腾,别人以“爷”相称……
徐爷是我中学时的老师,后来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我初中时,他是体育老师,本来我们应该无甚交集,因为他教男生,另有一位女老师教女生。但是,作为一个“玩儿家”,只教体育怎么行呢,每周的书法兴趣小组,是徐爷来带,什么都喜欢学一学的我刚好参加了那个小组,现在写了一手不算丑的字,便拜他所教。
也不知为何,那个时候很多男生不喜欢徐爷,背后常说他坏话,觉得他“劲儿劲儿的”,而且明显对女生照顾,对男生严苛。这点倒跟老炮儿们挺像,他们很多时候也不招人待见。可是,我后来发现,对女士的绅士风度,源自徐爷的家庭氛围和幼年受过的教育。他小时家中富足,住小洋楼大院子,家人送他读天津最好的学校,家中规矩也颇为洋派,后来家道败落,可习惯、心性已经养成了。
徐爷特别能玩儿,且什么都玩儿得通。练过体操,弹过钢琴,拉过小提琴,吹单簧管,后来又喜欢国画和西洋书画,除了体操这事儿不能自修,其他的都算自学成才。后来,到了我高中时期(中学六年我读的是一间学校),他干脆就在学校开了一门艺术鉴赏课。授课模式跟大学相似,每学期的课程有好几个主题,一个主题延续几周,一个学期下来,通常每人都能攒下几个小艺术作品。印象里,我们玩过篆刻,做过印章盒子,写过千字文,学过书画鉴赏。
因为我也爱玩儿,后来高中毕业,上了大学以后,和两位同好的密友,仍旧常常到徐爷家去刻章、写字。那时,他住天津最中心位置的胡同里。一个二层的小楼,不是洋楼,真的是“小”楼,通往二层的楼梯在室外,楼下是一间书房一间卧室,每间都有点局促,站进3个人就觉得转不开身。徐爷存货又多,大大小小的柜橱箱子里,都藏着他的家底儿。每次我们去拜访,必要拿出来一些好玩意儿给我们瞧瞧。
那小院虽窄,我却很喜欢。因为暑假去他那里玩过一会儿,很是惬意。通常,徐爷在院里铺开一张方桌,几条板凳,我们各占一边,或读书,或写字,或篆刻,分别闷头做作业,遇到做不好或想不通的地方,便问问在一旁的徐爷,然后接着做。师娘时常端来几碗绿豆汤或茶水,让我们消暑解渴。虽是夏天,小院却清净又凉爽,让人能平心静气写写画画,几日下来,收获颇丰。大学时的几个夏天,大约也是我“艺术成果”最好的时候,不但字精进了,还给身边好多至亲好友刻了一枚印章。
再后来,我们各自毕业、工作、恋爱、结婚,徐爷也从原来的中学退休。那小院子拆了,他搬到离市区颇远的生活区。退休之后,徐爷仍旧爱玩儿,闲不住,和几个朋友操持了一场挺大的画展,在大学里兼职教画画,每周还得抽空去淘宝——他喜欢收藏各种篆刻石料,见到好石头就忍不住想收。
他家搬远之后,我们偶尔有空也会去探望,但可能两三年才露上一面。有一年春节前,徐爷唤我们一起写春联,我们买了好些东西算提前拜年,可一进门他就狠批我们。“来我这儿,随时都行,什么也不用买。下次再买,我可不接。”批完,还照旧拉着我们一面用他的捷克水晶杯喝茶,一面看他新近收的宝贝,各自诉说新近生活趣闻。我忽然发觉,徐爷老了,喜欢说从前旧事,喜欢说这两年已经不做的教画兼职,还喜欢说再前几年办过的那次展。可从前,每次我们相聚,他总是迫不及待要说新鲜事,或者拿出刚画甚至未干的画给我们看,或者说说最近他的新点子。我总以为,人如徐爷,岁数是一回事,心态却永远不老,玩儿心重的人不就年轻吗?
然而,原来爱玩儿的徐爷也跟所有人一样,在渐渐老去,在渐渐地与社会的中心越来越远,连在玩儿的圈子里地位也大不如前——这时代新人辈出啊,旧事旧人,总会被新事新人所替代。爷也不再是原来的爷了。可即便如此,徐爷还是跟年轻时一样,爱玩儿,喝咖啡,出门骑跑车,戴洋帽,穿着讲究,即便圈子越来越小,即便连忘年交的小友也越来越没有时间和他一起玩儿,他仍旧保持着惯有的生活步调。“人得有心气儿。”这话,徐爷常说。
想到这些,我忽然情绪汹涌,眼眶微热。又是两三年未见,今年,要好好拜会一下徐爷,空着手,除了满肚子的话,什么都不带。
史潇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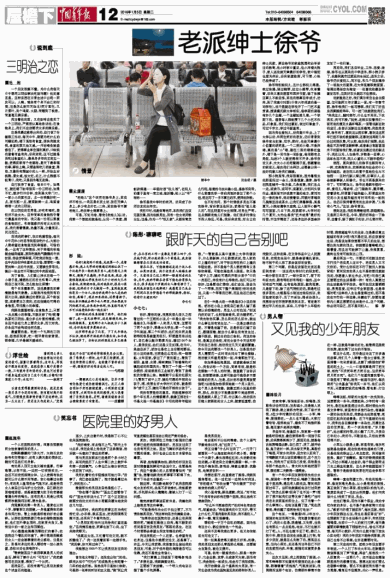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