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导师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他们庄重、严厉,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身份,甚至国人还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这显然与西方的观念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古代读书人的人生进阶只能依靠科举制,遍布民间的私塾是国人受教育的主要渠道,因而,私塾先生在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因为私塾先生的身份和受教育者的仕途、命运紧密结合,对一些缺乏“耕读传家式”教育的孩子来说,一个出色的教书先生犹如再生父母,“哺育——感恩——回报”的模式成了当时最常见的师生关系。但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涤荡下,私塾先生的知识和教育观念显得陈旧、迂腐。清末民初,越来越多的人抛弃私塾,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现代文化。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机缘下,导师的身份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教授西方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文学的导师,往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比如,在“五四”前后的北大,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样推崇新学的导师,也有辜鸿铭这样的守旧派。当然,新旧不是绝然对立的,如“清华国学四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是民国知识界的翘楚,与其说他们是传授知识的老师,不如说是传播、创造文化的精神领袖。在这个进程中,导师的身份也由授业“先生”向知识分子转变。
此后,导师的身份和形象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他们曾经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蜡烛”“园丁”和“鼓手”,也曾在“文革”中丧失了师道尊严。改革开放后,伴随“四化”建设的强烈需要,各行各业的导师再次走到前台,大学教师一度成为人们眼里最受尊重的职业。不过,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老师也逐渐向“老板”转化。
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让导师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所学、所教,能否改变自己和学生的物质生活、现实处境,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因为“经济收益”不大而被逐渐边缘化,经济、金融、理工等专业成为宠儿。与之相伴的是导师与老板身分的合二为一,越来越多的导师不再只是传道授业的先生,成了为申报课题、知识转化而奔忙的“老板”。
“老板”来了,“先生”走了,很多人对此颇有微词,甚至认为这是读书人的耻辱。其实,“学以致用”本身也是教育的功能之一,大量理工科、经济学的知识就是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因此,既要尊重能孜孜以求深奥学术的导师,也要理解那些能“变现”、懂经营的导师。我反对的是那些不尊重学生、浮躁地追求功名利禄的“老湿”“叫兽”(网友调侃语),只要他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有助于帮助学生增长能力,他就是值得尊敬的好导师。
黄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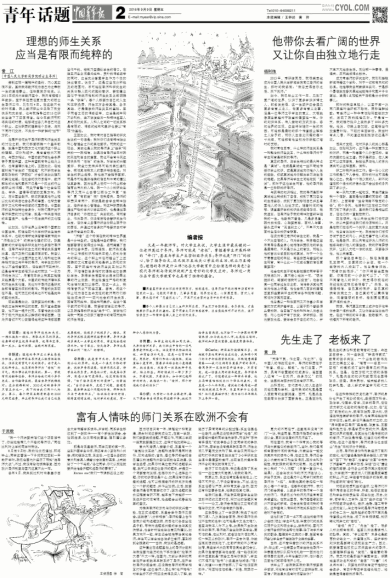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