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凯鲁亚克创作于1957年的小说《在路上》,影响了几代年轻人,这部小说在中国也有许多拥趸。只是原著中带着颓废的自由气息,并不适合在中国传播,它被异化成“远方”、“姑娘”、“梦想”等词汇,成为矫情的小资文化的组成元素。
西方的公路文学、公路电影,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对接土壤,因为中国人的“在路上”,总是充满生存焦虑,比如历史上三次著名的大逃荒,比如现在每年被称为“人口大挪移”的春运……对应“在路上”,中国有一个字叫“飘”,“飘”这个字近百年来已经融入中国人的骨髓,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生存状态。
想到写这些,是因为最近读了一本年轻作家写的书,《飘二代》。作者名字叫王若冲。在她年轻的生命体验中,“飘”就如影相随,父母飘在广州,她出生于广州,后来母亲到北京工作,她又飘在北京,因为非京籍没法高考,她在初中时就走上了飘往国外的教育之路,眼下正在美国一所大学就读。她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命名为《飘二代》,这也是给无数像她一样的年轻人的共同命名。
“北漂”是1990年代末盛行的词汇,那个时间段,也是三四线城市不安分的人开始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萌动之初,最初的“北漂”概念被美化不少,它被赋予了“改变命运”、“实现梦想”、“追求自由”等成分,尤其是外地知识分子的“文化北漂”,使得“北漂”更额外多了一点理想主义色彩。2000年,《新周刊》推出“飘一代”封面报道,把“飘一代”真正写进历史,那篇报道的预言性,如今依然能随时得到验证。
“飘一代”的漂泊动力,不是来自1942年由饥饿导致的历史阴影,而是源自1980年代充盈于文学作品与流行歌曲中的“精神还乡”潮流,如同电影《立春》所描绘的那样,无数人惊觉自己的精神故乡并不在“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而在遥远未知的他乡。于是一个至今未解的悖论就形成了——“北漂”在北京找到了精神安慰和生存土壤,某种程度上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但因为体制原因,却不能实现精神扎根,归属感始终处于悬浮状态,“飘一代”这三个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个状态。
在读《飘二代》之前,以为“飘一代”的那种无奈的愤怒和淡淡的哀伤,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但读完之后发觉完全不是这回事,《飘二代》的作者,完全没有父辈们因为“飘”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焦虑,“飘二代”在感受家庭因为“飘”的事情而烦恼的同时,也在自觉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理论——在他们看来,“飘”是父母的事情,和自己并无太大关系,并且,“飘”是与生俱来的生活状态,“飘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变化的环境强化了他们适应世界的能力,“飘二代”在感受到无法融入当地环境的时候,也把情感寄托在了别处,不断用思考与观察来判断自己的生存环境,让“飘二代”具备了前几代人没法拥有的淡定。
也没法拿王若冲和曾经引起“80后”写作潮流的韩寒、郭敬明相比,作为一名“90后”,王若冲的写作没有受到上一代哥哥姐姐们写作的影响,当然,更没受到国内文学圈其他人物或写作潮流的影响,她是成长在互联网高度发达时期的一代,随着父母的漂泊,在物理意义上打开了她的活动空间,而通过互联网阅读也使得这一代人拥有了世界思维。她写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心理,写青春期,就是直来直去地对外宣告。她的思辨能力,是在自己的思维体系中建立并完善的,这使得她通过一些故事传递出来的观点,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无从反驳。
“飘一代”飘到了北京,就飘到了尽头。而“飘二代”打开翅膀,北上广只是他们的起飘线,未来在哪里,没法看到。“飘一代”的未来是可以看到的,孤独终老是“飘一代”的宿命,但“飘二代”不会承接这样的宿命,因为他们一直“在路上”,并且习惯了“在路上”,他们会对路上的一切感到亲切、熟稔,要值得向他们祝福地是,在“飘二代”身上,终于卸下了近百年沉淀下来的苦难文化负担,他们是真正轻松地在飘。这真让人欣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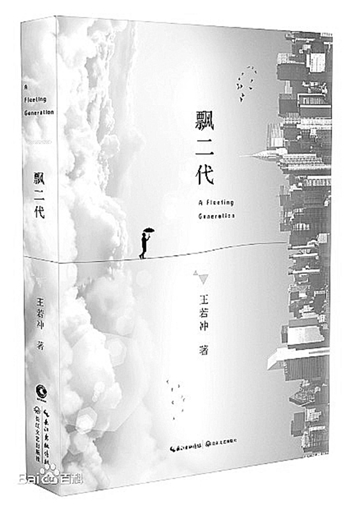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