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时刻感受着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姥姥经常陪我住院,出院之后也依然把我当做一件易碎品一般呵护。大人们常说孩子小不懂事,但那时的我却从不会给姥姥添麻烦、惹她生气,因为我知道,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真是从心底疼我,而我,也同样心疼她。
大了几岁,我的身体结实了。由于多病,比同龄人晚了一年上幼儿园,姥姥一方面害怕我不适应集体生活,另一方面仍然担心我的健康,于是坚持每天送我去幼儿园,一直看到我与其他孩子开始正常活动,才会安心离去。每天放学,我也总会看到姥姥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幼儿园大门口。时至今日,历历在目。
那时姥姥脸上的笑容开始多起来,看到我玩耍,看到我学着大人说话,看到我向她跑来,她会抱住淘气的我,在我额头或是脸颊上“狠狠”地亲一下,我甚至会觉得有点痛,然后笑着叫着挣脱姥姥的怀抱。当我转过身时,永远可以看到姥姥满脸的知足。
6岁时,我离开姥姥家和父母一同来到北京,记忆中我大哭了一场,原因是要去的那个名叫北京的地方没有姥姥。姥姥却表现得很高兴的样子,说想姥姥了随时就可以回来。时光自顾自地走,每年过年,爸妈都会带我回“有姥姥的”那个城市待一段时间,而在姥姥面前,我又仿佛被解开了缰绳一般“肆无忌惮”。姥姥还是会抱住我亲吻我的额头和脸颊,力气没那么大了,也不痛了,但她脸上浮现的满足却未减半分。
每个过完年准备回京的早上,姥姥都早早起床,一边看着我穿戴整齐,一边安静地微笑。她会站在阳台上探出头看着我们一家三口走出小区,直到消失在大门外的那个转弯处,而我也会边走边转过头看向她,心里想着明年我就又可以见到她。
我六年级时姥姥住院了。那时的我对于生病的印象就是头痛咳嗽,需要去医院见穿白大褂的人,打针吃药,闻几天病房消毒水的味道,然后回家继续玩耍。所以我想,姥姥应该也是一样的。后来妈妈专门去医院照顾姥姥,半个月后让爸爸带我也过去,我很开心,因为这次不用等到过年就可以提前见到姥姥。
来北京后我再也没有住过院,但人的嗅觉拥有记忆,浓浓的消毒水味道很快便把我拉回到以前姥姥陪我看病的时候。满眼白色,药品推车发出的咿呀声,我没有恐惧,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走到病床前时,姥姥侧过头看着我,脸上是力不从心的笑容,刺眼的透明管子从她的脖子上伸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用来做透析的。姥姥没有像预料中那样抱紧我,我只是呆愣着,不知该如何反应。
陪姥姥的那几天,她的精神状态似乎很好,除了没办法下地走路,吃喝说话都很正常。我听到家人说姥姥过年前差不多可以出院,这让我第一次强烈地盼望年快些到来。
我离开医院那天,一直在陪姥姥说话,直到爸爸叫我该走了。我坐在床沿跟姥姥说“再见”,却被姥姥轻轻拉住,她犹豫了片刻后轻声对我说:“亲姥姥一下。”不知怎么,大脑里突然一阵强烈的疼痛弥漫开来,心就像被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握住。我不敢再低头,害怕泪水在下一秒决堤,我起身快速走出了病房,没有回头,也没有人看到我已在心里泣不成声。
不久后,爸爸突然再一次带我回去,在飞机上他小心地对我说姥姥走了,而我很平静,只是望着舷窗外空洞的黑夜发呆。最难做的准备往往不需要特别准备,一切都会在你心里暗暗铺垫,所有的猝不及防和意料之外都可以慢慢消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亡,我不认为自己勇气过人,但我接受了也走出了悲伤。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时常梦到姥姥,而每一次都梦见那些我和她的游戏欢笑。我甚至因此告诉自己,姥姥没有怪我,最后的那一刻我没有亲亲她,但她离开时记得所有与我相关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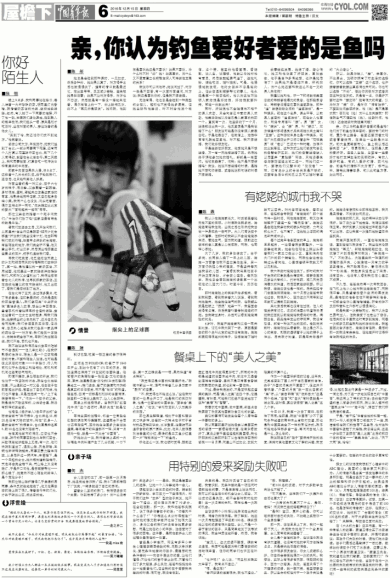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