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点,闹钟第一次响,我挣扎着翻身摁掉。之后,每隔10分钟闹钟再响,摁掉、再响。整个早晨在“叮铃铃”声中迷糊入睡,反复循环两三个小时,直至我忘记了它的存在。
凌晨两点躺下,设置一个7点的闹钟,成了我多年的习惯。我视之为一种激励、催促,7点起床是这一天充满希望的开始。事实上,很久的日子里我未见过北京的晨光。
这个习惯在做心理咨询时,我和我的心理师一起发现的。我很震惊,“原来这个闹钟响了这么久”。
那种被吵醒、惹恼、折磨的滋味在心理咨询中被一再唤醒。从2015年12月开始后的一年里,28次心理咨询,每周横跨北京东五环到西三环,50分钟的心理咨询成了庸常、琐碎、焦虑生活里的一次喘息、一次旅行。
首次咨询
第一次走进咨询室,连紧张都顾不上,我快迟到了。这是一家公寓内的一居室,经过厨房、卫生间、客厅。两张深蓝色沙发摆在角落,还有一张躺椅。并没有美剧、英剧里夸张的沙发,我想,什么时候来一次催眠,或许躺椅就派上用场了。
咨询师是一位普通女性,如你我一样,在地铁里擦肩而过也不会抬头。她年纪稍长,短发,和网站上的照片一样。我安心坐进靠里的一张沙发。
第一次想去咨询是在前年冬天。我坐在出租屋的书桌前,侧身可以看见窗外浓重阴沉的雾霾,找不到呼吸的出口。我着急地敲着键盘,打不出一个字。
那时,我刚工作4个月。进入一家体制内单位,每天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风尘仆仆地走进陈旧的大楼。楼里腻着一股油漆味,空空的肚子止不住地反胃。
窝在四面围着人的格子间,我写起了新媒体文案。词、句的堆叠和罗列,之后又是无止尽的修改。我强压着沮丧,宽慰自己:赚一份糊口的钱,交得起下月房租。
朋友大多进了报社、杂志社,跑起了正儿八经的新闻,我坐进了格子间弄起了“虚构”。他们跑进一个个现场,报纸上印着名字,挂靠在一个个单位下,而我们彼此间的生活隔了千山万水。
工作上的烦闷越来越不敢和朋友们倾诉,说多了怕打扰别人。有时,又急于和他们聊聊,看着微信对话框里一直跳不出来答复,愧疚感又涌上心头。
情绪像一个灌满水的皮囊,一个麦芒就能溃不成军。甚至恐慌起来,与朋友走在路上聊天,都要东张西望,发现四下无认识的人,才继续聊下去。
活在岛外
生活在北京的种种心绪自然也无法传递给父母。毕业后坚决留在北京,不如意似乎是自找的。电话更多地是问“工资够花吗?”“多跑腿,勤快点”,有时我多希望他们问问我,“今天开心吗?”可即使问了,我也就点点头,“嗯”一声。
关于孩子内心景观,他们是否真的有兴趣,我也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或许,他们也不知道如何问出口吧?临近毕业找工作时,妈妈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言语焦虑。有次,我发短信告诉她,我毕业论文被评上优秀论文,期待的表扬并没有出现,劈头就是“你工作找到了吗”?
除了工作日,大多数时间我赖在沙发床里。从小,我就有一个习惯便是在低迷期开始追星。我在一两个月内看完了一个日本组合出道20年来的综艺节目和剧集。
他们信奉“一生悬命”,拼尽全力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温暖。常常看困了就睡觉,醒了继续。循环往复,白天和黑夜用一集集40分钟的综艺节目串联。可惜的是,今年他们解散了。在微博刷到消息的那晚,我自嘲“连偶像陪伴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还有什么陪伴是长久的呢?”
谁说的,“人不可能活成一个孤岛”,而我分明活成了孤岛。躺在十二层的单人床上,下午日常杂音在耳边被放大,放学回家的孩童在楼下玩纸牌游戏,老人家在遛狗,更远的,还有人在叫卖。
没有办法,我想找一个专业的倾听者。
在一个提供心理咨询的网站上,我快速滑动页面,输入性别、价位。女性、年纪偏长、经验丰富、长相合眼、长期疏解情绪问题等。一位30至40岁间,短发、略胖的女性咨询师跳进我的视线。“就是她了”,我暗暗下定决心。
确认支付时,我没有犹豫。一次咨询费600元,那时我的工资不过三四千元,银行卡的额度可能更低。倾诉、吐露的欲望容不得再有迟疑,来不及再想下一周要靠什么生活,我需要被倾听。
求助
之前,我曾陆陆续续看过一些科普文章。那些写着“一次发现自我、探索自我的美妙旅程”的美言,吸引着我拨开云雾,看见光明。
知道我开始心理咨询的朋友仅有二三。我们大多年纪相仿,经历类似,听说过心理咨询。但当身边第一次有人说“我在做心理咨询”,大多还是一脸惊讶与迷惑。
“你有病?!”
“你不是很好嘛,笑得很开心啊!”
“花那钱干什么,我不要钱,你跟我讲!”
一笔开销不少的支出,到底能带来什么效用?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能给他们一个完美、有说服力的解释。
咨询的开始并不顺利。家庭、人际关系、对金钱的态度、外貌、如何对待赞美和批评……我们谈论一切,却没有目的。这背后的问题是我想要解决什么,更多的钱?更多的爱?似乎又不是。放松、从容的心态,安宁、稳固的内心秩序,我更想要这些。
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毫无逻辑,“这个……那个……”,我扶着额头,眉心拧成一团。这些话题我从未与人聊过,心理咨询是疑问出发的起点。
有时,我质疑“那些不过是小事啊”,咨询师总是回复,“那是对你重要的小事”。我又重新投入讲述。一团乱糟糟的毛线,被抽出一个一个线头。
不停歇的闹钟就是在抽线头的过程中发现的。她提到,被闹钟一遍一遍折磨的早晨,人该是多么的愤怒。但是我却没有,相反,我掉入了新的漩涡——愧疚,大学舍友常被闹钟吵醒,用翻身、叹息来抗议我的闹钟。
闹钟所带来的隐隐不安,如同编辑的催稿,愧疚感一再袭来,而我只能用拖延来抵抗。这种矛盾的存在极其不舒服。
逃避
咨询不如预期的积极,我也用更长的时间来逃避。
回头看,这一年咨询了28次,按照约定的一个月4次,我翘掉了一半的咨询。每次去,总要熬到最后时间点才出发。迟到是必然的,但时间是用一分钟8块钱计价。每次敲响那扇门,我冲进去的第一件事是要一杯水以及给手机充电。
没吃早饭,带着一个电量只有百分之十的手机出门。有一次,咨询师小声嘀咕:“你也需要充电吧?”
两三次的咨询之后,线头抽不动了。在大场景的回忆面前,我只有雾色弥漫的风景,情绪、快照深深刻在记忆中。
爷爷快离世的那年,我9岁。家中有把好看的椅子,我指着椅子问他,“爷爷,你死了,这把椅子给谁?”妈妈立即打了我一下,“乱说话”,旋即我被拖出屋子。在一个临终者前,“死”是避讳的。
高中时,成绩一落千丈,我抬不起头,身子藏进肥大的校服里。更害怕的是不敢说话。我看着“梅艳芳”,心里默念“不能读成梅兰芳”,脱口而出就是“梅兰芳”。周围同学爆发出一阵笑声,我脸涨得通红,用胳膊圈出一个空间,埋进去。
我记得的总是这些。咨询师常问我,“你在想什么?”“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甚至在一段咨询之后,她让我承认“心理咨询是没有用的”。我张不开口,警察又跳出来了,“没有效果暂时的,我愿意花更长的时间来看见效果”。
快结束的时候,咨询师说:“有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行走在沙漠里,我想搭着梯子来够你,但是找不到搭梯子的材料。”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崩溃。
这个漂在海面的孤岛,被浓雾笼罩,模糊得连我自己都看不清了,没有人来救我了。之后,我与她交流了内心的失落和绝望。“对不起,我为上次令你如此难过说对不起”,她回应。我愣在那里,好像从没有人跟我说过一声“对不起”,她真诚、坦白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十分郑重。
在过往的24年里,我是妈妈爸爸的孩子,一名按部就班的学生,一个机构里的职员。我听话、温顺、服从,自我的语言总是被更大的集体话语裹挟,对抗的方式就是沉默。
太多的鸡汤教你怎么做女生,怎么做员工,怎么做子女,可笑的是,仔细翻一翻大多自相矛盾。对与错,美与丑,道德与反道德,没了秩序,失了标准。焦虑、不安、失落,就好像那只闹钟,在我的神经里隐隐作响。
这时候,有一个人跟你说“对不起”。好像从前强加在身上的愧疚感,自己与自己的较劲,在一霎那松懈了。
端详自己
当咨询做到第20次时,妈妈知道了。从一开始我便没有瞒着她。但她没想到我坚持了一年多。果然,她的第一反应是“钱还够吗?”
我发了一堆短信给她,告诉她我没有严重的抑郁症,不需要吃药。得到一句“我不能理解”。但妈妈的理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了,我不再是以前在院子里徘徊着的孩子,不需要他们放手说声“走吧”。
我没有告诉她的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果。我可能在花一笔钱,花费精力做一件暂时看不到效果的事情。
我,一个“自个儿找病的人”。在东五环到西三环的地铁上,挤在人潮里,垂着眼皮,懊恼着又在低落、抑郁的沼泽里自溺。画出一周的心情曲线图,我不关心高点,只看得到低凹处。
直到我遇到一个故事收集者。他看多了人人身处世间的荒诞与温暖,告诉我“人需要一个整理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整理自我、表达自我”,看上去很简单吧。但击中了我,心理咨询不就是这样的过程么?
整理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去杂乱、模糊的我得到了理解,“无序”也是一种正常,并不是一种错误,我不需要为此感到愧疚。
想通这点时,是凌晨我躺在好朋友的家里。均匀的呼吸声,窗外疾驰而过的摩托车轰隆声,黑暗里朋友家的猫从我身上踩来踩去,时而凑到我的手机前,白光映着它的猫须,蹭着我的脸。感觉自己真实地踏在了地上,活在了人群里。
中学时,教学楼大厅里有一面镜子。路过时,我总是扭捏地在前面一晃而过,看个模糊大概,却不真切,又一股风般冲进教室。
这次,我又找到一面镜子。我要站在镜子前,仔细地端详自己,找到暗藏的怪兽,熨平心里的褶皱,关掉嗡嗡作响的闹钟。
张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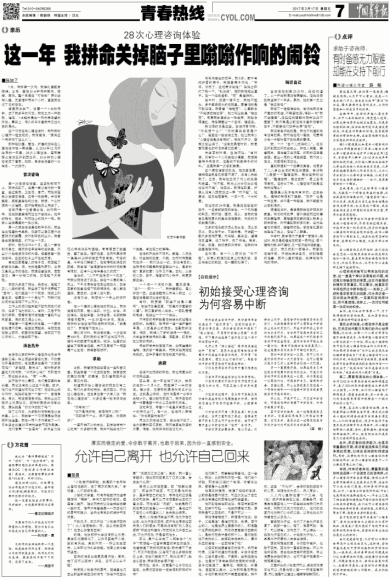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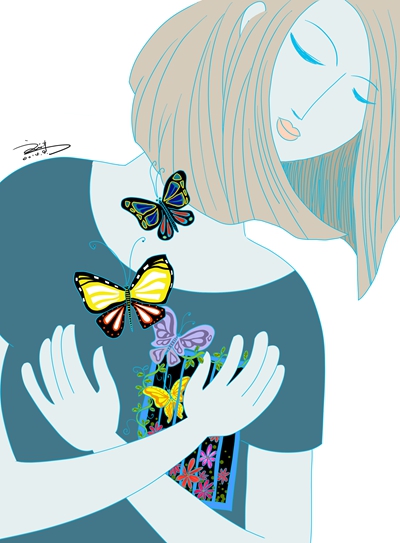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