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高龄的著名诗歌评论家李元洛,在出版了《万遍千回梦里惊:唐诗之旅》《曾是孤鸿照影来:宋词之旅》《风袖翩翩吹瘦马:元曲之旅》3部作品后,以一部《潇潇风雨满天地:清诗之旅》,为这一场纵横千年的诗词之旅画上了句号。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潇潇风雨满天地:清诗之旅》,近日在北京小众书坊举行新书发布会。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独家专访时,李元洛说,从先秦到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诗,加起来1万首左右;《全唐诗》收录了4万8千多首诗;宋诗约有27万首,金元两代约有12万首,明代尚未整理,据估计约50万首;而清诗的数量最惊人,据估计在800万~1000万首,远超历代诗歌作品总和,诗人在10万人以上。
李元洛用了两个词形容——浩如烟海、默默无闻。
李元洛认为,清诗的整体成就虽不及唐诗宋词,却远胜元明之诗,是仅逊于唐诗宋词的又一座高峰。夏完淳、陈子龙、钱谦益、柳如是、顾炎武、纳兰性德、郑板桥、袁枚、秋瑾、谭嗣同、梁启超……从明末清初沧海横流中的坚守,到避席畏闻的文字狱,从风尘侠女到巾帼英豪,从少年英雄到国士巨人,清诗未曾缺席历史。
在李元洛看来,清诗最大的特征莫过于充分体现了清代的艺术思潮,体现了古代史的尾声和近代史的波澜壮阔。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封建帝制结束,新的时代来临,清诗记录下了这个时代。
龚自珍,李元洛称其为“中国古代诗歌天宇上最后也最灿烂的一颗星辰”,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生于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期,当同时代的许多文人还在浑浑噩噩,大唱“四海晏清,天下升平”的赞歌时,龚自珍在《已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三首中反映了民生疾苦:“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龚自珍是看清历史的,他在《咏史》诗中写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龚自珍也似乎看到了未来,他呼吁“改革”是清王朝唯一的出路,提出了要培养和重用真正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就像他在最著名的那首诗中说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李元洛评价:“这种时代的最强音,不仅如鼓角震撼当时,如怒潮传扬后世,也如警钟警示今天。”
李元洛说,清诗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诗中融入了新的思想观念,比如个性解放、民主自由,“这一代诗人中,思想的新鲜开放,是历代诗人不可比拟的”。清代中叶的袁枚就是一个代表,他把奴仆视为朋友,破除了阶级界限,颇有平等观念。
据徐珂《清稗类钞·奴婢类》记载,袁枚有一个仆人名叫琴书,来的时候还是童子,服侍了8年之后想离开。袁枚不但主动为他毁掉契约,还以自由身,还赋诗送行,“都儿洒泪别阳城,来是垂髫去长成。人好才能八年住,春归那忍一朝行?交还锁钥知谁托,欲扫楼台误唤名。总为香山居士老,杨枝骆马备关情。”
我们现在常说“后现代”,那袁枚似乎更像是“前现代”,对女性解放也有超前的观念。李元洛介绍,据道光年间完颜恽珠所编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及清末施淑仪所辑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典籍统计,清代女诗人总数在4000人左右,“足可以成立一个女诗人协会”,相比之下,唐代的女诗人不过一二十个。
被袁枚收入随园门墙的女弟子就多达五六十人。他还以召集人与主持人的身份,在西湖至少办过两次闺阁诗词集会,在《随园诗话》中,对女弟子的诗词多有记载和表彰。袁枚在《二闺秀诗》中写道:“扫眉才子少,吾得二贤难。鹫岭孙云凤,虞山席佩兰。天花双管舞,瑶瑟九霄弹。定是嫦娥伴,风吹落广寒。”
李元洛记得,自己大学时代美学系列讲座的老师李泽厚说得好:“袁枚倡性灵,反对束缚,嘲道学,背传统,也是这同一历史逻辑的表露一样,它们共同体现出、反射出封建末世的心声,映出了封建时代已经外强中干,对自由、个性、平等、民主的近代憧憬必将出现在地平线上。”
如果说袁枚时代的女诗人还是“非主流”,那么到了19世纪末,“鉴湖女侠”秋瑾的横空出世,让从来都是“男人史”的中国诗歌史,有了女性的强硬位置——秋瑾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还是杰出的革命家。
1900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全国人均一两。消息传来,秋瑾的心情就是在《杞人忧》中写到的:“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
此后,秋瑾远上北京,东渡扶桑,投身革命。后来,战友徐锡麟举事失败,清廷发兵围捕秋瑾,许多人劝她暂避,她却誓死不走,1907年7月15日凌晨,在绍兴慷慨就义。
遥想百年前悲壮惨烈的一幕,李元洛背起了秋瑾的《对酒》:“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李元洛说:“清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后的辉煌,我喻之为落霞与晚潮。虽然是落霞,但它绚丽而不免苍凉的光彩,却是为落日举行葬礼;虽然是晚潮,但悲怆然然而仍旧澎湃的涛声,却预告了新时代来临的消息。”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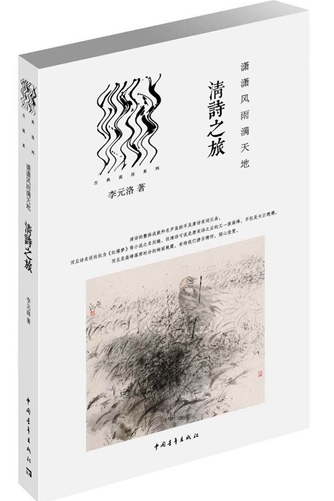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