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杯之路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啊!”说这句话的阿里木江·于山是第十三届“挑战杯”赛特等奖获得者,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生。如今,他已经毕业回到了家乡乌鲁木齐工作。
新疆流浪儿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2012年暑假,阿里木江·于山回乌鲁木齐,拿着学院的介绍信,来到自治区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一探究竟。他花了近两个月时间,走访了流浪儿童的家长和曾经被迫以偷盗为生的流浪儿童,与他们“混在一起”。
他发现这些孩子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在内地流浪时经常会和家里保持联系,让父母不要牵挂,还会时不时地给家里寄钱,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会隐瞒自己偷盗的行为……
在随后的《流浪儿童何以“流浪”——新疆少数民族流浪儿童的成因及对策研究》一文中,他认为,流浪儿童的产生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很难避免的问题,如何解决考验社会治理水平。对于新疆籍流浪儿童的救助,一方面要注意到他们的民族身份,一方面要避免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导致标签化和污名化。
阿里木江·于山对记者表示,不仅要把流浪儿童送回家,更要对这些孩子进行心理和行为上的矫正和引导,毕竟他们在童年时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历。要让这些孩子真正地融入社会,而不是逃离自己的熟人社会继续选择流浪。
在今年的“挑战杯”赛上,像阿里木江·于山这样的人有很多,已经形成了“新学人效应”:他们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在校大学生,不仅细腻地观察社会现象,也能清醒地给出解决方案,优秀项目众多,已经从“盆景”成长为“风景”。
教育:留守儿童内部存在“底层黑洞”
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流动儿童有什么不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许弘智在福建泉州市区、安溪县进行了实地调研。
“留守儿童群体中,好学生不太受欢迎!”许弘智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不同的是,流动儿童的榜样往往是好学生”。
如何得出这一结论?许弘智在支教时就做了一个社会实验,让每个孩子都在纸上写三个好朋友的名字,以此勾勒一个班级中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一所留守儿童学校的两个班级中,许弘智发现,每个班级有4~5个小群体,一个小群体有6~7个人,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群体有明显的核心和边缘人物。按照一个班级30人计算,小群体的数量占到了一半人数。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小群体中的核心学生一般不是成绩好的孩子。”许弘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在城市中跟随父母的流动儿童,他们有什么特点?许弘智用同样的方法调查发现,一个班级也有4~5个小群体,但是每个群体的人数也就3~4人左右,数量少一半左右,不同之处在于,群体的核心往往是成绩比较好的孩子。
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特点,许弘智用到一个名词——“底层黑洞”,意思是把“好学生”排斥在群体之外。
许弘智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在这种“反学校文化”的小群体中,越处于群体核心的人物,学业表现和发展期望等方面反而越不理想,这会促使他们毕业后走父母外出打工的老路——这是阶层固化的重要成因。
“对留守儿童的技术渗透很容易,但是文化渗透很难。”许弘智直言这是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困境。他调研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对技术很敏感,比如城市孩子用手机,他们也有;城市学校有电教设备,他们也不缺。可是,对他们的思想如何引导是个问题。
在对比研究中,流动儿童并非没有问题。“我们发现,问及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流动儿童会说做快递员、外卖员和去工地搬砖头。”他发现,孩子们的回答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做科学家、医生等答案,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城市孩子相差太大了。
“背后就是社会融入的问题。”许弘智研究中还发现,流动儿童交往存在结构问题,比如,贵州籍的孩子和贵州籍的孩子在一起玩,江西籍的和江西籍的孩子一起玩。
许弘智提出,阶层的固化问题,要从孩子就开始关注。
扶贫:调研显示南疆女孩14~17岁结婚,离婚率在30%左右
来自塔里木大学的薛珍这一次获得了本次“挑战杯”赛特等奖。她在南疆少数民族集中连片特困区调研发现,有的女孩在14~17岁就结婚,离婚率在30%左右。她们离婚后,受女方带孩子净身出户的传统观念影响,一旦出现两三次婚姻失败,有的单身妈妈就会有四五个孩子,加剧深度贫困问题。
“一定要解决这些单身妈妈的就业问题,同时还要帮着她们维权。”她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并不了解孩子的父亲也有抚养孩子的义务,很可能让代际贫困延续,薛珍给出判断:“南疆扶贫不能忽略妇女的作用。”
在这次“挑战杯”赛现场,不少学校利用“地缘优势”,所做的项目很“接地气”,同时也是直面问题。
塔里木大学位于南疆,李青教授是薛珍团队的指导老师。他们的调研报告《“精准扶贫”典型、经验与贫困户满意度调查研究——基于南疆少数民族集中连片特困区》显示,根据1247份问卷和144份访谈记录,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上,对因学致贫的帮扶满意度最高,达到了92.7%。
“不同的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认知和满意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李青直言,有这样一种观点:少数民族地区有自己的文化,即便贫困,但只要自己幸福感强就行,为什么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呢?
李青说:“有的少数民族贫困户,的确存在‘小富即安’的观念,满足低水平的生活现状,可是文化程度低和贫困会影响下一代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势在必行,但她坚持一定要精准识别和“辨证施治”。
其中,教育扶贫怎么做?作为该课题组的学生,薛珍在调研中发现,现在的教育政策很好,对职业教育也能免除学费,国家每个月还给学生提供生活补助150元,可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生活费仍然不够,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按照500元计算,还有350元的缺口,农村贫困家庭难以负担得起。
“国家要关注有这一情况的孩子。”薛珍提出建议,一些少数民族的孩子不上高中就外出打工,几年后发现自己的学历不够,想回到职业学院上学。可是,按照规定,只有19岁以下的孩子才能上学,他们想“回炉”却找不到门路。
“对这一年龄的限制可否松松绑?”薛珍说。
都知道因病致贫,是精准扶贫中难啃的硬骨头。李青带着学生调研发现,国家的医疗政策非常好,可是乡镇一级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
“关键是乡村医生太少!”她呼吁,对于因病致贫的群体,除了用政策兜起来之外,还需要想办法吸引更多的乡村医生。毕竟南疆地区地域比较大,老百姓的医疗不可能都靠去北上广解决。乡村医生不仅承担基层的保健、治疗小病,而且能实实在在帮助老百姓降低医疗开支。
“有这样一种因病致贫的情况,如果老公病了,老婆就要在家照顾,相当于投入了两个劳动力,扶贫先扶志不是一句空话。”李青指出,还是要发展庭院经济,在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通过劳动也能赚到钱,政府应该充当助人自助的角色。
婚恋:广州“巧克力妈妈”的难言之隐
走在广州的街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生马晓宇偶尔会看到中国女孩和非洲裔男孩拉着手,有说有笑。“非洲裔人士是广州的一个特殊的流动群体,中非伴侣在婚恋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是她的调研初衷。
2016年暑假,马晓宇和团队中的小伙伴,开始在非洲裔人士集中的区域寻找目标,可是一无所获,怎么办?她们通过社工逐渐打入这一群体的“内部”。
为什么一些中国女性与非洲裔的男性愿意结合在一起?她通过研究这一群体发现,这些女孩中不少都是从外地来广州做外贸工作的,她们面对的客户正是大量的非洲裔男性。
“一方面她们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不容易,另一方面,非洲裔客户做生意经济条件不错,而且性格外向,追求中国女孩的时候热情奔放。”马晓宇分析,不得不否认,中国女孩在爱情面前,也有实现阶层流动的愿望。
在调查中,她发现一些中非婚姻中也存在一些隐患。有的非洲裔人士没有合法签证,无法拿到结婚证,婚礼就举行一个宗教仪式,她称之为“事实婚姻”。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生婚变,男方有可能回非洲,法律将无法保护中国妇女的合法权益。
“她们生了孩子,我们称之为‘巧克力妈妈’。”马晓宇观察,她们会与自己的朋友圈越来越远,不仅要忙于工作,空闲时间还要带孩子,压力可想而知。
在调查中,“巧克力妈妈”并不愿意面对马晓宇团队。她们有自己的交际圈,外人的闯入,反而会增加不安全感。
她曾经遇到过个案,有个中国女孩为了和非洲裔男孩结婚,遭到家庭的强烈反对,为此父母还和她断绝了关系,“他们遇到的社会阻力太大了”。在研究过程中,她还发现,中国女孩与非洲裔男性之间还要跨越文化的鸿沟:前者希望伴侣彼此忠贞,后者却能接受多个性伴侣。“直到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男方才会告诉对方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曾有非洲裔人士对研究团队的女生进行追求,马晓宇笑着说:“他们的表达还是挺直接的。”
马晓宇认为,中国女孩如何选择伴侣是个人自由,但想要两个人能长久在一起,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性。比如在育儿上,非洲裔人士认为孩子应该自然成长,不必报很多补习班。这些孩子在中国上学之后,学习成绩显然不会太好。
“最迫切的提醒是,如果中国女性要和非洲裔男生结婚,必须要考虑到对方以后可能会回非洲这一点。”有一些非洲裔人士因为签证问题被遣返回国,中国妇女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马晓宇提出,如果广州收紧非洲裔人士的居留政策,他们可能会前往浙江义乌等其他商贸发达的城市,可是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专家指出,非洲裔男性比例过多,能否通过开放政策让更多的非洲裔女性来到中国,使该群体性别比例平衡,解决其内部的婚恋问题。
“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马晓宇担心,毕竟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对此如何应对和治理,是她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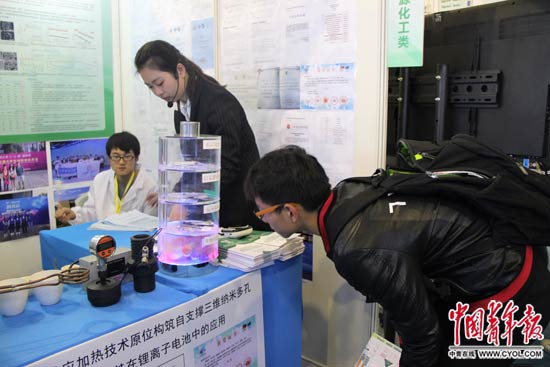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