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的3月18日,一个叫走饭的姑娘离开了凡俗世界。她罹患抑郁症,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她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微博账号,很多人因此认识了她。
在她走后,评论区来了很多人。抑郁症患者在这里交流病情和治疗经验,或只是单纯的发泄情绪。一些人日日来打卡,絮叨三餐和恋情;一些人路过,向沉默的账号打招呼,告诉她世界的一些美好之处。有科学团队利用这里的数据研究人类情感,也有志愿者在这里发现潜在自杀者,拯救了一些生命。
我和走饭共享一种疾病,至少我的医生是这么认为的。去年11月,我去北京市安定医院就诊,医生判断我具有重度抑郁症症状,而且很可能持续了很久。我至今都时时怀疑她搞错了,因为我太正常了。知道这件事的朋友也偶尔会表露出惊讶,因为我太正常了。
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家人和朋友。我抖机灵的能力从未疲软,葆有对一切不健康但好吃食物的渴望。我见人时并未形容憔悴,坚持着我不算成功的眼妆试验。我高谈阔论,追剧看书,最主要的是,我努力尽一个好家人、好职员和好友人的本分。如果我偶尔拖延、敷衍或者在压力下掉眼泪,那应该是源于我的人性本能,而非病情所致。
也可能是因为这种“正常”,我几乎从不吐露自己的精神状况。得病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怕给别人添了麻烦,也恐惧他人强行给予我的歧视或优待,偏见和善意。这个病火了以后,很多人都宣称自己与之有关,趋之若鹜之态仿佛旧时代文人渴望结核病,能于夕阳西下时被书童搀扶诗情画意地咳一口血。我很怕别人觉得我也是在赶时髦。我是一个“深柜”抑郁症患者。
我慢慢地发现,我这样的人在这个城市实在很多。她们隐藏在我热热闹闹的朋友堆里。我得病之后可能触发了某些雷达,于是我们互相辨认。我们只是很偶尔讨论病症,好像讨论“双11”购物清单。她们给我推荐好医生,以及哪家医院开药比较柔和,药量适中。新冠肺炎疫情多少影响了我们开药,大家交流哪家线上平台更靠谱。
上周我询问“你们想死的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大家都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一边痛哭一边观看在线学习视频。“你得晃一晃,找点事做,把这个念头晃掉。”一个姑娘告诉我。
结束生命是一个经常会出现的念头,但也不是难以对付。它只不过是一只尾随我的恶狗,我下蹲或者扔个石头它就呜呜哀鸣着跑掉了。我一直非常怕死,难以想象那种空旷——没有呼吸,没有念头,什么都没有。但有时我也会觉得活着太辛苦了。软弱的时候我不是想死,我只是想停止活,就一小会儿。
得病之后我开始明白这些人类基本状态的细微差别。就像我开始明白,爱和喜欢不等同于快乐。我仍爱这个世界,爱家人、自己。我喜欢电影、某个好看的明星或一条绿裙子。在其他人那里,这种热烈的情感会通往高兴,以至于他们会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而在我这里,这个连接中断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没有体会过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抑郁症患者“万念俱灰”的感觉。我只是很尴尬,有时有点不知所措:世界在我眼中仍然是彩色的,可那又如何呢?但爱也一直让我活下去。它变成了一种需求,我需要能给予这个世界爱。如果我中止了自己的生命,那我的爱也将停止了,我不能忍受如此。
最初发病时我以为只是肢体出问题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历着越来越剧烈的疼痛,可始终检查不出个所以然。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说话时会经历一些骤然的卡壳,好像闪电把一片空白劈进了我的头盖骨。我去医院,经历了一系列非常好笑的检测,包括一种像冷战题材电影里美国特工抓外星人的把戏:脑袋上戴一个编织着小球的大网兜,在一个女声提示下玩组词游戏,与此同时,电脑观察着我的大脑。
医生推测,我将情绪压抑在身体里,而它们最终钻了出来,窜上了神经,让我痛得嗷嗷直叫。这让我很不服气。我差不多是我见过的人中情绪最稳定的,我很少焦虑,从不崩溃,定期为爱情电影哭泣从而健康宣泄出眼泪。
但我也不能否认,那些可能不受控的情绪正在扰乱我的生活,集中体现在“又来了”的时刻。我开始表现出异常的状况,并越来越频繁。我的家人不知如何形容这些状况,于是统称为“又来了”。究竟谁来了?我们都不想多说。
“又来了”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结巴,词组消亡在我的大脑里,像饼干融化在牛奶里;我可能会痛哭,哭到浑身颤抖,像一把无法正常关闭的电动牙刷。哭泣时常发生在深夜里,我丈夫会被哭声惊醒,发现我坐在床头,眼泪从每个毛孔里冒出来,发出非常难听的哀嚎,像一只惨遭绝育手术的小公猫。我的手指强迫性地一下下敲击,如果他握住我的手,我就得一直抑制拿头一下下撞墙的冲动。
这些状况通常毫无原因。这让我很愤怒,好像回到家发现一个强盗正坐在我的餐桌边喝牛奶,而我无能为力。一些情形也会触发它“来”。在得病前我就对周围人的情绪非常敏感,得病后这种观察带来了极大的麻烦。那些他们自己都没察觉的情绪,我捕捉到,团成一个球塞进自己的身体,直到它们互相反应成一个炸弹,在我的系统中爆炸。
一些无心之语,一个非常微小的错误,会随机性地让我愧疚异常,让我质疑自己的整个存在。我曾因为外卖点辣了而觉得有愧于家族,恨不得自裁谢罪。整个晚上我以自己的存在为耻,整个星期我反复咂摸着家人的评价,“太辣了,点得有点失败”。这个过程于我的内心舞台进行,没有影响工作,也没有家人察觉。两个月后我回忆这场大戏,感到不可思议。
在这些小状况之外,我仍是那个稳定的自己。我是人群中的幸运儿,出生于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父母和睦;我接受了不错的教育,工作很有成就感;婚姻平稳,孩子可爱,丈夫也愿意负担一半家务。我的生活也有裂缝,那些幽深的、不能为外人道的瞬间。但谁的生活没有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病症会选上我。一些论文说是我脑中的化学元素在开一个不太得体的party(聚会),一些论文说是我的基因有问题。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活着。
根据世卫组织的调查,全球每100个人里有4个人患有抑郁症,而全球3.5亿患者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接受了治疗。每个病人的症状不一定与我完全一样。如果你感觉到异常,请不要依赖网上的量表,及时去专科医院或资质良好的综合性大医院精神科挂号咨询。得病不可怕,现代医学能给你很多帮助。去早一点,排队还挺长。
走饭在8年前说:“太生气了明天是周一,同意的请不做声。”我也不做声。我带着我隐秘的疾病,继续我正常的生活,经历一些很好的日子,一些很坏的日子,和大部分不好不坏的日子。那条微博最新的回复显示在23分钟前。
王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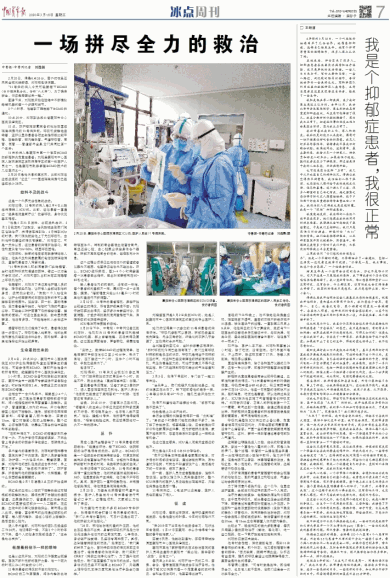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